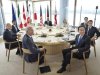(張倫,法國賽爾奇-巴黎大學教授)
本採訪刊發於《南方周末》時略有刪節
此為從作者處獲取的未刪節版
正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法國賽爾奇-巴黎大學教授、法國「人文社會科學之家」所屬的「全球研究院」教授張倫,最近談論疫情的話題引發中國讀者廣泛關注。
張倫師從法國行動主義社會學的代表人物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ne)教授,但他的研究興趣涵蓋了中國的現代性、認同、轉型以及東亞地緣政治等問題。
張倫感動於今年已經95歲高齡還筆耕不輟、幾乎每一兩年會出一本新著並上研討課的阿蘭·圖海納教授。「那種思維的清晰與邏輯讓人常常驚嘆,其勤勉也讓我感動不已。」張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去年夏天,張倫受《世界報》和法國文化電台之邀,去法國南方古城蒙比利埃(Montpellier)參加以中世紀意大利詩人彼得拉克名字命名的年度知識分子論壇(Les rencontres de Pétraque),期間與近兩年定居那裏的圖海納先生的好友、法國當代著名思想家、97歲的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聊了兩個小時。莫蘭剛去過巴西長途旅行,又去梵蒂岡見教宗,就有關人類當代一些重大問題即將發表的一個意見書進行了討論。莫蘭十幾歲時就參加過抵抗運動,著作等身。
「有人開玩笑說他和我的導師是『法國當代最年輕的兩位社會學家』。他們身上那種對正義、人的尊嚴的一生不變的追求,其實也是對我學術之外又跟學術相連很有影響的東西。」張倫說。
張倫在北京大學期間學經濟,博士讀的是社會學,但他想對西方文明、現代性問題有更深刻的體認與把握,就跟不同領域的學者學習,聽他們的課。這包括了他的導師的同窗至交、中世紀史大師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法國革命史大家弗朗索瓦·福亥(François Furet)、社會學大師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現代政治史著名學者皮埃爾·羅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大弟子傳人政治哲學家皮埃爾·瑪南(Pierre Menent)、著名社會學者米歇爾·韋沃爾卡、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他的夫人因新冠肺炎剛剛去世,等等。「其中有一位原籍德國的哲學家海因茨·魏茲曼(Heinz Wismann),是古希臘思想、德國近代哲學尤其是康德專家,他對我理解西方思想脈絡有過非常大的幫助,我陸陸續續前後跟他上了近二十年的討論課,直到現在。」張倫說。
與這些學者結下的深淺不等的友情,從中受到的學術和思想訓練,即便與他現在的教學與研究沒有直接的關係,但還是讓他從中獲益良多,「不會讓自己的思想輕浮」。他認為他現在分析問題時,從經濟、政治、社會、哲學、歷史各個視角都有,有時混雜在一起,有的時候從一個視角到另一個視角跳躍。「這或許還是歐洲的傳統吧,不太像北美的研究專業劃分比較細。我還是執着於一種看法,在人文社會領域,過度地分化專業,有細碎、抓不住要領之憂。對與制度規範已確立的西方不同的處於大轉型時代的中國來講,過度技術化的視角看待中國的問題恐怕會有失偏頗。其實審視這個世界的變動,也需要一些更複雜的視角才行。」
因此,南方周末邀請張倫就目前世界性的新冠病毒蔓延,從跨學科角度談談他的思考。
南方周末:張倫教授,你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現在,哈佛因為新冠疫情關閉校園,那麼,你在做什麼呢,原來的計劃打破了吧?疫與所有的個人發生了關係,這是我們這一代人面對的最大的危機,你和它處在什麼樣的關係中呢?
張倫:是的。很遺憾。我原有些寫作計劃,要查些資料,利用哈佛豐富的藏書,現在都不可能了。哈佛一些原來聽的課我也斷了。學生們在上網課,但我因為沒有固定的要求,也不習慣,就算了,在家讀書寫作看看電視,提高我的英語水平。另外,麻省沒有強制,但要求大家儘量呆在家中,出於對當地政府及他人的尊重,我也應該儘量呆在家。
至於您提到疫情與所有人發生關係,是你們「這代人面對的最大的危機」,我想說應該是的。就中國來講,前幾天我還在跟些年輕的中國學生講,最近二三十年成長起來的一代中國人,可能是一百多年來最幸運的一代:沒經過戰亂,動盪,也沒經過文革,又趕上中國的經濟增長期,個人與家庭的財富與機會都在增長,對外開放,科技互聯網等新時代的通訊技術,似乎給你們這代人一個良好的感覺,好像自己國家及個人的未來即使不是一片光明,也不會很黯淡,只要自己努力或再加上有能力的家庭的適當幫助,可以讀大學,漂洋過海到世界去留學,遊玩。將來即使負債貸款,也可以買上房子,成家立業,過一個不錯的生活。至少對都市的許多年輕人來講是如此……也許你們有意或無意地忽略去正視人生或社會可能具有的危機。今天考驗到了。而問題是可能這還不是個結尾,或許還有更嚴酷的考驗在後頭。我想,也沒有別的辦法:正視現實,召喚勇氣、良知、耐心,友愛,對社會的責任感,認真去面對就是,逃避也是沒用的。我的個人經驗就是:任何危機或磨難都可能是讓人永不能翻身,墜入深淵的原因,也可能是讓人新生,再造,超越自我的機緣,這一切端取決於你怎麼對待。爭取最好的,準備最壞的,就不會進退失據。
你問我與疫情帶來的危機是個什麼關係?其實我在上面已回答,我把它轉變為另一種機緣:這些年工作過勞,身體透支,那我利用這個機會調養身體,因沒有其他的雜務騷擾,可以按自己規定的時間作息,吃飯,讀書,寫作,學語言,鍛煉……又未嘗不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在法國二三十年,我基本就與人很少來往,社交、遊玩的事很少,甘做邊緣人,對於一個快二十八歲才正式開始學法語的人,要讀好書,拿到教職,做好一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學教授,其實不做些自我約束是不行的,人是不能什麼都要的。所以,除了要去定期買菜、做飯,本來對這種自我約束在家的日子就不陌生,所以沒有任何問題,還很珍惜這種有利思考的清靜。中國人喜歡扎堆,其實是不利於思考的。我最近一直建議認識的年輕朋友,抓緊這個機會,不要浪費掉,利用好,將來有一天回頭一看,你會覺得是一段難忘且豐富的人生時光,它讓你更深地體味一些東西。
南方周末:哈佛校長和夫人最近也確診染病,他的情況怎麼樣了?你覺得這是不是有一種標誌或象徵意義:作為世界第一的大學校長也未能倖免。此外,首相、王子、影星球星,以及哲學家德里達的遺孀,這些社會名流和權貴都患病了,而不僅僅是骯髒、擁擠、貧窮的籍籍無名之輩。文明世界或世界文明不堪一擊。假如你認為這有意味的話,它的意味是什麼?你認為這是文明的大危機呢,還是文明從來就是脆弱的、自視甚高而已?
張倫:我不認為這是「文明世界或世界文明不堪一擊」的表現。當然是一個危機,但也許從另一個視角看,它可能也是另一種「文明的表現」——至少在這些國家,權貴名流與你所說的那些貧弱的籍籍無名者相隔並不像許多人說的那麼遙遠。用本人最喜歡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看法來講:現代社會是一個「民主」的社會,一個最廣義上的社會成員的權利日漸平等的社會。我在西方生活三十年,因各種機緣,自己也認識相當一批學界與政界的著名人物,最大的感觸就是那種日常生活中所體現出的平等意識。自己的兒子曾與法國最富有的億萬富翁之一的兒子同學過,如果別人不講,你看不出他與其他的孩子有什麼區別,沒有一點那種驕奢狂妄之氣。也確實的,有些人今天是部長、議員,明天可能就是你坐公交車身邊的乘客,街角打招呼的鄰居。而這些人也確實沒什麼可傲慢的,如有架子,用法文講會被人非常mal vu(看不起或看不慣),被人嗤之以鼻,影響其聲譽。這些政要名人此次染病,除跟前期對病毒的傳染方式缺乏了解,整個社會對這方面認識、準備不足有關外,我想跟他們與社會的這種密切聯繫是有很大關係的。如果他們躲在某些地方,甚至像普通人那樣隔離,到哪裏去視察離人二三十米遠,不去從事某種社會接觸,估計也不會是這個樣子。
另外我想,在西方,那種貴族傳統在這種危機的時候是不是也是有影響的,越出現危機,那種精英的榮譽感越起作用:你不能顯示比別人高貴,怕死,你要盡更大的責任。去看看英法等國家一戰時那些貴族子弟、最精英學校畢業的學生成千上萬戰死疆場,比例遠比普通民眾要搞幾倍,或許就明白這個道理了。我想這是種現代的民主、公民意識與傳統的貴族精英責任榮譽意識在現實公眾生活中的奇妙結合,我們可以在許多事情上觀察到的。這次應該也不例外。當然,我還是希望他們能更好地做好自我保護,就像我對任何一個西方人、任何這世界上的一個普通人的希望一樣,大家都好好保護自己,為自己,也是他人,為這個社會早日戰勝疫情。在這場戰「疫「中,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戰士,保存好自己,同時就是消滅了敵人,為最終的勝利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