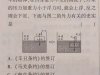立冬了,2022年,至此就剩下了一個小小的尾巴。
一整年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世界下沉的速度過快,我與我的朋友們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了深夜被黑色擊中心臟的人。
有一天和Y聊天,她孤懸海外,尚且是遠遠看着這裏的一切,也已抑鬱。我講不出什麼有用的話,只能講一些實話。我說,你看,我們就活在這個時刻了,那些少時讀過的所有文學作品所描述的動盪、荒謬、瘋狂、殘酷,也輪到我們去親歷了。那些遠走他鄉的旅外作家,那些失去信念草草結束一生的創作者,那些隱沒於人群的「太平客」……過去的命運最終都會落到我們頭上,這樣那樣的,好的,壞的。
瘋了,都瘋了。無數次喃喃。
認真地講,我仍有吃與穿,事業尚未停擺,朋友們還在近側,至親並未遭受滅頂的劫難。但肉眼可見地,受苦的人群在瘋長,枷鎖的包圍圈逐漸縮小,滿目的血霧越來越近了,迸濺到衣上時,已經很難裝看不見。
常常會有無法抑制的愧疚。那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場景,秋天餘暉落下的時刻,貓咪的頭蹭上手背的時刻,安靜地坐在桌前翻開一本書的時刻……一個聲音會冷不丁響起:我是要下地獄的,時間有早晚而已。你敢說自己沒有一秒鐘站在妥協的一邊嗎?你敢說自己不曾膝蓋一軟閉眼退讓嗎?時至今日還不做點什麼嗎?可你到底能做什麼呢?屬於眾人的大洪水已經來臨,但誰知道該如何去造一條舟?
一個意外的帶來寬慰的瞬間,是前幾日去蘇博。館內正好在做木心的展,館裏遊客寥落,就那樣靜靜放着他的紀錄片。寒冬的烏鎮,呵氣成霜,他窩在搖椅里語速很慢地回憶那個十年,具體的詞句記不清了,大意是:「我跟自己講,我不能被他們毀掉。就算把我關起來,我要去要紙筆,我要創作。不給我紙筆的話,我腦子裏也要在創作。只要我還在做我要做的事情,我就沒有被他們毀掉。」他說他從監獄的欄杆里伸頭往外看,「月亮很好。」
只要還能感受到冬夜裏月亮的美,就沒有被毀掉。任憑他們綁住我四肢,但凡思想還在繼續,他們就沒有贏走我的一切。
如果像那十年一樣,理性和科學被獵殺,一切都將變成惡的角逐。懷抱真誠善意的人,要逾越這個寒冬是艱難的。做好這個心理準備,然後拿胸口的熱氣一點點捂着它,捂着自己也是捂着別人。呵出的熱氣如同伸進天空的信號塔,我們都將靠彼此這一點點遙遠的溫度去越過寒冬。
前不久在某地演出,在劇場門口查驗完證件、掃碼完畢後,保安攔了不讓進去,說「院長正在前面大廳里參觀」。定睛一看,果然前面某一處站着院長等人,正對着一面牆賞玩。這一行人不過佔了開闊大廳的小小一角,所有人就被封了路。不管是着急去演出的、劇院工作人員上班快遲到的、馬上要開重要會議的,大家都被要求在遠處等待,為公卿清道。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我在這沉默的等待中愈發感到荒誕。開始問保安還要等多久。他說再等等。我又試圖講道理,我們持工作證,一切都可查驗,並非什麼來路不明的人,而且穿行大廳也就是兩分鐘的事,遠遠地經過並不打擾領導參觀。他不耐煩地說,讓你等你就等。我提高了聲音,這裏是劇場,是公共場所,難道現在是什麼封建王朝嗎?領導出行,普通人就沒有走路的權利了嗎?事先有通知嗎?有文件嗎?他不再言語,只是非常不友好地盯着我,示意周圍幾個保安慢慢圍過來。
但原本靜靜等待的人群,終於在這一刻開始有了反應。一位看上去同齡的姑娘站了出來,跟我一同高聲質問,保安自知理虧卻仍不放行。姑娘冷眼看他,直接拎了包邁開腿走,我跟着一起。想像中的阻攔並沒有發生,我倆就這樣直挺挺走進了大廳。沒想到的是,剩下的人目睹我們離開,也並未跟上,仍有許多人留在原地等待着沒有盡頭的「刑滿釋放」。
後來我跟那位姑娘互加了微信,得知她也是一位創作者。再後來我邀她來看春逝,她卻說自己早已有票了,還在來劇場的時候給我留下了自己的作品周邊。那一天的心情都是好的,並非因為在闖關時提早獲得了自由,而是在這個過程中識別了同類。我們都沒有背叛自己的靈魂。
友鄰分享給我麥克尤恩的一段話,他說創作者有三個本分:良知、書寫的技能和見證的意願。在如今的環境中,這大概是所有人抵抗虛無的一種可能:我救不了他們,但我沒有假裝一切不存在。
我還在這裏,我在記錄和見證,如果有一天我的筆不被允許,就用我的身體作為載體。這具普通人的普通軀體,她的耳她的眼,將努力地記住現在發生的一切真實,在生命的每一天選擇絕不遺忘。等到歷史被試圖改寫、蓋棺定論的那天,以及到達那天的漫長過程里,發我微弱之音,即便不能扭轉任何,也要留下痕跡。正是依靠這樣微弱的聲音,我們會找到同類。如果有一天我這具軀體不在,我的同類會繼續記錄這一切。如果有一天我們都被抹去了,至少我們沒有不發一言地沉入水面。莫管浪潮卷向何處,這漣漪存在過。
將軍,你的坦克很難摧毀,可坦克手也是個人。他有一天會想從欄杆里伸出頭去,看看月亮。
祝我的友鄰們平安。雖然常態化的奧斯維辛里,不會再有真正的平靜,但願大家能夠有片刻原諒自己、心無旁騖地擁抱月色,再回過頭來在夜深人靜時繼續書寫和抵抗。
以下為中國數字時代編輯摘自微博網友評論:
呂伏陽:知識分子在這片土地向來最脆弱。你相信嗎?有些痛苦來自「不願相信它已到來」。回京後我已徹底覺悟:未來一旬兩旬甚至一生,事情只會這樣下去,不會有心中一直虛妄期待的那個「迴轉」。所以,要快樂地活下去。為了種子留到看不見的未來;要麼就驚天動地地死,也為濺出幾粒種子,或吹動那人,看看月亮。
fo了蛙了瓜:「那些追問答案的人啊,不要羞慚。」
我坐金漸層那桌:知識分子總是多一分痛苦,因為他們總在思考「世界應該是什麼樣」……我想我會因為「世界是什麼樣」而停在保安圍欄前,也會因為「世界應該是什麼樣」而一腳踏過去。(姐姐晚安
等花開_leaf:最近在讀的一些書常常使我感到荒誕,仿佛八百一千年來都沒有什麼變化。這樣的日子還要繼續過多久,這些事件中展現出來的性格底色還要在我們的群體裏存在多久。至少不應該鼓足勇氣才能說真話,不應該要做好準備才能說真話。
冰瑩落雪:讀完想說什麼,卻在心裏打草稿的時候就擔憂地逐字逐句刪除,甚至於讀到原po的第一反應是慌張地保存下來,生怕哪天失去這份記憶。或許未來哪一天我所謂的「不妥協」也會被保護自己的沉默代替,在那天來臨之前,我只能痛苦地記住一切。
歐神妮可:曾經覺得我們離那荒誕的年代很遙遠,而實際上卻早已開啟了下一個十年。
海子街的瓊:來看月亮吧,即使隔着霧。
羊哥punk:活着的每一天感覺都是在對共情能力強的、有良知的人的一種審判。「我可能救不了他們,但我沒有假裝一切不存在」。含淚再讀兩遍。活下去,見證。
Reachable_:這樣的時代里,保持清醒和憤怒容易,保持抗爭或希望很難。但是難也要保持下去。我是這時代的一部分,那麼無論能客觀地留下什麼,主觀上,我都要留下屬於我的感受。同行。
雲妨psyche:永不妥協,永不做幫凶。
時鐘下的兔子:我也是一個創作者,我寫作,我繪畫,我從髮絲到指尖遵從生命的律動,我愛,我追求,我探尋,我不懼。想把鳥兒困於籠中的儘是妄想,因為沒有牢籠,因為根本就困不住。
你是哪塊小五花:大概是在深夜裏嘶吼的聲音實在太過於渺小,以至風輕而易舉地將他吞噬。只是寧願痛苦,也不要麻木。月亮很好,遙祝你我平安。
西貝利亞山下雨了:想起王小波致李銀河:你和我的勇氣加起來,對付這個世界總足夠了吧。當我跨過沉淪的一切向永恆開戰的時候,你是我的軍旗。
是溫慕舒啊:在怪誕與荒謬中,原諒自我的怯弱,更對那些同行的靈魂,他們為突破絕望所做的堅守與抵抗動容,在常態化的奧斯維辛里,還有黑暗中大雪紛飛的木心們,告訴我們不要被毀掉。
Boat輕舟已過萬重山:「常常會有無法抑制的愧疚」這句真的讓人流淚。在我沉默,在我假裝忽略,在我下意識選擇性的只看歌舞昇平的時候,在我安靜下來的時候,和我同在一片土地的哭泣和傷痛依然充斥在我的身邊、心上,於是我的沉默就變得可笑。
超大隻王:反覆看了幾遍原文和評論里的回應,仿佛內心也有什麼東西被點亮了,猶如這黑暗雲霧中亮起的一個火把,得到了另一個火把的回答。而又有更多未發聲的觀察者,他們也不是在沉默,而是在等待一個點燃的機會。
安之若素如我:這個世界共情能力有多強就有多痛苦。
噢哦耶嘿餵:「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看到「無法抑制的愧疚」一時愣住,轉眼看到「莫忘草木青」又放心了一點,加油誒,你並不孤獨。
落拓章魚:「歷史已經全部記住,就看人們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太陽照在腦門上:最近情緒很脆弱。雖然處於這個瘋狂的漩渦里,也多年不曾用筆記錄什麼,但我依然有熱愛的生活,有最愛的親人,也不至於為了幾鬥米折腰,在這個生搬硬套、沒有理性,令人窒息的運動中,自身的力量真的太小,我只能要求自己慢慢平靜下來,祈禱自己和愛的人平安健康,保護自己不被裹挾進這場瘋狂的運動中。
NLDRDDT-:堅守自己的觀念,最大可能地為作惡增加成本。
一潭水水養樂多:只怕是書寫下的記憶,也被有心引導篡改,變成方方類的『不實傳說』。如果生活在一個鼓起勇氣才能有良心的時代,大亂也就不遠了。
無恥海航欠債還錢:我貧瘠的語言無法描述我的心情。但我也是一位迷霧中試圖突破思維禁錮的普通人。這個動亂的世界,如果誰說真話,當權者就會給ta帶上「反」的帽子。希望越來越多的人清醒一點。
MoonVelvet:想起木心在無法獲得紙張的監禁歲月里,就在飛馬牌香煙殼的背面手寫曲譜。一切「愧」不成軍的人,不要羞慚,也不要被擊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