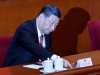改革時代到了末期形成兩種政治思潮力量,一種是改革派的復興新民主主義傳統,另外一種是80年代文化批評界轉化而來的新社會主義傳統,也就是通過改革,已經把時間流推回到1949年1956年這段歷史記憶當中。
本文的目的在於重新審查1949政制,是否可以轉變為憲政,也就是改良是否可能這個「天問」;以及一個更加遭到遺忘的問題,那就是是否可以實現民生或者共同富裕。我命名為1949政制的彈性:憲政或者民生。對1949政制,是消除,還是肯定強化,這是衝突的方向。
預設1949政制的可變性,可以內在地調整政治、社會經濟矛盾,必須假設專政力量的組成人員,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且具有絕對權柄。《聖經》中說,鬼王驅鬼。這時候政治、社會經濟矛盾被一個魔鬼所吞併,這麼這樣的魔鬼,如果沒有美化成上帝,那麼就是萬惡之魔王。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這個本來是虛的,根本無法實現的前提,被當做先驗的,必然的。這種「as if」爆發出一種強大巫術的黑暗,讓人無法理性思考這僅僅是前提假設。
官民矛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裡面包裹着無數的政治、社會經濟矛盾,共振集中起來爆發。這比沒有這種吞併帶來無政府主義狀態還可怕,代價更大,與吞併組合的程度,成正比。
1949政制就是彈簧,允許有伸縮,但是絕對不允許拉斷。左右的原教旨道德運動都是伸縮,真正實現就是拉斷。復興新民主主義傳統有一種努力:改革的憲政。可這是慣性的下注,就像下圍棋,在沒有眼位的大龍,不斷投注,結果死得更慘。新社會主義傳統渴望專制如刀,可以挖掉蘋果上的潰爛,是把挖掉蘋果上疤的刀,當做倚天刀。可是刀鏽讓蘋果爛得更快。
1949政制正當性來自何方,是來自本來應該具有的目的,還是秩序本身。其實對一種現存權力秩序無可奈何的維護,也必須來自這種維護還能產生和平、安全的秩序,如果是繼續瓦解,只會造就自然狀態,那就大錯特錯了。
對一種現存權力秩序無可奈何的維護並不成構成一種道德性信仰,它需要一個前置條件的滿足,那就是現存權力秩序並不是萬惡之源,並不是導致瓦解和不斷自然狀態化根本原因。這是首要的,必須首先滿足之後,才能保守。如果保守必然導致更大的自然狀態。那麼這種保守就沒有正當性,長痛還不如短痛。
1949政制的事實存在,當做正當的,或者合法的,這種做法不管是從反革命的動機,還是私人動機(不外乎一點課題經費),都是革命的,激進的。現有的政治權威,本來就是革命黨,還有壓根停不下革命腳步,連改革都是革命,經濟建設都是戰爭,所以越支持越革命,不僅現在革命,將來更革命。
堅持黨的領導,到底是維護秩序,還是超越憲政;到底是民生的,還是憲政的,處於混沌。可以說新社會主義傳統的政治文章,回到1949年專政秩序本來的混沌當中。
1949政制的原教旨道德運動,不管是憲政的,還是民生的,是一把雙刃劍,不管對官方還是對民間都是如此。左右派的原教旨道德運動會美化專政,加持其欺騙性,延長其統治,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改革對專政的延續。同時構成一種非政治或者反政治的情緒性政治壓力,到了 2003年之後,左派對改革的文革批判,同樣是對專政統治的非政治或者反政治的情緒性政治壓力。所以民間必須拋棄原教旨道德運動,用維權運動把它變為劍柄在握的屠龍刀。
1949政制是一種塞壬妖法。讓人聯想到《荷馬史詩》中賽壬歌聲使人變成的豬。中了社會主義魔法的中國人變成的 「豬」。女妖塞壬的迷惑人的歌聲。神女喀爾刻把他的同伴用巫術變成豬,改革三十年就是一場夢遊,豬的夢遊。知識分子變豬的概率,要遠遠大於普通老百姓。關在豬圈裏面的豬,從來不會對豬圈提出質疑,只會對豬食提意見。但是老百姓從來不會創造一套主義學說來帶上自己頭上,加持自己的豬性。也就是擺脫變成人更容易些,概率更大一些。
左右派的鬥爭是1949政制的內鬥,咬不斷與1949政制的臍帶。原教旨道德運動無關於1949政制的開端和終結。道德始終是一種對生與死,掐頭去尾的秩序,如果按照原教旨道德運動走下來,最後都會爆發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決開端和終結。既然右派在意圖中想告別革命,但是還會如期而至。原教旨道德運動不具有真正改變專政的能量。而後改革與維權運動如果說從1949政制中誕生,以法律取代道德,因此獲得咬斷臍帶的能力。
後改革的「靈魂剝奪」
後改革是對1949政制地基處埋的炸藥,那就是1949年政治秩序的死亡與其靈魂的重生,回歸中華民國法統。後改革跳出1949,後改革是憲政與民生之目標的加速度,最後的畢其功於一役。
就像後改革繼承改革目標,否定拋棄改革的政治方案及其實施手段,後改革同樣拋棄否定1949政制的政治方案及其實施手段。這就是後改革「靈魂剝奪」的過程。也是修復民國之魂魄的過程。1949年之後,民國之殘魂在大陸上空遊蕩。
「靈魂剝奪」經常使用,例如文人對法律的批判,就把法律說成沒有價值的技術,然後把自己說成總體性的化身。後改革是一種對1949年政治秩序的「靈魂剝奪」,尤其發生在(後改革的改革時代根基就是天安門的血泊)。1989年天安門開槍之後,對其靈魂,也就民生、民族和民權剝離出來,剩下一個殘忍恐怖的奴役和徵收剝奪。
與此相對應是,互相配合的是權貴官僚集團,他主動剝離靈魂,把自己以外的人,都當做剝奪和奴役的對象,當做了要征服的自然。後改革與權貴官僚集團才構成敵我之後,此外的,沒有永恆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需要不斷的界定和劃分。
1949年之後一直存在的對專政的消解力量,尤其是1978,更尤其是1989年之後。有的人直接否定,例如余英時,例如台灣國民黨以及台獨,有的人以改良的方式間接否定。間接否定這力量亦非政治性或者反政治的情緒性存在,本身並不構成政治以力量,反而是專政得以維持的因素。直接否定的,作為專政的敵人,以維護專政。間接否定,反而成為專政有限性調整,得以維持掌權的因素。
最明顯的例子莫如改革,不外乎是專政壽命的延長。他們雖然有有溢出體制的力量,但需要憲政降臨或者維權運動等超越體制的能量,來洗白自己。也就是類似於基督徒,需要基督再來才能到的恩典與拯救,否則都有着原罪。如無這一些,間接否定只會與專政同船異夢,異之夢以非政治性或者反政治的情緒性存在,除非訴諸於他們所反對的暴力革命,否則沒有改變政治結構的能量。
在中國如果去找一個最像在野黨領袖的人,找到的就是溫家寶。在野黨的路數,不斷地訴諸於民意,與權貴官僚體制隔開一定距離。溫家寶獲得如此巨大的民意支持,有一種隱隱然要衝出權貴官僚體制體系的位勢。當老百姓感念溫家寶好處的時候,都僅僅說溫家寶的好,已經不會再將溫家寶的功勞,歸於中共。那麼如此冰火兩重天的境界就出來了:中共完全等於腐敗的權貴官僚集團,而中共內的螺絲釘們一旦做了好事,感動了民眾,那麼獲得脫離權貴官僚集團的能量。溫家寶有一種趨勢,超出1949年,與毛澤東一樣。
由此看來,在憲政和民生兩個現代化未竟的層面,中共內的螺絲釘們如果做出有實質性的貢獻,能夠感動人們,那麼就化惡為善,可以進行贖罪,逃離死門進入生門。
新社會主義傳統的政治幼稚病
新社會主義傳統一小撮人與改革派的共享知識:例如中共可以變革,變為民生的,或憲政的。對於目標,新左派是含混的,游移不定的。相對而言,改革派呈現出來的,僅僅是強烈的希望,而且也當做政治立場,但是還保留着虛無的超越改革時代的渴望。可是新左派把強烈的希望轉化為一種道德性信仰,當做其政治方案不可離開的地基。後改革派決然否定這種希望,對其打擊最大。整個來看,整個新社會主義傳統就是一連串的精緻得引人入勝的情緒和偏見而已,然後就是隱藏在背後的個人權力意志。
新社會主義傳統隱含着中國資產階級成為權貴,分享權力的渴望,努力加入自己已加入方式正在破壞瓦解的權貴等級秩序。羅伯斯皮爾渴望着加入自己親手破壞的貴族等級。資產階級成為權貴的渴望,與工人階級成為小資產階級的渴望相同。,一般而言,整個階級上升的渴望,就是可以接觸到的上一個階層。
總是可以找到新社會主義傳統這種道德要求背後的權力意志。變成通俗的話,就是如此:我們的「神」能,等於我們能。這一小撮保黨分子還因此產生一種自傲:我聽了,你們要學我,一樣也要聽,你們跟隨我的路徑,走我的門。因此聽黨的話,就像太陽,聽保黨分子的話就像月亮,月亮從太陽那裏得到光線,因此也能照亮黑夜。太陽與月亮,一起分享崇拜服從的權利感。這時候,保黨分子隱隱然狂妄有這種趨向:非經保黨分子,才能找到黨。
新社會主義傳統被迫不能直面政治,而用文化政治作為表達形式,就學施特勞斯別搞政治,就在學院裏面呆着,帶幾個學生玩玩就是了。人文話語談什麼政治,回家抱老婆去。
根據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加塞特《大眾的背叛》中一個注釋的說法,知識分子大概在十五年之間,產生新一代的,對老一代進行背叛。1998年浮出水面的的新左派,就是如此,它是對四五一代的政治方案的背叛。他們比四五一代更加注重實現手段,那麼四五一代的手段,就成了他們的目的和道德性信仰,本來要加以改變的政治社會經濟條件,成為他們的指導原則。他們反對經濟自由主義,並且強化經濟自由主義替代自由主義。也就是他們和經濟自由主義者是在改革時代這個死胡同中,把死胡同當做全部世界的一對廝殺角鬥士。沒有能力跳出改革時代這個死胡同。當後改革判決改革之死,跳出改革時代,那麼新左派的預設條件全部挖空,其理論體系成為空中的七綵樓閣。
新左派的政治主張,後面表述為新社會主義傳統。作為碎片化群體,其自大和放大,有着兩層牢籠:過去社資之爭記憶之中,那麼就是一種保守主義的現秩序的政治神話,這個面對這樣一種根本規定性而粉碎:現代性之中,自由與秩序之間衝突,生成和凝固、掌權,就變成反自由反革命,也就是說秩序本身並不是目標,而是手段,而手段的追求並不能以啟蒙運動的方式,來獲取政治正當性。秩序只能是臨時的,被貶低的,被置於不穩固的地位,隨時被自由和革命脫殼而出拋棄的。
另外是作為內心虧欠臉紅的天安門背叛者和對四五一代超越的身體渴望出現。以啟蒙運動的方式,實際上一部分是為了掩蓋自己的背叛,一部分是是為了表明自己的身體,而不是而不是思想,已經超越了。很大程度是為了超越而體現出來背叛與超越的姿態。完全可以說成是似是而非的政治神話,以極端的方式涵蓋四五一代不夠政治性和滿足所在時代條件的缺陷。新社會主義傳統公雞攻擊母雞蛋下不圓,但是自己努力假裝下蛋,卻只會拉雞大便。
自由派注重理想層面的推行,而忽視具體條件,下降到改革洞穴當中,而新左派把具體條件當做一種信仰和主義,迫使人遵守,就在洞穴裏面,看起更像體制外的南書房行走。從精神病歷上分析,是一種迫使別人跟隨自己的渴望,也就是與改革派奪取馬楠式資產階級欲望暴徒,爭取香火的渴望。其身位是太監性「咱家」。太監要是沒有皇帝做後盾,就沒有任何權力制服別人。
在各種歷史相對主義病毒組成的迷宮和漩渦當中的新社會主義傳統,他們是對鄧小平改革政治方案的注釋學派,而不會注意到自己僅僅如此,而沉浸在對比右派的理念政治更加適應中國特殊條件的優越感之中。
事實就當做啟示,或者說成事實的規範性效力。有所不同的事實,通過對比他國,顯示出來不同的渴望,就代表中國具有獨特性。這一些不同且不說,僅僅是超越渴望的虛無主義政治形式的表達,還是不能證明其獨特性,因為在西方歷史中可以找到重複的。對比的時候,只是找到了拿來反面印證自己政治傾向的歷史事例。也就是對歷史政治知識,進行取捨,挑新聞事件來暗示自己的觀點,沒有整全性的現象學洞察。
在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運動及其政權中,可以發現兩種分野,主掌的精英積極將極權主義運動組織官僚化,而底層民眾則保持原教旨主義精神,保持其持續不斷運動。底層民眾要的是持續不斷的運動本身,而對組織官僚化與運動本身之間的衝突,保持道德批判的張力。緩解二者的衝突,其辦法在於讓底層民眾加入,分享掌權,也就是通過向上流動來抑制極權主義運動的運動性。
當然除了海洛英般的精神安慰,民眾得到的是手段之危害,而目的通過永恆的例外狀態而不斷拖延,好像到彼岸。如此不斷地把手段措施當作目的,也就是說是只見一木不見森林的歷史主義自義,不斷把手段例如黨的領導,通過道德論證,內在化,轉化為政治信仰。如此一來,改革目標就不斷延遲,拖延。就像夜航船黑夜中的燈塔,越行越遠,目標越模糊。
精英的組織官僚化,讓掌權成為唯一目標,犧牲一切原初目標,為掌權奮鬥,不僅僅在奪取政權之前,而且之後還是如此。
對於新社會主義傳統來說,掌權就是正當性。掌權的首要性,民族國家及其公共福祉反而成為手段。權力作為公共福祉的手段,一種反噬作用,歷史上非常常見。權力利用金錢與暴力,也可能為反噬。掌權者成為肉身欲望的天選民。魔鬼噬食了自己的魔鬼,也同樣是吃人的。他總是不惜一代代價,甚至國家的主權,來確保自身的特權。國家就是他的殖民地,這時候,他們就不是自己人,而帶有外敵的意味,家裏的外人,胳膊往外拐。所以變為買辦很容易。
啟蒙政黨的掌權邏輯,最後將所有的政治矛盾吸納入自己體內,那麼只有死路一條,相信自己可以解決,自己自我神話的迷狂,在永恆例外狀態中的迷狂。
簡單說,新社會主義傳統僅僅回到極權主義啟蒙及其建制化的內在張力,這種內在張力比啟蒙運動原初內核的內在張力,更大。因為極權主義致力於解決啟蒙運動原初內核的內在張力。所以我說,改革三十年與歐洲的現代化進程具有同構性,是其縮影。改革三十年的思考,基本上是身體的激情,作為時代的私生子而已(官方之外,就沒有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