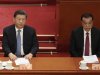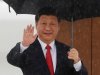吳國光:改革的終結與歷史的接續
一 改革的終結:意識形態領域的回歸和變遷
中國的改革已經終結。這至少體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第一是從意識形態來看。1970年代末在中國開始的改革,像中國歷史上的多次「變法」或「維新」運動一樣,也是從對正統意識形態的改造開始的。事實上,社會變革和對傳統思想的改造這兩個層次,往往同步;而在一個意識形態佔據支配地位的社會體系中尤其如此。當然,改革的肇因深植於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緊張之中,因而改革的許多具體發端和實施措施是由實踐者自下而上創造的。但是,這與下列判斷並不矛盾:只有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造出現突破,並且這一突破為當局所接納乃至高揚時,改革才真正形成中國發展過程中的新的歷史階段。因此,安徽農民的「包產到戶」,必須等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之後,才真正成為全國性農村變革的主導思路。所以,中國的改革始於「思想解放」;在原有意識形態框架下改造並利用這種意識形態,為社會變革提供了包括政治合法性、思想資源和政策原則等一系列要素。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不但看到所謂「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而且看到保守派的中堅正是傳統意識形態的發言人;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看到,知識分子曾經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成為極為活躍的政治力量,沒有在任何重大社會事件中缺席,甚至常常成為社會變革的引導。同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看到,8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見證了從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到蘇聯東歐式的對「現實社會主義」的批判思潮的主流演變線索,為社會變革的不斷深化提供着智能或嫌不足但卻充滿政治活力的解說和指導。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幅大相逕庭的圖景了。首先,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框架內部,尋求意識形態改造的空間已經大大縮小几至於無。80年代,儘管人道主義思潮和現實社會主義批判思路都不斷遇到政治上令人窒息的壓力,但卻持續顯露它們的鋒芒;而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隨着共產主義已經在全球意義上宣告死亡,這些思想似乎已經被送進了歷史博物館。而在中國思想發展的內部脈絡中,實用主義的「不爭論」戰略或「只做不說」的實踐方式,現在也早已走到了極限,遇到一個必然出現轉折的關節口:或者是在意識形態上走回正統,那就是以鄧力群為代表的所謂「老左派」或斯大林主義的傳統,要以理論糾正實踐;或者跳脫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向與《資本論》背道而馳的某種修正主義的「社會主義」乞靈,根據新的社會現實而試圖超越傳統理論框架。兩個傾向都在超越以在原有框架內實施改造為基本特點的「改革」,區別僅僅在於:一個指向超越框架,而另一個則指向反改造。
民間觀念的多元化,更是已經拋棄了無論舊有的還是經過改造的官方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試圖創造各種相對於中國五十年來的當代史來說的新話語,以另行解說現實和規範未來。開始,有「新儒家」思潮和其它新保守主義觀念的涌動;接着,是自由主義的浮現;同時,所謂「新左派」繼起,形成了與自由主義的激烈爭論。此外,民族主義也強勢回歸,與多派思潮形成了錯綜複雜的關聯。在至少兩層意義上,它們無一不是思想理論領域內對於原有意識形態的顛覆和革命。首先,它們在「改革」話語之外「另起爐灶」,已經超越了意識形態領域長年以來一元主導的發展,衝決了政教合一的制度框架;其次,它們不是像80年代的諸種「改革」思潮那樣,無意(也無力)與前改革時期的意識形態爭奪正統地位或官方解說權。
其三,被改革所否定的傳統意識形態,借三屍而還一魂,已經擺脫了它曾經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處境:一是「老左派」也被認為正在說出某種社會實情,二則「新左派」更是春風得意,三則當局也轉而動用傳統的意識形態手段,比如「三講」這樣的政治運動,來重新組織政治生活。如果說,共產主義框架的改造極限和民間思想的多元化,顯示了從變遷的方面「改革」正在被超越;那麼,這裏所說的三種「回歸」,則說明由改造傳統意識形態而支撐的「改革」正在被消解。一句話,改革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資源已大抵耗盡。
二 文革、穩定與民族主義:其它向度的觀察
第二,改革的終結還體現在歷史向度。我們知道,中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文革」的反彈。隨着對文革的懷念越來越強烈,這種反彈的力量顯然已經減弱到很低的程度了。當然,對文革的懷念來自不同的群體,也各有其不同的着眼點。比如說,一般民眾可能是渴望以文革式的政治運動來懲治腐敗官員,糾正社會不公;「新左派」的一些知識分子,比如崔之元,則試圖重新在文革中發掘某些理想因素,作為中國乃至西方政治改造的藍本;而當局也時有藉助文革手法,就像對待法輪功的宣傳動作,以實現其某些已經在改革中弱化的政治功能。總而言之,文革作為改革的積極資源的歷史狀態已經大大變化,而越來越成為校正改革缺失和弊病的一個重要歷史資源和政治參照系。
觀察改革終結的第三個層面是政治。1989年以來,中國政治的中心,就是所謂「穩定壓倒一切」。改革本來就是要改變現狀,但穩定則是要維護現狀;一旦對現狀的堅持佔據主導地位,為了維護穩定可以放棄改革,豈不就是改革的死亡?於是,我們看到,甚至單純經濟改革的許多措施,也會為了政治穩定的考量而胎死腹中。如果當局在1978年也是這樣一種治國哲學,中國哪裏還會出現甚麼「改革」時期?
第四就是經濟的層面。中國的改革,根本是經濟體制改革。簡略地說,這種改革大約走過了三個階段:一是「放權讓利」,即經過分權而改造經濟制度,這在80年代上半期已經大體完成;二是市場化,即引進市場機制以調節宏觀經濟運f0行,這在80年代中期起步,目前已經基本實現;三是90年代的所謂引進現代企業制度以適應市場化,即在微觀層面實現市場化,這也似乎大體上走完了其歷程。因此,自進入「十五」計劃以來,可以看到,調整產業結構、開掘國內市場、西部開發和引進外資等這樣一些東西,而不是制度面的改革,已經佔據經濟政策的中心。事實上,經濟增長確實也不再主要源於經濟體制的改革,而主要是源於上述政策。其中當然也包含部分體制改革的內容,但體制的改革卻明顯已經不佔中心和主導地位。
與此相關聯,但是不妨另闢為第五個層面以強調的,就是制度。隨着私有產權被承認,產權制度的變革已大體完成,今後面臨的主要是實踐過程中的安排和演化問題。國營企業改革作為經濟制度改革的最後一場攻堅戰,或成或敗,都已經走到盡頭。所謂「成」,就像當局所宣告的那樣已經成功,當然是結束了;如果是「敗」,那說明它也已經走到死胡同的底端。
第六是國際層面。中國當代改革與對外開放不可分割;而開放本身,作為改革的一種資源、一種途徑,現在也來到一個新的轉折點。以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標誌,中國已經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國內外都有許多人,預期這一步驟將為中國的下一步制度變革帶來進一步刺激。但是,從當局的表現來看,充其量,這只可能會帶來一些行政和法制層面的調整,但很難出現類似當年經濟改革那樣有力度和深度的其它層面的制度改革。而在國際政治方面,一個明顯變化是,冷戰的結束雖然緩和了中國的北部安全環境,但主流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善意並未增加,甚至在減少。這從中美關係的發展中可以看出大體脈絡。換句話說,經過後冷戰時代十年左右的調整和磨合,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雖然沒有走到「新冷戰」的狀態,但相互的衝突卻日益凸顯。更為重要的變化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態度和反應,已經和改革年代大大不同:所謂「改革」,在中國國際關係的含義上就是擁抱西方、學習西方,或者說親西方;現在則是民族主義持續加溫,反西方情緒濃烈。
與此相聯繫的是「改革」的正當性的終結。不僅是民族主義的崛起終結了對外以學習西方為特徵的改革的正當性,而且,在內部,以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為軸心來觀察,同樣可以說,「改革」作為政府政策和國家發展戰略,也已經在民眾的意識當中,也即在社會層面,喪失了正當性。「改革」已經不是民眾可以短暫犧牲自己利益而在長遠理性上可以讚賞的東西。人們不再擔心改革的基本政策或方向會出現變化;相反,越來越多的人從不同角度要求調整甚至改變現行政策,以平衡或糾正改革的負面效果。
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就同時出現了第八個層面的變化,即戰略層面的變化。自下而上的改革,像農村改革在其發動年代的軌跡,已經不可能重現,因為民眾越來越不認同改革的正當性。更重要的是,當局已經很難接受民眾中哪怕仍然存有的促進改革的自發性。至於當局自上而下推動改革的戰略,我們前面已經討論了它的極限與終結。於是,我們看到:要麼是下層的變革意願不能為上層所容忍,則社會層面的變革意願與動力越強,則國家與社會關係越是緊張、對立;要麼是上層的變革思路不為民眾所贊成,則國家以「改革」之名推出的諸種治理舉措,愈益遇到民眾的反抗。那種既有自下而上、又有自上而下、從而上下結合推動改革的戰略模式,已經很難再出現了。
上述八個層面的觀察都在說明:中國改革的資源已經耗盡,其支撐力量已經分化,其動力已經衰竭。因此,可以說改革已經結束了。也許,還有人在政策層面不斷試圖推動某些所謂「改革」措施,但這並不能改變上述層面的時代現實。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不難發現,領導層中的所謂「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分野,正在日益失去其指示意義。看一看現任領導人或候任領導人們,就經濟改革而言,誰不是改革派?就政治改革而言,誰又真的是改革派?他們本來都是經濟中心論的中國改革的產物。在一個詞彙失去其分辨現實中不同事物的意義時,這個詞彙還有甚麼生命力可言呢?反過來,這正說明,現實中的區分與矛盾,已經超越了這一詞彙的指代。換句話說,「改革」已經沒有意義,中國已經進入「後改革時代」。
三 走進「後改革時代」:非經濟問題與非漸進態勢
那麼,「後改革時代」在中國意味着甚麼?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恐怕首先還要回頭去看:中國的改革究竟意味着甚麼。簡單地說,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理解改革,因此也就可能從四個角度來展望「後改革」的含義,並檢討相關的思想論爭。
首先,在中國的歷史現實中,改革就是經濟改革。雖然政治改革呼聲如縷不絕,但從來也沒有真正實現。當然,一定限度的政治改革措施有所發生和實施,從而為經濟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政治條件。但是,改革等於經濟改革,這是中國的現實。因此,所謂「改革的終結」,當然就是經濟改革的終結。更進一步,所謂「後改革」,就可以意味着:或者經濟制度也不再改革,或者出現經濟領域之外的變革。事實上,我們可以把經濟改革的終結,大體理解為經濟問題不再是困擾中國的主要問題這一現實的表現。換句話說,中國改革比較成功地解決了這個長期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大國的經濟發展道路問題,而這曾經在至少整個二十世紀是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困擾。現在,中國當然還有她的經濟麻煩甚至潛在的經濟危機。但是,第一,能不能找到一條解決經濟麻煩的道路,顯然已經不是主要問題;第二,這些麻煩與其說是經濟本身的,不如說是產生於非經濟的因素;第三,解決麻煩的手段,主要不是通過經濟制度的變革,而是在經濟領域實行常規管理──即按照國際上的一般模式來不斷調節經濟運行,或者同時需要在非經濟領域進行變革。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不難明白,為甚麼90年代以來出現的多種思潮,從新儒家到民族主義,從新左派到自由主義,無論其立場和觀點如何不同,但都具有鮮明的非經濟關懷。事實上,即使是那種相信經濟發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並認為市場是經濟發展的萬能靈藥的觀點,顯然也有一種隱含的政治前提,即現行權威主義國家作為一種權力體系,足以提供市場運作的政治條件。這個前提似乎在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過程中得到了驗證,於是這種「市場萬能論」就可以偷天換日地將自己打扮成80年代曾經振聾發聵的改革新聲在今天的衣缽傳人了。殊不知,80年代作為改革理論支持的市場論,在全權主義(totalitarian)國家幾乎完全拒絕市場因素的歷史條件下,本身就是對傳統國家權力結構的深刻批判。進一步,它又是與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聲氣相通,因此構成一個以建立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配套架構為訴求的沒有自由主義卷標的自由主義論說。而今天的市場論,在理論上不過是傾力於論證已經泛濫的市場運作機制本身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在政治上則大體捨棄了國家權力改造的內涵(或將政治改造無限期推遲),因此在實踐中就不能不經常尷尬地淪為國家政策的辯護士,甚至是不公平市場運作下產生的少數新特權階級的代言人了。即使是那種呼喚公平市場的聲音,一旦在理論上落入「市場萬能」的窠臼,而不是訴諸國家權力改造,也就變成自相矛盾的論說(如果市場是可以自發解決公平問題的,為甚麼它至少在目下中國不能擺脫權力因素的干擾?),從而成為蒼白無力的一廂情願。這樣,與80年代不同,今天的「市場萬能論」包涵了消解政治改造的政治功能,正在日益喪失其對於現實的認知與批判能力。
可笑的是,有些批評者也偏偏響應論敵的這種偷梁換柱,要給這種「市場萬能論」戴上「自由主義」或者「新自由主義」的帽子。其實,這種「市場萬能論」連所謂「經濟自由主義」都不是,因為「經濟自由主義」──按照它的有力批判者博蘭尼(Karl Polanyi)的界定──在鼓吹儘可能由市場調節社會生活的同時,要求「自由國家」(the liberal state)──而不是政治專制──作為其政治前提。這種正版的經濟自由主義當然同樣要求削減國家的職能,但沒有說過這種功能削減足以改造國家本身。如果中國今天出現的情況是某些理論家所批判的「國家與市場共謀」,則這種狀況及其理論表現就絕不可以稱之為「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前提之一就是國家與市場的功能分割。這在概念上是如此清晰,以致令人懷疑那些這般混淆視聽者根本不至於如此理論無能,而是另有「新左派」與「市場萬能論者」的「共謀」以閹殺真正的自由主義了。其實,與風車作戰並不儘是理想主義的表現,它也完全可以是規避現實生活中某個真
正惡魔而又要表現某種勇氣的犬儒行為。
這裏,我們也就來到了解讀改革的第二個向度:改革作為漸進的變革。如所周知,中國改革以其漸進模式著稱於世,與前蘇聯當年引進市場化時的「震盪療法」和蘇聯東歐在政治上的革命性變革恰成對比。由此引出兩層涵義,需要在這裏討論。第一層涵義甚為明顯:改革的終結,也就是漸進變革道路的終結。這不是說,中國已經不再需要進一步的變革;而是說,能夠推動中國進一步平穩漸進變革的動力正在或已經喪失,以致中國的變革進入了一種尷尬的悖論:在民眾強烈要求變革的方面,當局乃至大多社會精英都無意進行變革;而對那些當局和精英階層自認為正在進行的重大改革措施,一般民眾要麼是無動於衷,要麼甚至是非常反感。在這樣的狀態下,只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當局和精英繼續佔據支配地位,從而社會將出現只有漸進而沒有甚麼重大變革的相對停滯狀態;一是大眾的要求突破了當局的控制,甚至與一部分精英相結合,從而形成自下而上推動的重大變革。這兩種情況,都與當局、精英與大眾大體結合而推動的平穩變革即改革大大不同。換句話說,一則由於當局拒絕重大變革,二則由於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日益與當局合謀,三則因為容易平順進行的重大變革已經大體都進行過了,剩下的都是難度極高的變革任務,則今後任何重大變革的出現,似乎已經不可能不伴隨劇烈社會震盪而仍然平穩漸進地進行。
第二層涵義則關乎更進一步的追問:改革的這種漸進性來自何處?鑑於自由主義對於理性的強調和政治上相對溫和的態度,它似乎就與「漸進」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那麼,無論是出於「爭功」或是「諉過」,我們能夠由此把中國改革解讀為自由主義的社會工程嗎?無疑,在中國改革的過程中,不自覺的自由主義論說早已出現(而不是等到90年代才橫空出世),自由與權利更在社會現實中漸次浮現與擴展。但是,第一,這與其說是自由主義支配國家政策(在我看來,這種狀況從未出現過)的結果,不如說是自由主義所揭示的個人自由之原發性的勝利;第二,在自由即個人權利尚未伸展到國家領域的時候,這種浮現與擴展只能說是非常初級的。換句話說,中國改革的漸進性與其說是自由主義思維的勝利,不如說是自由主義未能強大到改造國家即同時改造社會生活的多方面重大機制所致。因此,非漸進狀態的醞釀,並非宣告自由主義的失敗,而毋寧說是人們在實踐中追求自由不僅追求消極自由而且需要積極自由所由此展現出來的歷史軌跡。
在這個意義上,90年代以來出現的各種社會政治思潮,似乎都仍然落後於實踐,並沒有充分體認到這種「非漸進」轉折的呈現,而至多是曲折地從某個角度反映了這種轉折。新保守主義和新儒家頗為艱難地試圖以「秩序」與「穩妥」等理念拒絕這種現實發展,甚至所謂「自由主義」也還在一定程度上沉浸在80年代末對於歐洲大陸革命傳統的批判性反思當中,一如既往地偏愛某種循序開展的漸進變革。這都是在用價值判斷來替代現實分析,把願望思維當作不可移議的真理。另一方面,新老左派的態度卻都相當含混和矛盾。已經衰朽多年的老左派,儘管厲聲譴責新的階級分化,卻不可能在任何條件下支持工人農民對於現狀的反抗;一部分處於青春期或懷舊期的激進新左派,表現當然慷慨激昂得多,似乎有認同革命的苗頭,但是實際上卻在向上個世紀上半葉回歸,從今日壓迫制度的締造者身上汲取能量;而那些比大多激進者老了一個世代的新左派主流,在時代選擇上也老上一個世代,寧願認同上個世紀上半葉革命的產物,也就是50年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其原則和精神,而不是認同革命本身,就像他們不認同改革(即那種制度的溫和改造)一樣。這種取態,在中國今天的歷史條件下,都毋寧說是「右派」而非「左派」,如果我們把向後看看作「右派」的一個基本思想特徵的話。有一種新左派並且和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合流,試圖將這種「非漸進」態勢導往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國際層面,從而稀釋中國內部正在不斷積累的可能導致「非漸進」局面的政治壓力。在這個意義上,除了對剛剛提到過的少數激進者之外,「新左派」的名稱確實不太適合它目前的大多數發言人,儘管這些人正在相當熱情地從西方「新左派」尋找精神支持。他們的概念譜系或許是「新左派」,但在中國社會和思想現實中的角色卻是保守的。也許可以套一個當年概念來稱呼他們:「形左實右」。這裏,「右」是認同現實,「左」是倡導變革。同樣,也可以叫作「外左內右」。稍稍發展一下,則可以說是:國際方面左而國內方面右,概念層面左但現實層面右,經濟領域左而政治領域右。
四 歷史重新開始:資本主義與制度變革
於是,我們看到,大多數看來嚴肅認真的當代思想,在社會發展呈現「非漸進」轉折的時候,實際上並沒有跟上社會現實的發展並反映現實精神。這也就難怪90年代以來的思想論爭往往局限為「茶杯里的風波」,那麼合乎那些象牙塔學者自身要「做學問」的要求了。當然,這樣一概而論,總有其不恰當之處。如果我們換一個向度,把「改革」主要界定為在原有制度框架內進行改造和調整,則論述可能更為完整周到一些。在這個意義上,改革的「終結」或「後改革」的來臨,也展示出兩種完全相反的前景:一是現行制度已經不再需要繼續改造,就可以獲得政治正當性,維持社會公正和穩定,促進經濟繁榮和發展;一是突破現有的制度框架而進行改造,否則就不可能達成上述社會功能。與此相聯繫,不同的思想流派,對此有不同的解讀、判斷和展望,提出不同的社會政治發展道路。
對許多人來說,第一種前景看來正在成為現實。他們歌頌今日中國的「太平盛世」或「歷史最好時期」,期盼目前的狀態能夠成為「千年王國」而無盡持續。有人或許會問:在當代思想論爭中,難道真的有嚴肅的思想者持這種看法嗎?答案是:如果沒有,那恐怕也是思想的失職,居然不能完整反映現實;如果有,他們當然也會出之以更加微妙、老道和晦澀(據說等於深刻)的論述,而不大可能這樣赤裸裸地放棄自己的「批判」精神。於是,我們看到,對一些人來說,現行制度已經獲得了自我改造和自我調節的能力,它甚至正在真誠f0地實踐從「費改稅」到街道選舉等諸種政治改革,何況還有黨內民主的希望和中產階級的崛起──它們都會將現行制度平穩地帶進一個「更加」民主的未來。為甚麼要「更加」呢?「批判」精神當然不會像香港商人或北京太子黨那樣滿足於現狀。他們發現:現行制度有它的缺陷。就宏觀看,他們發現,在這個制度下,面對地方,中央權力太小;而面對市場,國家權力太少。就微觀看,他們發現,東部沿海地區享有太多特權。對外看,對美國的政策則太過軟弱。從理論到政策,他們構造出一系列學說。據此,中國目前的要務,就是強化中央權力,加強國家干涉,大力開發西部,對美敢於說「不」。換句話說,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改造現行政治制度,而是要不要強化根植於現行政治制度的國家權力。當然,你可以說這種強化也是「改造」,就像說重新中央集權等於政治改革;你還可以說,有這種集權才能為民主化創造基本條件,就像說文化大革命等於真民主而西方目前的「多元政體」不是民主一樣。不過,這種概念把戲恐怕只可唬唬從不深思熟慮的頭腦,作為理論論爭則未免玩笑了。
當然,對他們來說,最大的敵人在於國際資本主義,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這就需要討論界定「改革」和觀察「後改革」的第四個向度,即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如前所述,中國的改革,實際上就是中國走向世界、擁抱世界的過程。而「後改革」時代,因此也預示兩種不同的前景:或者中國成為一個「正常國家」(a normal state)而躋身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與世界主流形成對抗和衝突。目前一個相當明顯的發展趨勢是後者。表現在當代思想論爭之中,我們看到,在這裏,除了自由主義成為最大的落伍者之外,其餘的幾乎所有當代思想流派,都爭先恐後地加入了批判國際資本主義的大合唱。我這裏當然意含諷刺,而且,這種諷刺是雙重的:第一,它針對那些敵視國際資本主義並進而敵視國際社會的種種思潮的鼓吹者。前面我們已經發現,這些有政治頭腦的思想家們對於中國現狀的評價和分析,往往與沒有政治頭腦的國際資本一致:他們對中國的擔心,都是害怕中央政權太過弱小。二者的區別僅僅在於:國際資本希望中國政權進一步向西方資本靠攏,這樣它們就可以幫助中國「開放」、「改革」和穩定;而那些「批判者」則要求中國抵制西方資本,這樣就可以實現中國進一步的強大和平等的繁榮。不難看出,前一種觀點假設自己(即國際資本)比中國政權(或者中華民族──對某些論者說來)更高明和更有力量,這當然很容易被看破是具有偏見乃至陰謀f0的論調;而後一種論述則相信,中國現行國家體系一旦具有更強的自主性,就是當今社會一切弊病的最好(至少是最有效的)處方──這就滿足了中國的一切權勢:政治上的國家體系本身,經濟上的本國資本,和文化上瀰漫於大眾之中的民族自尊。
不可忘卻第二重諷刺,那是針對中國的自由主義的。如果自由主義僅僅是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在中國的代言人,就像當代中國的所謂「經濟自由主義」那樣,那麼,這一則不過是現實的背書,可謂真正落伍於現實;二則,就算在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它也不過是少數金權力量的聲音,從而遠遠不如「批判者」們能夠得到更為廣泛的政治、知識和情感權勢者的呼應。如果自由主義是試圖藉助國際資本的壓力而改造中國政治呢,就像許多歡呼世界貿易組織如歡呼孫大聖來臨一般的朋友那樣,則我們剛才已經談到,這種壓力是如何有保留,又是如何有偏見。在我看來,自由主義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概念反映,就像它決不是政治專制的理論一樣。在今日中國民眾作為個體與中華民族作為整體面臨兩面夾擊的背景下,儘管某些人試圖以批判資本主義來合理化甚至正義化他們自己對於政治專制的附庸關係,難道自由主義者就應該站到相反的立場上來為資本代言,哪怕是同時批判政治專制嗎?
歷史本身沒有這樣的偏頗,雖然不斷有人試圖偏頗地解釋歷史。在當代思想論爭中,有人要回到1989年重新尋找自己理論的根據,這顯然是一個聰明的動作:的確,1989年的事態發展,正是中國改革進入其死亡或終結過程的起點,從而也是後改革時代中國一切思想的發源地。如果我們借用福山(Francis Fukuyama)喜歡的黑格爾(G. W. F. Hegel)和馬克思的「歷史」概念,把歷史看作矛盾和衝突的場所的話,則1989年雖然對福山來說是「歷史的終結」,但對中國來說恐怕正是歷史的開始。至少,那是歷史的接續。自那時以來,以「改革」凝聚社會共識的現象趨於消失,多元的矛盾與衝突主導了中國的發展。更準確地說,在那場運動被鎮壓之後,金錢施威曾經短暫消彌了歷史;而隨着改革終結的過程走到底線,歷史真相再度暴露於思想之前,則歷史在今天到1989的小接續中應該可以發現其從「後改革」到前共產主義中國的大接續了。改革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這就是將一個共產主義的中國轉型或還原為共產主義在這塊土地上出發時的中國。它是「半封建半殖
民地」也好,是官員腐敗高壓政治也好,是道德崩潰倫理敗壞也好,其與改革前中國的距離都大大超過了與共產主義之前的中國的距離。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1989就是1919,「六四」就是「五四」;基本場景類似,雖然歷史角色頗有騰挪轉換。兩相比較,最大的不同,或許一在經濟,一在政治:今日中國與前共產主義中國相比較,經濟成就是明顯的,而這應該歸功於市場化;而政治的壓制力量卻也明顯更為強大,這是不是因為國家能力還不夠強大,或者是由於國家與市場的「共謀」呢?如果說,着眼於對現行制度框架進行根本的政治改造,已經構成了當代任何思想流派中可能有價值的部分的主要精神;而對於普通人的自由和權利的伸張,則成為這種改造的最為可行的基本方向和基本道路。爭論的真正焦點,正是隱藏在這裏;而爭論的弱點,也正是沒有可能在那種語境中誠實地直搗焦點。僅僅從這一點就能看出,究竟是甚麼東西在阻礙所有爭論者至少表面上共同讚賞的那些價值比如自由、民主、公平和秩序的實現:政治專制甚至不能容忍人們直接討論這樣的課題,遑論其解決?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在今天中國的重新開端,似乎並不比在上個世紀更為容易。
(作者吳國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人民日報》評論員、中共中央政改辦研究員,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 鄭浩中 來源:二十一世紀網絡版0二年六月號總第3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hk.aboluowang.com/2007/0327/34915.html
相關新聞









 國事光析:「孫悟空」代表什麼樣的中共外交?(圖)
國事光析:「孫悟空」代表什麼樣的中共外交?(圖)
 國事光析:習近平為什麼訪問美國?
國事光析:習近平為什麼訪問美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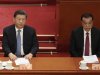
 吳國光:獨裁與惡政的螺旋效應:再談「斯大林邏輯」
吳國光:獨裁與惡政的螺旋效應:再談「斯大林邏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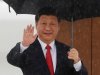
 吳國光:反間諜法的奧妙:隨心所欲抓敵人
吳國光:反間諜法的奧妙:隨心所欲抓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