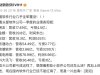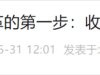圖為中國高鐵列車。(Wang He/Getty Images)
中共官媒日前發文指,近年來,高速鐵路的大規模建設新增大量高鐵車站,但至少26座高鐵站閒置,質疑誰應為無效投資負責,矛頭主要指向地方政府。專家分析,高鐵網絡是中共盲目發展的基建狂魔錶現,是中央和地方一起投資的,基本上是一拍腦袋就一窩蜂上馬的計劃工程,如今產能過剩,深陷債務危機。
另外,作為中共黨魁習近平形象工程的雄安新區,其高鐵站被寄望成為未來交通樞紐,現在也乘客寥寥,被指其投建完全是政治考量。
陸媒質問大量高鐵站閒置誰負責中共基建亂象引關注
5月21日,據《中國經營報》報導,中國至少有26個高鐵站建成後,因位置偏遠、周邊配套不足、客流量低等緣故,處於未啟用或關停狀態。
其中,海南儋州海頭高鐵站投資超4000萬元(人民幣,下同),去年7月,曾因建成7年多卻未能投入使用引發爭議,原因是日客流量不足百人,開通運營後鐵路部門虧損嚴重。後在輿論壓力下,海頭站在2023年12月15日才開始使用。
海南環島高鐵萬寧市和樂站、京哈高鐵瀋陽西站、丹大快速鐵路丹東西站和廣寧寺站等,均處於建成未投入運營的狀態。株洲市的九郎山站、位於北京經開區的京津城際高鐵亦莊站、距離瀋陽市中心二十多公里的瀋陽西站、位於南京市的紫金山東站、江浦站等,短暫投運後又因客流過小而關閉。
有的城市大量投入資金建設了高鐵站,卻大部分停止運營,如桂林,共建設了9個高鐵站,其中的五通站因位置偏遠、交通配套不足等因素,客流量嚴重不足,車站日均發送客流量不到200人次,開通運營僅4年就停止辦理客運業務。
報導質疑,這些花費不菲的高鐵站是如何從設計、規劃,到投資、建設,最終走向閒置的?設計單位、高鐵運營方和地方政府在這一過程中分別發揮了怎樣的作用,究竟誰應該為這些無效投資負責?
中鐵二院負責高鐵項目設計工作的人士稱,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減輕市區拆遷壓力,推動新區土地開發,也樂見高鐵站設置在郊區。
有地方政府人士表示,在高鐵建設初期以原鐵道部出資為主,鐵路部門在走向、設站等問題上的話語權相對較大。近年隨着高鐵建設地方投資比例越來越高,地方政府話語權也不斷提升,地方政府將擁有高鐵站與政績等掛鈎,投資建設高鐵站的積極性非常高。這就導致最近幾年規劃和開工的項目如沿江高鐵,整體車站數量遠高於早期規劃建設的「四縱四橫」高鐵項目。
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國鐵集團)人士則表示,鐵路部門在征地拆遷等方面需要依賴地方政府,部分沿線地方政府提出自己出錢設站並建設連接線,鐵路部門通常不會激烈反對。但線路開通後,如果車站出現交通配套不到位、客流量較小的情況,鐵路部門會減少停靠車次或暫時不辦理客運業務。

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5月23日對大紀元表示,鐵道投資實際上是中央和地方一起投資的,都是政府投資,它沒有做真正的可行性的研究,沒有看到客流量多少,人們的收入多少,人們的需求多少,這些其實都沒有。
「原來設計的時候就沒有真正地考慮過市場需求,基本上是中共的一拍腦袋就一窩蜂上的計劃工程,因為對中共的GDP有利,對政府的政績有利,反正浪費也就浪費了。中國高鐵有那麼多的線路都有這個問題,連電費都付不起,投資的貸款更償還不上。」
謝田說,中國的高鐵網絡就是中共的基建狂魔錶現,盲目擴張,盲目發展。
「為了構造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假象。基建狂魔,為了GDP,為了欺騙國際投資界,這個大興土木的計劃,糊裏糊塗地建起來了。現在發現沒有人用,也沒有這個需要,現在經濟下滑以後,老百姓更沒錢去坐高鐵了。」
美國華裔經濟學家黃大衛5月20日對大紀元表示,就高鐵亂投資的問題,很難去區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關部門之間的責任。而從經濟學原理看,當投資過了一個界限之後,再多的投資只會令到利潤率降低甚至是虧損。
「中國經過過去的40年發展,因為產品出口歐美,需要大量建設各種運輸工具,但是這些投資增加到一定幅度,超過了實質的需要。尤其是近十幾年整個經濟形勢沒有快速增長的勢頭,變成依靠不斷增加貨幣投放,不斷增加放貸來拉動,已經陷入了一個投資收益遞減的周期。」
中國高鐵仍在高速發展巨量債務成「灰犀牛」
2019年6月18日,負責高鐵建設運營的中國鐵路總公司,改制成為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是由中央管理的國有獨資公司。而仍在高速發展的中國高鐵,背後的債務問題倍受關注。
據國鐵集團官方數據,2023年,全國鐵路完成固定資產投資7645億元,同比增長7.5%;投產新線3637公里,其中高鐵2776公里。2024年一季度,全國鐵路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248億元,同比增長9.9%。第一財經分析,一季度鐵路投資明顯加速,雖然國鐵集團沒有公佈2024年全年投資目標,但作為投資淡季的一季度,已完成超過1200億元投資,這預示着2024年總投資額或將超過2023年。
但截至2022年上半年,國鐵集團負債已破6萬億元。
2024年5月,官方宣稱國鐵集團2023年「扭虧為盈」。但直至2023年末,國鐵集團資產負債率仍高達65.54%。
北京交通大學經管學院教授趙堅2019年初曾在「財新網」發文指出,人們通常只看到中國高鐵運營里程的世界第一和高鐵的快捷,卻對事件的另一面——高鐵債務和運營虧損的世界第一,及中國交通運輸結構的嚴重惡化視而不見。趙堅預言,以高鐵的財務狀況,終有一天會成為中國金融的「灰犀牛」,即巨大的金融風險。
灰犀牛常被比喻發生概率高、影響巨大卻被忽視的危機。
黃大衛表示,中共沿用大基建的方式拉動經濟,早期是通過投入資金,出現了虛假的繁榮,當高鐵項目出來之後,人們沉浸在所謂中國速度、中國製造的自我滿足之中,但建設超出真實需要的高鐵項目,會導致債務迅速增加。而十幾年前集中建設的高鐵,又已進入維護的高峰期,需要大量維護資金,增加了整個債務水平。
「很多的高鐵線路都是虧損的,根本無法償還債務,疊加原來已經有的地方債務,房地產債務,中小金融的債務問題,導致經濟硬着陸的風險不斷增加。」
謝田認為,中國現在大規模產能過剩,高鐵實際上也是一種產能過剩。「它就是基礎設施建設過剩,沒有市場需求,沒有消費基礎,但是它還要維護網絡,維護站點。現在陷入債務危機,中央政府的債務,地方政府的債務,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高鐵是盲目、浪費、過度擴張性的基建的代表,或一個象徵。」他說。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un Huang)(黃大衛授權)
雄安新區的高鐵站被聯想
有網友借中共黨魁習近平授意建設的號稱「亞洲最大高鐵站」但卻空置的雄安新區高鐵站諷刺,指這種亂投資和亂建設是自上而下的,而且不僅局限於高鐵領域:「來看看千年大計的高鐵站」、「與全國爛尾的項目比不算啥」。
雄安新區是習近平主推的國家級重點建設項目,在2017年4月1日正式設立。官方宣稱其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但雄安新區一直不被看好,因它位於內陸,沒有經濟基礎,沒有發展經濟的吸引力。另外緊靠白洋淀的雄安是華北低洼地帶,易受水淹。
過去幾年雄安新區的建設時斷時續,爛尾一說頻傳。其中,號稱亞洲最大的雄安高鐵火車站,2023年1月一度被視頻曝光站外雜草叢生。
2023年5月10日至12日,習近平到雄安新區,稱自己對雄安新區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不能心浮氣躁」。他還在河北開會,親自督促在京央企總部及子公司加快疏解(搬遷),警告:「不能憑自身好惡,需要搬就得搬。」
但習近平離開河北近一個月後,親北京的香港《星島日報》2023年6月6日報導,記者在雄安實地採訪,看到高鐵車廂乘客寥寥,站台大廳空蕩清冷,人流稀落。車站除兩家餐廳,再無其它商鋪營業。市內的居民安置區、商務中心、市民服務中心等也不見人潮。
有當地人向港媒透露,投資逾300億的雄安高鐵站,當時雖已開通運營2年多,因缺少交付資金,似仍未通過正式驗收。
黃大衛表示,雄安新區高鐵站與陸媒前述講的高鐵站亂象是另外一個概念。雄新新區完全是政治考量,當時是想建立第二首都,把北京的行政中心搬去雄安。但問題是中央要北京的機關企業搬過去,搬遷成本要各個企業買單,企業並不願意浪費這麼多的資金去完成政治上的任務,就導致了雄安新區的高鐵站沒有什麼使用。
黃大衛說,這主要是政治需要跟經濟發展,以及個體之間的一個矛盾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