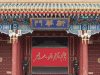在異族的鐵蹄踐踏之前,皇權早已拗斷了這個民族的精神脊樑。
1
如果說在近代以前,有哪一段歷史最讓中國人的感到屈辱、不堪回首,那麼我想也許非南明史莫屬,站在明朝和漢族的角度去看,化用丘吉爾的那句名言:人類史上,從沒有這麼少的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征服這麼多的人。
關於滿清入關之時一共有多少兵力,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數據記載,按照比較靠譜的推測,當時的滿洲總人口不過就兩百萬左右,再減去老人、婦女、兒童等人,最後的實際兵力也就在9萬左右,如果加上蒙古軍隊,總兵力應該不超過12萬人。
反觀當時關內的漢族政權,崇禎上吊後的南明,經過徵兵等措施後,賬面上可是有百萬大軍的實力。可是就是這樣一個一百萬打十來萬「優勢在我」的大好局勢,外加山川險阻、夷夏大妨、兩百年正統王朝積威等等眾多對南明有利的因素,滿清入關後對明朝的侵攻、掃蕩卻如喝涼水一般痛快。
沒有東晉的淝水之戰、沒有南宋的擂鼓戰金山,從1644年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到1662年永曆皇帝被吳三桂用一根弓弦勒死,南明一共只存在了短短18年,大明死的創紀錄的脆生。
期間,中華大地天下披靡、萬民流離、剃髮易服、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明朝的軍民就像是被驅趕、宰殺的牲畜一樣,對入侵者幾無抵抗之力,明朝的知識、軍事精英則紛紛賣身求榮,毫無氣節的投靠「新朝」的懷抱。

這樣事情,如果發生在一個如古印度那般沒有統一民族精神、不看重現世的榮辱興亡的、只等着新征服者出現在興都庫什山口就乖乖歸順的民族身上可能也就罷了,畢竟人家不太在乎這個。

可是,中華文明發展到明朝,偏偏是最以「氣節」自詡的,有明兩百多年,士大夫一直把「忠君愛國」「夷夏大妨」的口號喊的震天響,到了明末,這些口號還成了束縛皇帝自己作出決策的絆腳石——崇禎皇帝之所以在天下糜爛時遲遲不肯作出與滿清媾和或者遷都南京的決定,就是因為朝堂上總有人在唱不可割地求和、祖宗社稷不可輕棄的高調。

這樣一個喊了兩百多年愛國口號,在內部時刻拿着放大鏡找「奸臣」,把任何主張妥協退讓者都揪出來當敵人來消滅的「皇明」,怎會在敵人真的打到家門口時「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呢?
才18年啊,這跪的也太快了吧?
這些疑問,是我大學讀明史的時候就一直存有的。前兩天再讀顧誠先生的名著《南明史》,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歷史學家顧誠
首先說說顧誠先生這個人,很多非歷史學的人一聽這個名字,往往就往80年代寫朦朧詩的那位顧城那裏想。其實我們歷史學界的這位顧誠先生在成就上絲毫不應亞於文學界的那位。
顧誠先生是北師大的教授,主研明朝歷史,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特殊年代依然拿出了一系列今天看來頗有價值的史學成就。最著名的一個,我想當屬他對李岩的研究,郭沫若寫《甲申三百年祭》,花了大量篇幅寫這位傳說中李自成手下的幹將,後來又因為《甲申三百年祭》被領導人定為「全黨都要學習」的模範文章,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該文一度成為明史學界不容置疑的研究起點。
可是作為一位嚴謹治學的歷史研究者,顧誠先生偏偏在那個年代對這篇「學術聖經」提出挑戰。他在論文《李岩質疑》當中,用嚴謹的史學證據一步步進行推論,最終提出了「至今未發現一條可以證明李自成之外存在着另一個李公子或李岩的可靠證據」的結論。等於說郭沫若的論述是在無的放矢。
我上學的時候老師曾經評價說,顧誠先生這篇文章相當於明史界的《君士坦丁大帝贈禮的證偽》,而顧誠先生的這個膽量和對史學嚴謹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了。
這段對郭沫若的抬槓被收錄在了此次出版的《南明史》中,而如果你在往下讀,會發現顧誠對郭沫若權威說法的挑戰不止於此。
比如《甲申三百年祭》中認為,李自成在進城之後,是因為腐化墮落才喪失民心丟了江山的,此論在上世紀中葉曾經頗為興盛一時。
香港那邊的金庸在小說《碧血劍》裏也以此為基礎塑造的李自成形象,一個前期豪俠仗義,後期腐敗忘本的形象。

可是顧誠在《南明史》當中,用了一個特別簡單的方法就擊潰了這個傳統觀點——他就把李自成從進京到敗亡的時間線給大家縷了一遍,「三月十九日大順軍進京,四月初十左右,即得知吳三桂率部叛變回軍攻佔山海關,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帥大軍離京平叛。」李自成在北京,一共也就住了二十三天的時間,屁股還沒把龍椅坐熱呢,想腐化能腐化到哪兒去?
顧誠還舉了很多王朝腐化、衰落的例子,說明腐敗對於一個政權,一定是一個內生於制度的、延續時間漫長的過程。
所以《甲申三百年祭》在這個問題上的立論和結論都是不對的,腐敗不是突然發生的,也不會因領袖的個人意志而突然消失,李自成對他的政權能做的事,其實相當有限。
當然,顧誠在該書中重點解謎的,還是南明衰亡的過程,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個問題——一個尚帶甲百萬,掌握中華正統、以氣節自詡的王朝,是怎樣在異族入侵時秒跪的?

2
在顧誠寫《南明史》以前,很多史家對南明敗亡的論述承襲了清人修明史時的一些觀點,把明亡歸咎於「忠奸之辯」——明朝之所以亡國,就是因為史可法這樣肯壯烈死節的「忠臣」太少了,而馬士英、阮大鋮這樣賣國求榮的奸臣太多了,活活的把大好河山賣給了大清。
這套說辭,當然是老百姓最容易理解的,而清朝作為後繼統治王朝,也希望老百姓這樣想——畢竟哪個統治者都希望自己治下能多一些陪自己一條路都到黑的忠臣。

可是顧誠先生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基於史料作了一番非常細緻的呈現,比如史可法,他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接任兵部尚書一職,又怎樣迫不得已「自請都師江北」,在江北四鎮、他看到的四鎮兵馬是個什麼樣的狀態,最終又是以什麼樣的心態困守揚州城。而後世又出於什麼心態一定要為這位忠臣的軍事能力「貼金」,明明只守了一天,卻非要說他守了十幾天。
在顧誠先生的還原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史可法其實是一個能力不足的垂死王朝的裱糊匠,與傳統史學敘事中描述的那個壯懷激烈、主動請纓、對保衛大明、收復河山信心滿滿、胸懷韜略的「文岳飛」形象不同,史可法在南明歷史舞台上的表現,全程都是非常被動的。
「他缺少雄才大略,總想處處應付,八方妥貼,最後落得個事與願違。」這是顧誠對史可法的總體判斷。而看了他的相關論述後,你會贊同他的判斷——他忠心也許可嘉,但卻是一個不合格的「大明裱糊匠」。
當然,這種能力不足實則並也不怪他自己,自開國以來就防權臣如防賊的大明,從來不會主動培養那種能在危難時刻力挽狂瀾的能臣,英宗時土木堡之變,瓦剌軍打到北京城下,千年的鐵樹好不容易開了一次花,出了個能人于謙挽狂瀾於既倒,結果下場還那麼慘,後世的大明臣子們就更不敢「逾矩」了。
史可法其實也是晚明那種壓抑氣氛當中在官場上委屈求全的渺小一分子,他性格中的最致命缺陷是被動,缺少祖逖、岳飛那種救國英雄所必須的主動精神。
只不過在山河傾覆、社稷板蕩,中國的傳統忠奸敘事要求此時必須抬出一個人來做一做忠臣表率,唱一出「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的悲歌。而史可法好歹在揚州嘗試着守了一下,矬子裏拔將軍,只能是他了。
再讀下去,你會發現就像《南明史》中的「忠臣」沒有那麼忠勇,而「奸臣」們,似乎也沒有傳統敘事當中那麼可惡,他們其實就是明代有意培養的那種「被動型人格」的另一種體現。與史可法只是一體兩面而已。
這裏面的突出代表,大約是美女柳如是她老公錢謙益,清軍遠在天邊時,他作為東林領袖,愛國口號也是喊的震天響。好像全天下就他錢某人最愛國。可八旗軍的鐵騎一到南京城下,這老夥計果斷就慫了,剃髮、開城、下跪,一氣呵成,是漢奸里的英豪。
從表面看,錢最初的「戰狼」與後來的秒跪似乎是兩個極端,但在顧誠先生為我們還原的那個南明場景當中,你就能理解他為什麼那麼干:忠君愛國、華夷之辯這些口號,本來也不是錢謙益這種人自己思想中內生出來的人格理想,跟當時所有能夠被明朝那個體制所吸納的人一樣,錢謙益其實也是一個皇權和社會強力說啥是啥的「被動型官僚」。
在清兵沒來之時,晚明的主流是袖手高談忠君愛國,那他錢謙益就也談,一不小心還因為文辭卓著,混成了東林領袖。可是當清軍的屠刀架在脖子上,一種更大的強制力到來時,他頓時就隨風倒了。
相比之下,反倒是投降之後,錢謙益倒有了一點發自內心的主動性,多次與殘明勢力暗通款曲,試圖反正,但此時已經晚了——可悲是,在那個年頭,像他這樣先跟風「愛國」、又跟風投降,活到人生最後才隱約有了一點自覺、卻也晚了的人物,並不在少數。

是的,晚明政局的一個奇葩之處,就在於它的中心被一群典型具有「被動型人格」的人所佔據。
無論是抗清的史可法、還是降清的錢謙益,亦或是後來那個被推上皇位、然後一門心思到處逃跑的永曆皇帝。他們的性格共同點就是都是極為被動的人,只能被歷史大勢推着走,而不能也不敢去主動改變形勢。讓這樣一幫人來主持與滿清戰鬥的大局,當然不亡國才怪。
而這種人格如果再墮落一步,就是後來被魯迅先生所深惡痛絕的那種奴才。

所以從晚明的士大夫秒跪,到清代的奴才遍地,這個過程其實如德芙一般的絲滑。
那麼那個年代,華夏大地上有沒有積極主動、願意主動出擊,捍衛自己的內生的人格與理想、護國護民的真英雄呢?
其實也是有的。但你會發現特別奇怪,這種人在那個時代總是被精準的排擠到明朝那套體制的外圍、被重重壓抑着。
比如壯懷激烈、南明史上唯一真夠格當皇帝的隆武帝朱聿鍵。

明末亂世中因為主動募兵勤王,他居然被崇禎廢為庶人,派錦衣衛把其關進鳳陽皇室監獄,苦熬了七年,直到崇禎上吊才勉強撿回一條命。
比如縱橫數省、兩厥名王、打的清廷聞風喪膽的大將軍李定國。

作為南明史上不可多得的將才,出身居然是「反賊」張獻忠的義子乾兒,如果不是明朝馬上要亡天下,根本不可能給他「反正」的機會。
再比如一度兵臨南京城下,後又收復台灣的「民族英雄」鄭成功。

他爹鄭芝龍是個常年與朝廷為敵的大海盜,也是在明朝快不行了的時候才被勉強收編。
而鄭氏集團高層除了鄭成功一人似有志匡扶社稷,他爹他兒子他叔他侄……所有其他人,都是一幫只求「把鄭家家業做大」的精緻利己者。
不難發現,以上種種「主動型人格」的人,在明朝體制還能正常運轉時,都是體制想要限制、鎮壓乃至剿滅的「反體制者」。而當這個體制本身無法自保,必須將他們招安、引他們走向舞台中央的時候——非常悲劇的是,時間已經不夠這些英雄長成羽翼,挺身抗暴了。
更讓人感到喟嘆的,是即便明朝這個體制已經朝不保夕,它依然將打壓、敵視自身內部的「主動型人格」者作為其第一要務。弘光朝廷的「借虜平寇」、魯監國與隆武帝的正統之爭,都是這種打壓思維的表現。當然最狗血、最讓人喟嘆的,還是逼反孫可望的操作——同樣作為一個舊體制邊緣的「主動型人格」者,孫可望確實是個人才,只不過跟其干兄弟李定國不一樣,他有更多的私心,想讓朝廷封自己個秦王噹噹。按說此時的明王朝,土地都丟的幾乎只剩廣西和雲南了,你就是痛快的封孫可望個秦王又能怎麼樣?可是不行,明朝的皇權從朱元璋那會兒開始,就是葛朗台般極端吝嗇、拒絕分享的。你一個老西營、臭土匪出身,也配姓趙?啊不,也配封一字王?給你個兩字王算頂天了!不僅如此,我還要猜忌你,提防你,用皇權的那套「馭臣術」離間你和你兄弟,結果硬生生把這個主動的能臣逼成了貳臣。
說到底,南明的速亡,其實亡於明朝一種主動篩選機制的過於成功——這種篩選總是把被動應命的人挑出它的體系,而將積極主動的人才排擠出去。
為什麼會這樣,這個憋屈的體系是怎麼形成的?
3
在顧誠先生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南明的病根,其實在明王朝建立之初就落下了。
兩百多年前,當朱元璋奪得天下後,這位權力欲極強的皇帝,為了讓子孫世世代代坐穩江山,訂立了一套非常不近情理的「祖宗之法」,他鼓勵、甚至強行要求他的臣子、百姓們必須「忠君愛國」,且這種「忠」和「愛」的方式,必須由他自己來定義,臣子百姓在這個體系中只是被動接受的客體,你們沒有主動發揮的權利,遵旨辦理就可以了。

中國儒家思想十分強調「忠君愛國」,但至少在孔子和孟子的時代,這種「忠」和「愛」是有條件的,允許臣與子保留自己的判斷力和主動性。
比如說孔子雖然曾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意思原本很可能是「只有君有了君當有的樣子,臣才能相對的有臣該有的樣子。」強調君臣義務的對應性。
孟子在這一點上就做了集中闡發,他闡述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強調君主只有愛民才能要求臣民忠誠,如果君主不把臣民當人看,臣民則有權利推翻他——這就是強調臣與子對君與父的愛,應該是活潑、主動、有自己判斷的。
可是這樣的闡述,讓權力狂朱元璋非常惱火,他不允許臣子對他的忠誠是講條件的——君主賢明你們就愛,不賢明你們就不愛,萬一我子孫後代有個「不賢」的,豈不是反天了嗎?
所以朱元璋要壟斷對忠孝的定義,他將孟子移出孔廟,還下令刪除《孟子》中不合時宜的章節和言論,比如《盡心篇》中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萬章篇》中的:「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以及《離婁》篇中的:「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等等等等……
而朱元璋對明朝臣民的設計也完全是「被動式」的。在朝堂,取仕的八股完全是代聖人(實則是皇帝)立言,官員的一舉一動全在錦衣衛的監控下。而在民間,老百姓沒有路引就不能出縣,甚至所從事的各個職業也必須代代相傳,你在明朝初年掏大糞,到了明朝末年你第N代孫理論上說也必須掏大糞,不考公務員(科舉)就沒有換工作的指望。
這個被動式的體系,經由他兒子明成祖朱棣的進一步改良,變得更為變態而令人訝異——如果說朱元璋是把臣民都當成了植物,栽在地里不許動窩,那麼靠靖難之役上位的朱棣,就是把皇親國戚也當成豬來圈養。厚其祿而削其權,圈在地方王府里,除了生孩子,什麼也不許你干。朱姓皇族們只有在王府里吃飯睡覺玩女人作威作福的作惡權,想干點利國利民的實事,基本門都沒有。
所有這些動作,都是為了最大限度的打壓、削弱除皇帝以外所有人的主動性,然後再通過帝國體系對臣民進行反覆的、填鴨式的忠君愛國教育。
明代這一點做的確實是非常成功的,一直到明末,帝國舞台中央所剩下的都是一群沒有自己主見、只能循規蹈矩、一切循規辦事的「被動型人格者」,「主動型人格」的人則被排擠、被圈禁甚至被逼反,遊蕩在社會邊緣。而這個被動型社會因為不斷接受皇權的要求,應激性的不斷做出「忠君愛國」的反饋,看似民氣十分可用。
但問題在於,這種馴化過於成功了。
當突然有一天,皇帝在煤山上上吊了,那個強行要求臣民們該怎麼忠君、怎麼愛國的「主人」不存在了,於是進入了一種「天下失主」的狀態。這個時候人們才發現,由於皇權有意選拔了太多「被動性官僚」在自己周邊,擁有「主動型人格」的人在天下巨變中有沒有足夠的時間進入中心,進入了也不會怎樣完成權力的分割與妥協。這個民族進入了一種茫然無措、束手待斃的可恥狀態。最終在外族的入侵中亡國、亡天下。
所以,南明之亡,是誰之過呢?
冶金學上有個專業詞彙,叫「金屬疲勞」,指金屬構件在外力的不斷扭曲下內部不斷積累損傷,最終發生脆斷。
我想,其實南明的故事,也是一個「金屬疲勞」的故事,在孔孟時代,中國人曾有一種活潑的、主動的、堅韌的忠愛本能,但終明一代,皇權不斷的在用強力反覆扭曲、彎折這個本能,皇權告訴你,這樣忠,必須這樣愛。最終,就像被扭曲、彎折了無數次的軸承一樣,這種「忠君愛國」的精神,在最需要其發揮作用時脆斷了,在外族的鐵蹄與屠刀面前,億萬萬人齊束手,竟無一個是男兒。
這,就是顧誠先生的《南明史》為我們講述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