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寫了兩部巨著:《美國的民主》與《舊制度與大革命》。這兩本書都從只提問題開始,結果勾勒出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民族的畫像,儘管這兩個民族在某種意義上註定會有共同的命運。
法國和美國都沒有避開把近代社會捲入民主制的不可抵抗的運動。「平等的逐漸發展是符合天意的事實。它有符合天意的主要特徵;它是普遍的、持久的;它每天都在避開人類的權力,一切事件和一切人都在促進平等的發展。」
民主制是我們時代的宿命或天意,但是,它在政治領域中給各種體制都留下了餘地,尤其是它不在自由和專制之間作出決斷。某些民主社會現在是或將來是自由的,另一些則相反,是奴隸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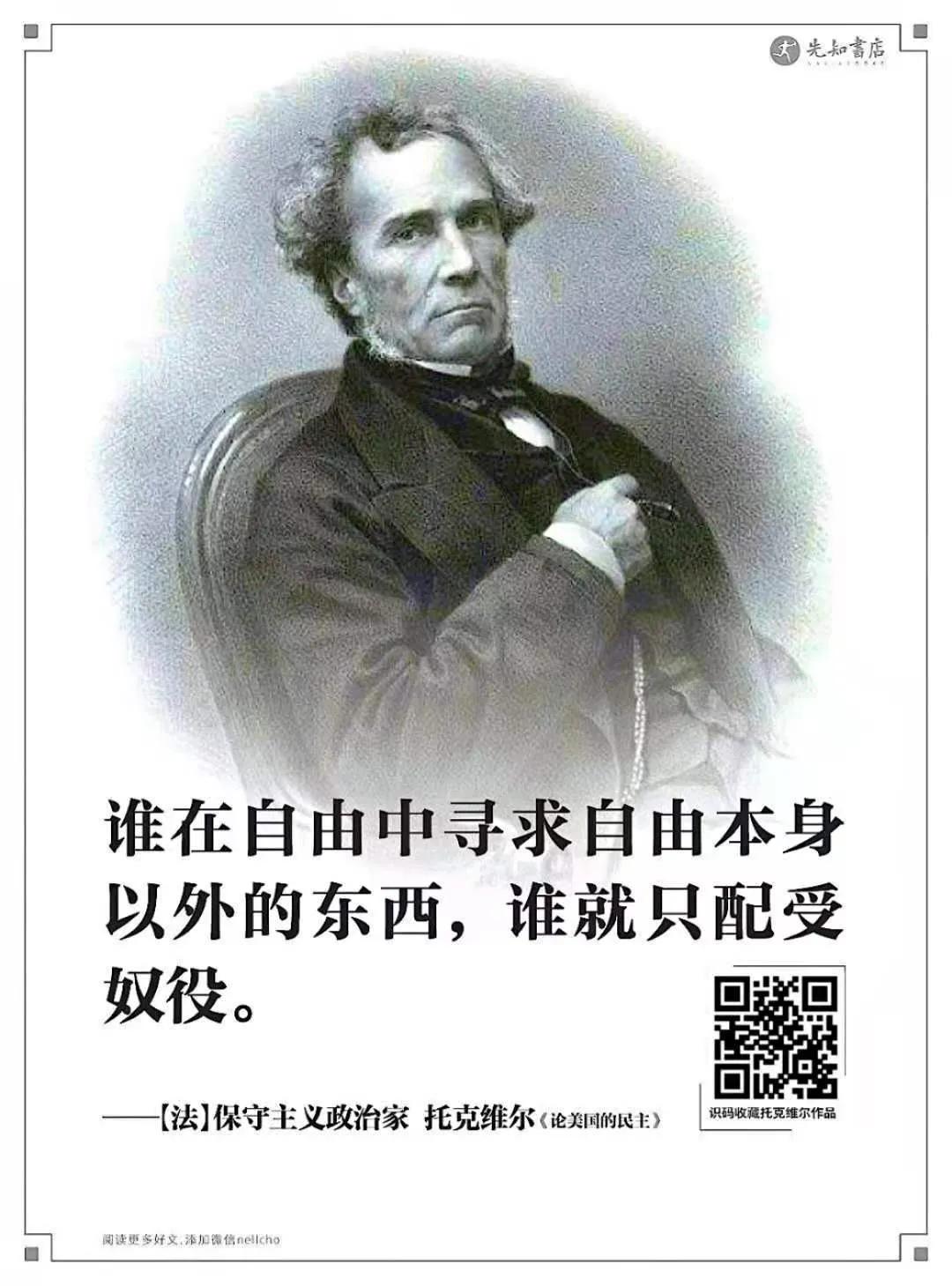
▌托克維爾的問題既是歷史的,又是永恆的
在美國,托克維爾並不只是一位只觀察他人風尚習俗的旅行者。作為一位社會學家,他想同時描繪一個獨一無二的共同體,弄懂大西洋兩岸新舊大陸共同的民主傾向藉以表現自己的特點。
在研究舊制度時,他並不只想用孟德斯鳩弟子的方法去使各類事件能夠被理解,而是盡力領會和解釋法國的歷史過程,他認為法國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進入了民主時代。美國的特點決定合眾共和國具有自由的素質。歷史的進程不但在現在,並在將來繼續使法國面臨着專制主義的危險。
於是,我稱之為托克維爾的「獨一無二的問題」就出現了。柏格森寫過,每一位大哲學家都以一個觀念或一種看法,作為自己學說的啟示和中心,他的所有著作都構思着這一觀念,但都沒有全部說盡它的意義。
也許政治哲學家不大從一種直覺,而更多地從一種疑問出發。我認為,政治在本質上是有疑問的,幾乎是矛盾的。
馬基雅維利假裝幼稚,提出了一個人們在以後幾個世紀不斷思考和研究的問題:既然政治是行動,效益是行動的法則,人們怎麼能以道德和宗教的名義拒絕有效但可怕的手段呢?
如果一位新君主奪取了政權,如果他饒恕了舊統治家族中一個孩子的性命,他就增加了遭到反抗的危險。不論他哪一天成為他應該清除的那個人的犧牲品,這種時來運轉的責任全在於他自己,因為他不發慈悲本來是可以避免這件事情的。
自然,這樣提出政治問題沒有明顯的說服力。也許應尋求什麼是最好的政府,或在什麼條件下權威是合法的,而不是講那些應當用權宜之計來對付的極端情況。換言之,哲學家一開始構思的問題其意義本身就是成問題的。
激進主義的問題,或者應當說他對醜行表示的義憤,來自於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的集體財富的增長和群眾的貧困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他對資本主義所作的解釋的中心,也是他的人類歷史觀甚至宇宙觀的中心。
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要通過一個既悲壯又有諷刺意義的辯證過程,他們只有經過不可調和的鬥爭才能獲得自己勞動的利益。資本家本身是革命的,他們在進行創造的同時就為自己的毀滅作好了準備。現代社會特有的對立達到了暴力的頂點,因為它醞釀着一切對立的結束。
馬基雅維利的疑問是永恆的,所以馬基雅弗維主義世代相傳,只是某些方面有所更新,本質不變。
如果激進主義的問題限於生產力發展和群眾貧困化的對立上,那它就只與一個歷史階段有聯繫。如果它表示了對社會矛盾的反抗和對一個無矛盾社會的嚮往,那麼它也是永恆的。
我覺得,和激進主義的問題一樣,托克維爾的問題既是歷史的,又是永恆的。說其是歷史的,是因為思想家本人把它與現代社會民主化的明顯事實聯繫在一起。說其是永恆的,是因為它使我們面臨着平等和自由的矛盾或協調。
以平等為最高理想的社會能否是自由的社會?社會在什麼意義上和在什麼程度上可以平等地對待天性不同的個人?

▌托克維爾最喜歡用的詞是自由,他的思想沒有什麼曖昧含糊之處
托克維爾的語彙是難以捉摸的。我只舉一段話為證。這段話引自《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二卷:
最能引起思想混亂的是人們對下列這些詞的使用:民主制國家、民主制度、民主統治。只要人們還沒有明確地確定它們的意義並就這些定義取得一致,人們就將生活在錯綜複雜的思想混亂之中,結果大大有利於蠱惑人心的政客和獨裁者。
人們會說一個由專制君主統治的國家是一種民主制國家,因為他通過法律或在有利於人民生存的制度中進行統治。他的統治將是一種民主統治。它將構成一個民主的君主制。
然而,根據民主制國家、君主制度和民主統治這些詞的真正意義,它們只能說明一件事情,即人民或多或少地參與其統治的政府。它的意義與政治自由的思想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根據這些詞的本意,把民主統治這一修飾語賦予一個沒有政治自由的政府,是顯而易見的謬誤。使人們接受這些虛假的、至少是曖昧的說法的原因有:
一、希望在群眾中造成幻覺,民主統治一詞對群眾總是有這種效用的;
二、無法用一個詞來表示這樣一種相當複雜的觀念,如一個政府是集權的,民眾絲毫不參與公共事務,但置身民眾之上的階級不享有任何特權,法律的制定也是盡力有利於民眾的福利的。
我們上面引證的這段話表明,托克維爾沒有徹底與民主一詞的傳統用法決裂。民主一詞傳統上指的是一種統治方式。
這段話還表明,在他眼中用在統治一詞上的民主的這個形容詞要求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當托克維爾提到民主專制主義時,他考慮的是可能在民主的民族中出現的專制主義,他並不想把民主的尊嚴賦予一種專制主義。因為,作為統治方式,專制主義是民主的對立物。
托克維爾沒有明確區分社會狀態和統治方式。我們剛才引用的那段文字的最後幾行字又使這個模稜兩可的態度增加了一些複雜的因素。
在民主社會中,一切制度都打着民主的旗號,因為這個詞在群眾中是頗得人心的,因為甚至專制主義也促進大多數人的福利,而沒有構成貴族的特權。用現代的語言來講,我就會說平等社會中的統治者所援引的合法性始終是民主的(人民主權)。
法西斯主義者自稱為民族意志的解釋人,國社黨人自稱為種族意志的解釋人,共產主義者自稱為無產階級意志的解釋人。甚至恢復了權力原則的各個政黨也聲明他們的權力來自所有的人、來自民族、種族或階級。
讓我們總結一下這個初步的分析。根據托克維爾的看法,民主首先是一種社會事實,即地位平等。在政治範圍中,這一事實的正常表現是人民主權和公民參與公共事務。
在經濟領域中,儘管它不要求結束財富的不平等狀況,但它卻引出了窮人對財富分配的反抗,有助於正常地促進不平等的縮小。然而,民主社會並不一定就是自由的。
托克維爾最喜歡用的詞是自由。但這個詞並沒有得到多少明確的說明。然而,我卻覺得他的思想沒有什麼曖昧含糊之處。

▌一個社會要成為自由的社會,就必須擁有自由的人
托克維爾繼承了孟德斯鳩的思想,他認為自由首先是用來指法律保護下的每個人的安全。享有自由,就是不受權勢者或權威的專橫行為的侵害。這種不受專橫行為侵害的範圍應當延伸到少數人身上,並應禁止人們濫用自己的權力。
毫無疑問,托克維爾可能贊同孟德斯鳩的這一名言(《論法的精神》第十一章第二節):「還有一點:在民主的國家裏,人民仿佛是願意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因此人們便認為這種政體有自由,而把人民的權力同人民的自由混淆了起來。」還有:「政治自由絲毫不是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第十一章第三節)
法律的統治和尊重法律是自由的首要條件,但這不是自由的全部意義。還必須由人民自己來為法律的制定作出貢獻。能不能說,政治自由與被統治者參與制定法律和管理事務的活動有直接的比例關係。
因此托克維爾腦子裏充滿了行政與代議對立的觀念,相信國家職能的擴大和集中最終會給自由帶來致命的打擊。
平等和自治這兩個思想也許還不足以完整地確定自由的定義。一個社會要成為自由的社會,就必須擁有自由的人。
「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脫金錢崇拜和雞毛蒜皮的瑣事,使他們每時每刻都看到和感到在他們之上和身旁的祖國,只有自由能隨時用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代替對舒適的愛慕,使人們的雄心轉向比獲取財富更偉大的目標,放射出能使人看清和判斷人類的罪惡和美德的光芒。」(《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維爾為貴族被「打倒、根除」而不是「折服於法律」感到遺憾,而貴族恰恰是受自由精神鼓舞的。

此外,「必須避免用人們對最高權力的服從程度來評價人的卑下,因為這是一種錯誤的尺度。不論舊制度下的人怎樣服從國王的意志,也還存在着一種他們不知道的服從,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服從一種非法的或受到異議的權力。人們不尊重,而且常常蔑視這個政權,但人們寧願忍受它,因為它既能提供服務又能帶來危害。他們對那種有失尊嚴的奴役形式總是陌生的。」
後面還寫到:「對他們說來,服從的最大禍害是強制;對我們來說則是微不足道的了。最大的禍害在使人服從的奴隸性之中。」
托克維爾在內心中是一位貴族,他不厭惡地位平等,但懼怕使人服從的奴隸性。他害怕對舒適的專心致志,會在獨自操持庸俗小事的人們中傳播這種卑賤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