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淄博市羅村鎮千峪村,從出生到上中學,我一直生活在這個村里。「80後、大學擴招、畢業即失業、農村到城市、重男輕女、北漂、離婚、單身媽媽、海外定居……」這些關鍵詞都可以跟我無縫銜接。
我的童年記憶里,有着農耕文化的所有印記。沒有公路,沒有電燈,沒有電視。

我出生的小山村,一個鄰居拍的照片。
腦補一下這樣一種生活:沒有自來水,生活飲用水要到村里一個露天大水窪里去挑,夏天水上面漂浮着一層綠毛,冬天挑水的入口處冰凍三尺,不小心就會溜跟頭;沒有廁所,白天在豬圈如廁,晚上在屋裏用桶方便;收割莊稼靠手,小麥用鐮刀來割,玉米要一個一個掰下來,用手推車拉回家。
女孩讀書沒用的觀念深入人心,我每天回家都要把家務做完才可以寫作業;上學的教室也是簡陋到可怕,夏天下雨,學生們要不斷地挪動桌子防止房頂漏下來的雨水把課本打濕,冬天,學生要輪流從家裏拿玉米棒去教室里生火。

四歲時的照片,在當時住的院子裏。
那些生活的日常,今天翻出來看,居然感覺自己活得像原始人一樣:原始,真實,粗糙,自然,稀罕。我不覺得是苦難,反而覺得那是我的根,是我發芽出土的地方,是我的起點。
1995年,我上初二。這一年,當煤礦工人的爸爸從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城鎮戶口),全家人從農村搬到爸爸工作的礦區。而之前在農村的那些玩伴們,現在大部分都依然生活在農村,能讀到高中的都屈指可數。

這是我們搬到礦區後的家,我的父母現在還住在這裏,是我2017年回國時拍的。
1996年中考,我落榜了,或許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絕望,我第一次體會到把自己命運捏在手裏的感覺。
比那些考過分數線的同學,我要多交4000元才可以有資格去讀。1996年的4000塊是一筆很大的花銷。父母沒有錢。我跟媽媽一起去親戚家借錢。借來的4000元,媽媽用手帕包着,放在我面前。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那麼多的錢,內心充滿了愧疚。

高中時,我在我的座位上。
我天生愚笨,性格懦弱。三年高中,像一個陀螺一樣的,一方面被老師領着往前走,另外一方面被內心那種罪孽深重拖着讓自己「戴罪立功」。我的數學不好,其他文科科目都名列前茅。
高考後,我的分數線只過了大學專科線。選擇院校就像抓鬮一樣,拿着厚厚的一本志願選擇指南,我不知道要選擇哪個學校,哪個專業。我從來沒有離開過生活的縣城,礦區,哪裏知道外面的世界?志願選擇指南上那些省市,對我來說就是名詞,連距離的概念都沒有。正常的三個志願,我都填了山東省內的學校。當時想着提前志願也別空着,隨便填一個吧,我在隨便翻到的一頁的左下角,看到「北京物資學院英語類」,就填了。
結果陰差陽錯地考到了北京物資學院,更是稀里糊塗地讀了英語專業。
到北京讀書,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拿着大學錄取通知,可以買半價票,票價是24元。1999年,在綠皮火車上晃蕩了12個小時後,我土裏土氣地到了北京,那一年,我正好18歲。

1999年,建國50周年時,我在北京拍的照片。穿的是離家時我媽找裁縫給我做的衣服,也是我最好的衣服。
還記得大一暑假過後返回北京的那個下午。從北京站到通州,經過長安街,雙向10個車道的寬闊,讓剛剛從逼仄的礦區中返程的我,感受到的不僅是視覺的衝擊,更是激發了我對美好的嚮往。那一刻,有個聲音說:我屬於這裏,我要一直留在北京。
2001年,大專畢業,國家早已開始了大學擴招。有很多同學選擇專升本,學費要5000元。而父母已經無法再負擔我讀書的費用。我沒有夢想,沒有規劃,只想留在北京。那時候BP機是找工作的必需品,把個人信息登到一份免費的報紙上,BP機上會不時收到面試信息。
第一份工作,2001年6月份,某政府機關辦事處。面對一屋子的面試官和應試者,我居然「脫穎而出」,被錄用了!
開始工作,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撥號上網,那是我第一次接觸網絡。基本不會打字,敲半天才能敲出幾行字。發傳真,不會用傳真機,複印文件,不會用複印機。領導讓我翻譯做書面英語翻譯,我一塌糊塗。學校里學的和工作中的英語完全是兩回事,日常溝通對話、讀英文小說、寫英文日記還可以,真要做書面翻譯,我兩眼一抹黑。
一個星期後,我被開除。領導看我可憐,發了我一個半月的工資,2000塊,對於當時的我,是一筆巨款。

2001年初,我在大學裏操場上拍的照片。
萬幸,7月份,我又被某製藥公司的北京辦事處錄用為行政人員,包住宿,月工資600元。日常的工作包括買菜、打掃衛生、遛老闆養的狗。我天生怕狗,或許那狗也感受到我不喜歡它,總是無緣無故攻擊我,我卻不敢反擊,在那個環境下,那隻狗要比我金貴的多。
工作了兩周就莫名其妙被解僱了,拿了50塊錢工資,老闆要求我當天把所有的行李搬走。那天是2001年7月13日,全國上下都沉浸在中國申奧成功的喜悅中,而我,還沒來得及開始構建自己的夢,就一個大跟頭,摔了個四腳朝天。
我打包好行李,在同學宿舍的地板上睡了兩天。第三天,同學說,「我們這裏的水電都是要交錢的。」我聽出了畫外音,給家裏打電話,終於撐不住了,「媽,我想回家。」是真的在北京無處容身了嗎?是找不到工作了嗎?不知道,沒有計劃,沒有目標,一切都是本能驅動。

走投無路,離開北京時在北京火車站,當時的男友幫我拍的。
回到家後,沒有安慰和溫暖。爸爸邊抽煙邊嘆氣:「這大學是白念了,錢都打水漂了,連個工作都找不到。」弟弟說:「還大學畢業生呢,都不如我上技校掙得多。」我說:「我肯定能一個月賺到1000塊。」我媽說:「自己不知道扒幾碗乾飯?你吹牛皮啊?」
我在紡織工廠當過工人,沒多久,工廠發不出工資,面臨倒閉。又去了另一個效益好的大工廠,月薪400塊,培訓完後,要求上繳畢業證書並把戶口遷到工廠。我覺得自己不能被禁錮在那裏,待了一周後又跑了。
後來被一個賣兒童英語教材的銷售組織錄用。在那裏,每天早上和晚上一定要大聲唱歌,呼喊:「我能行,我一定做得到,我是最棒的。「每個銷售人員都着裝靚麗才可以去大街上推銷。一套教材是7000多元,即使放到現在也有點離譜,何況是20年前的小縣城。

這段「流亡」期間,我做過幾天英語老師,這是我給培訓教室設計的背景牆。
晃蕩了半年,在那樣顛沛流離的狀態下,我居然完好無損地生存下來,沒有步入歧途,沒有自暴自棄。這期間,一直靠第一份工作施捨給我的2000塊生活。在存款還剩一百塊的時候,心中突然萌生出一個想法:我得回北京,再不回去,就沒有錢買火車票了!2001年12月份,聖誕節前夕,買完火車票,還剩30塊。
我拿了幾件換洗的衣服,偷偷地跑回了北京,它徹底打消了我所有的退路,家是回不去的,我承受不了父母的嘆息。就是要死也得死在北京,不混出個樣來,不回家。
回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文秘,月薪800塊。從我住的郊區到工作地點,每天往返要5-6個小時。說是文秘,其實也是半個保姆,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中午去給老闆買菜做飯。雖然月薪才800塊,我居然存了錢,工作2個月就給父母買了第一台彩色電視機,或許是太急於在他們面前證明自己了。這份工作做了3個月,試用期過後老闆給漲薪到1000塊,但我在北京已經安頓下來,想要去找更好的發展,所以辭職了。
當時我基本每年換一份工作,幾乎所有工作平時的書面溝通都是全英文,我的書面英語能力也在日常工作中慢慢提高。不知道要做什麼,只要這份工作比我前一份工作賺的多,我就換,薪水是找工作唯一的衡量標尺。

2003年的照片,我跟別人合租,終於有了自己單獨的房間,家具家電都是從當地的二手市場淘來的。
沒有大夢想,只有三步之內的小目標:從與別人合租一個房間,到有單獨的房間;從只能買路邊攤的衣服到可以買超市的衣服;第一年工作,過年回家給父母買了彩色電視,之後的一年又給家裏換了沙發……同時,也在父母面前找到自尊,證明他們讓我上大學不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從2001年底到2006年,和無數的北漂一族一樣,我住在郊區,到市區去上班。沒有生活,只有工作,兩點一線。又和很多北漂不一樣,因為我把北京當成家,覺得自己本該屬於這個地方,回到山東父母生活的礦區,反而覺得自己像個異客。
每天上下班在國貿橋下等公交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仰望着國貿大廈,想着哪天我一定要在裏面工作。像王爾德所說,「我們雖然都生活在陰溝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而那時候,眼前的國貿大廈就是我的星空。

2003年,工作時的照片。
2002年春節過後,面試了一家香港的展覽公司,全程英文,我通過了面試,月薪1700塊。結束面試,第一件事就是找公用電話,打給父母,告訴他們我不僅掙到1000塊,而且公司還給我上保險。在打電話要按分鐘收費的年代,我無法知道他們知道這個消息的感受,我猜他們應該是驚訝的。
在這家公司期間,有位同事離職,這麼好的工作怎麼還會要離開?我特別驚訝。我從來沒有規劃,因為此刻已是人生的最高點,實在沒有能力和想像力去憧憬未來。我以為自己會在那裏一直做下去,但其實只在那裏做了一年半就離開了。後來又陸陸續續換了幾份工作,每份工作都比上一份薪水更多。

2004年10月份,我去香港參加展會時的照片。
2005年,去了一家外資媒體公司,見識了很多大場面,還有很多名人。工作地點是在國貿對面的SOHO現代城,離國貿大廈,還有一步之遙。2006年,我應聘到目前就職的公司,辦公室在國貿大廈。應聘這個職位的每一位候選人都比我厲害,有的是海外留學,有的是知名院校碩士,而我只是二流大學的大專。
當我真正坐在國貿大廈的辦公室里時,多了一份和別人不一樣的滿足,那是願望達成一樣的夢境。

2014年,我坐在北京國貿的辦公室里。
工作基本穩定後,父母的催婚讓我無處可躲。我和前夫婚戀網站認識。前夫溫文爾雅、學識淵博,還是北京戶口,有房有車,這似乎是上天對我多年北漂的嘉賞,給了我一個不用太拼搏就很安穩舒適的家。按部就班,我們熱戀時就結婚了,結婚第二個月就懷孕了,現在想來真的是無知者無畏,甚至兩個人都沒有經歷磨合期。
由於工作關係,接觸到了北京各大高校的MBA。我萌生了想繼續讀書的想法,至少得有個拿得出的學位,這是我在北京活下來後的第一個計劃。婚禮結束後三個月,我就進入到MBA的學習中。2009年的那個冬天,我挺着個大肚子,每個周二下午下班後,從北京東三環坐地鐵去北四環中科院MBA管理學院,上課到晚上10點多,再從學校回到北京西四環的住處。而前夫的工作只能每個月回北京一次。整個懷孕階段幾乎都是我一個人。

我的MBA畢業照,但那時我的工作已經穩定了,讀完MBA對我的職業發展目前尚未有什麼幫助。
後來前夫辭了職,整天沉浸在遊戲中,我們又從與公婆合住的房子裏搬了出來。我一個人工作,擔負着租房和一切家用。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有了離婚的想法。不是背叛婚姻,是想逃跑,覺得自己快要死掉了。只有離開這一切,才能活下去,離開是求生的本能。
在女兒過完三歲生日一個星期後,2013年3月9號,我們走進民政局,協議離婚。

這是離婚後我朋友圈的狀態,女兒成了我的全部。
原本以為離婚是個動作,是個瞬間,後來才知道,離婚是個漫長且痛苦的過程。就像長在樹幹上的一節枯樹枝,樹枝不是一天變枯的,而要在這節死去的枯樹枝上再長出新的枝丫,不知道要再經歷多少個日日夜夜。

離婚後,我拍了個人寫真,來記錄當時的樣子。
很多朋友說,你真能幹,自己一個人既要上班,又要帶孩子。但是他們哪裏知道,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品得到,相比生活上的辛苦、經濟上的拮据,更苦的是女兒跟我要爸爸,我卻給不出。隨着女兒一點點長大,看到別人的爸爸,她卻連爸爸的影子都看不到。

和女兒的生活,女兒在廚房做早餐。
朋友看我一個人騎自行車帶着孩子,建議我買個車,而買車需要先搖號,我就稀里糊塗註冊了,沒想到第二個月居然就被搖中!這是在2013年10月份,離婚半年後,也是我好運的開始。命運不會虧待一個認真生活的人,這一切在我離婚後得到了最好的驗證。

這是中籤時我在朋友圈發的狀態,由此開始了我開掛的人生。
以前從未想過能在北京買房。結婚時,住在婆婆早年買的房子裏,妄以為她兒子的家就是我的。在離婚半年後,我居然買房了。離婚,我是淨身出戶,帶着一車行李和女兒,沒有一分錢。自己買房,又是一次無知者無畏的大膽行為。
2013年7月27日,一個炎熱的星期五,本想看房,結果當天就買了,是排了一晚上的隊,從晚上7點排到第二天早上9點,那些一起排隊的都是一家人,不斷輪崗,而我,自己找了張報紙,愣是一個人堅持了一宿。買房的首付款基本都是借的,辦公室里的同事,能借的都借了。記得自己有個Excel借款表,記錄着每位朋友的借款金額和借款日期,借了40多萬。

這是排了一宿的隊,發在朋友圈的狀態。
一個人邊工作邊帶娃,雖然日子過得拮据艱難,但是卻沒有了以往的痛苦和糾結。雖然離婚的傷疤還在那裏,我也會像一個怨婦一樣數落前夫和婆婆的行為,但是內心卻平靜了許多,對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掌控感。

這是在買的新房子的小區里,自己一個人帶着女兒生活。
2014年10月份,我正考慮女兒上小學的事情,在一個星期四下午,突然收到人力資源部的電話,老闆們要和我開會。開會的內容是,我這個工作職位要被調到國外,問我是否願意去?思考再三,我決定離開漂了15年的北京,就像當年從山東義無反顧地來到北京一樣,把過往都扔到身後,踩到腳下,給自己再一次的進行復盤結算。
出國前的那個春節,我回家跟父母一起過。在家期間,我和老闆電話溝通相關事項。聽到爸媽悄悄在說:「聽嘰里呱啦的,英語說得那麼溜,厲害啊,一般人可做不到。
原本以為這麼多年,自己早已無數次、無數倍地找回了自尊,再無需任何人的肯定和證明。但是當無意中聽到父母的這句肯定,卻依然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心裏有個聲音,「我做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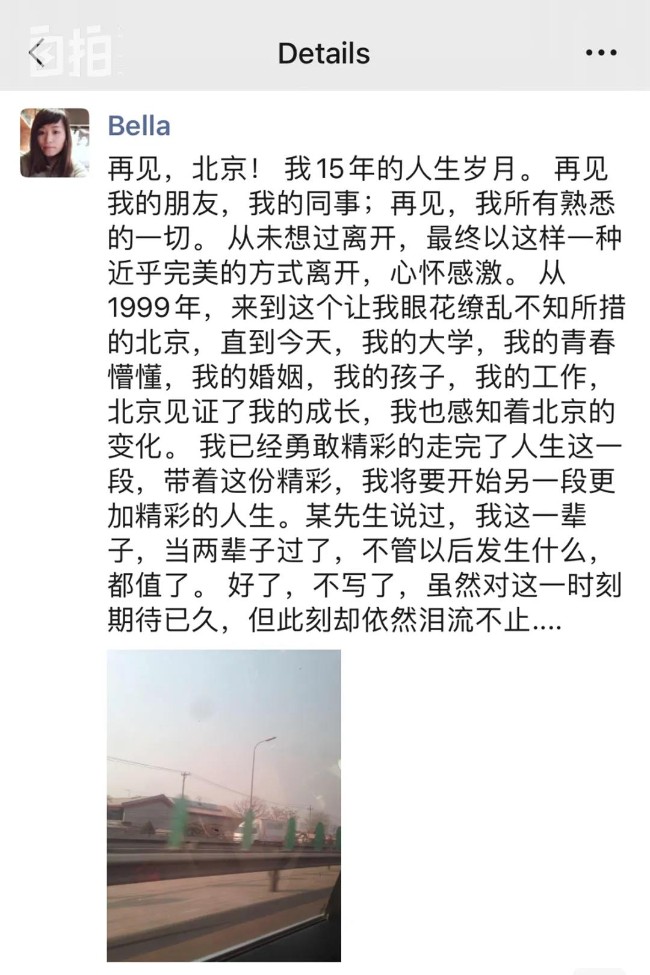
這是當時去機場路上發的朋友圈狀態。
在女兒過完五歲生日後,除了房子,我處理了在北京的所有家當,拉着兩個行李箱,抱着女兒,踏上了澳洲的土地。就這樣,把我過往三十多年的生活經驗一點點塗抹清零復盤,把饅頭、大餅、油條切換成這個世界裏的toast, roll, pasta。

悉尼CBD,我的辦公室從北京的國貿大廈到了悉尼歌劇院旁邊的大廈里。
記不清楚多少次,或者是剛到辦公室坐下,或者是在開會,或者就是在工作,收到老師的電話。狀況百出,有時候是因為哭得太厲害,老師根本無法上課,被老師送到校長辦公室,有時候是在教室大鬧,躺在地上打滾,誰也碰不得,誰哄就踢誰。

女兒上學2個月後,給我做的母親節卡片。
大概半年後,2015年10月份左右,女兒才慢慢安靜下來。有一天我下班去託管班接她,老師說,今天你女兒跟我說話了,叫我的名字了。我抱着寶貝女兒,沒有人知道我有多高興。

悉尼歌劇院,就在我的辦公室附近,我中午散步的地方。
這些年,公司內部經過幾次併購重組,我作為元老員工,接連不斷地在在股票分紅中受益,還清了我北京買房時的欠款。公司被納斯達克上市公司併購,我兌現所有公司股票,用所得的部分在悉尼市區買下了一個地段非常好的公寓。
而我,剛進入這家公司時,財務行政占我工作的60%,其它的跟項目相關的數據工作佔40%。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在工作中找機會學習,現在被提升為高級數據分析師,開始獨立管理和運營一些大型項目。

我和女兒在家附近散步,我偷拍的女兒背影。
漸漸地,我走出了離婚的霧靄,心裏沒有了抱怨,也沒有了傷痛。應了那句話,愛的對立面不是恨,而是不在乎。是的,對於前夫,只有滿滿的祝福,祝願他的人生下半場能平穩些。至於我們的關係,也達到了從未有過的平心靜氣,像對待老朋友,又像對家人。

從去年疫情開始,就一直在家裏辦公,這是近期的自拍照。
人生走完上半場,我依然站在風雨飄搖的路上。我從一個落後的山村里走出來,從一個被煤場污染着的礦區走出來,從山東到北京,從一個人飄忽不定到走進一段期望的關係,又從這段讓我掙扎的關係中掙脫出來,從北半球來到南半球,這一路走來,那些令人鼓舞的時刻,幸福的瞬間,那些糾結的痛苦和掙扎的眼淚一起拼湊成了現在的我。

我家附近的小路,從小生活在山村和礦區的我,以前從不知道有這樣的地方存在。
我小心撿起這些散落的碎片,藉由這次回顧自己的時機,仔細地把每一個碎片拼接起來,無需隱藏任何傷疤,因為那是我人生旅途的勳章。
我對自己說:不必仰望別人,自己亦是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