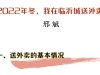外賣行業是按照男性的身體和氣概打造的,為了適應這個行業,阿瀟得付出更多的代價蔣芷毓攝
外賣網絡鋪天蓋地的今天,要見一個騎手,是輕而易舉的事。但要找到一名女騎手,並不容易。要和女騎手約出時間聊天,也不比約見任何一個「996」狀態的打工人簡單。她們是最忙碌的人群之一。
我是在上海的繁華地段見到阿瀟的。彼時是周日,本該是她的休息時間,但為了跑滿每周500單(滿500單單價會漲到8元),她還在送外賣。阿瀟來自湖北,1975年生人,成為一名女騎手已有兩年。每天早上8點出門,夜裏十一二點收工,是她的工作常態。
我提出跟她送一天外賣。為了在中途搭上車,我在商場門口等她送完之前的單子,才坐上她的後座。那是我坐過最驚險的電瓶車,考慮到後座有個人,阿瀟還「放慢了速度」。做騎手後,迄今為止,她已換了三輛電瓶車。這一輛的後視鏡也已經撞壞了,但她並不介意。她說,沒有一個騎手是看紅綠燈的,往往在燈還沒有跳轉時,他們就發動了。有一次,阿瀟停在十字路口,信號燈已轉紅,另一個騎手看她着急,打趣式地伸出雙腿橫在路中間,說:你快走,我幫你攔着。
這是一個男性化的行業。美團研究院最近一次提到女騎手還是2018年,根據當時的調研,女騎手佔比約為8%。外賣行業是按照男性的身體和氣概打造的,為了適應這個行業,阿瀟得付出更多的代價。
阿瀟身量嬌小,身高不到1米6,體重現在瘦到了90多斤,皮膚曬出了小麥色。在不久前加入要求更高的「樂跑」隊伍後,她剪掉了長發。她很少購置衣物,我們見面那天,她穿着紅色的寬大衛衣和淺藍色牛仔哈倫褲。聲音溫和,但有些沙啞。
除了在外形上逐漸「男性化」,阿瀟對自己的身體也有更多限制。每天工作十幾小時,她很少喝水,「上廁所耽誤時間」。她已經46歲,每次經期都疼痛難忍,但她沒有因此休息過。送外賣時,除了風雨無阻地騎車在路上,她的日常,就是在商場、辦公樓和居民樓之間奔跑。
常有男騎手問她,在樂跑,男的都吃不消,一個女的吃得消?而她用實際行動給出了答案。現在的她,每個月能拿到上萬元報酬。而根據美團研究院的報告,2020年上半年,92.6%的騎手月收入在8000元以下。毫無疑問,在這個男性為主體的行業中,阿瀟也是佼佼者。
儘管月收入已接近「白領」,阿瀟仍然過着儉樸的生活。她與其他女騎手、家政工住在上海一個老小區的四人間裏,住架子床,月租850元。大多數時候,她在餐館吃一份10塊或15塊的騎手餐。平常,她去得最多的是地下的樓層:停車場,地下美食廣場。大商場的餐飲,也多在地下。她說自己不喜歡大商場,那裏步行距離長、容易迷路,很難送外賣。
與這個城市裏的大多外來務工女性一樣,阿瀟掙的每一分錢都要往家裏輸送。她捨不得為自己花錢,很少購置衣物,也幾乎沒有娛樂活動。來上海兩年,她只去過迪士尼和海洋館,都是帶女兒去的。以前,她喜歡外出散步,以及吹陶笛,現在則沒有時間。
這並不是她喜歡的生活狀態,但她覺得「沒有辦法」。前幾年離異後,她獨自撫養女兒。過去二十年,她做過紡織女工,當過老師、會計,也做過家政、打字員、推銷員。如今做騎手,是她賺得最多的一份工作。在艱辛的工作和生活中,她依然懷揣着夢想,希望能為自己和女兒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而每一天,穿行在車水馬龍的都市,於車流中穿梭,爭分奪秒地追逐着時間,她也時時會擔心自己:明天,還能不能看到太陽升起?
以下是女騎手阿瀟的自述。
第一天送外賣就賠了700塊錢
2019年,我已經45歲了,經老鄉介紹,從湖北老家到上海做家政。我不太會做菜,太精緻的菜品,我都得拿着手機搜索。那份工作包吃包住5000塊錢,我挺滿意。但後來,聽說騎手可以賺更多,我就去應聘騎手了。
第一天送外賣,我賠了700塊。車子是跟站長借的,電池起碼有五六十斤,我啥都不懂,當時住三樓,根本提不動電池,我就扔到樓下。第二天,電池被人偷走了,我什麼都沒賺,反而賠了站長錢。
每天都出狀況。我花八、九百元買了一輛破舊的二手電瓶車,因為找不到地方,老是超時。站長說,你把這幾條主幹道記下來。有一天送餐到一個工地上,我發現路中間特別光滑,我覺得好奇怪。等我開過去,原來是一塊水泥池,我連人帶車掉裏面,推出來之後身上全是泥巴。
第一個月賠了兩三千。第二個月,我又老是被罰錢。因為害怕超時,老是手抖,我經常提前點送達。被平台監控到,點一單,我要被罰500塊,站長的星級要降一級,可能被罰3萬塊。他的損失很大,同事經常說,「站長被你氣得要跳樓」。
我跑過眾包、專送,現在在樂跑。相比眾包,樂跑的單子好、單價高,要求也高。很多人想進樂跑,但每個隊人數控制在二十多人。現在我們每個星期都踢三個人,再招三個人。被踢的都是被投訴,或者單量不夠。
我上周不知道被誰投訴過,隊長跟我說,站長點名要開除我,但他保住了。「這裏不是給你養老的地方,跑不了下星期不要幹了」,聽站長這麼在群里說,我們都嚇死了,拼命跑單。
我現在每天能跑80單。跑得越多單價越高,一周跑到500單的話,每單能有8塊。樂跑每天都要求一定的出工時長,時長沒有掛夠,就會被開除。每個騎手每天必須要跑滿三個時段,時段可以選擇。早班是7:00~10:30,10:30~13:30是午高峰。午高峰單量最多,所有人都必須跑。下午茶有兩個時段供選擇,1:30~3:30,3:30~5:30。晚高峰是17:30~20:30,也是必選的。
我選的是3:30開始的下午茶時段,每天早上10點半開工。但要想跑滿80單,基本上8點半就出門,晚上十一二點結束。我以前還會去江邊吹吹陶笛,現在連做飯時間都沒有了。前段時間剪了短髮,就為了這個工作。我經常碰到男騎手,聽說我在樂跑,人家說,男的都吃不消,一個女的吃得消?我們隊裏只有兩個女騎手。
平時我從來不帶水,上廁所耽誤時間,很少喝水。如果碰上經期,就更麻煩了。我46了,每次經期第一天都很難受,但還是得跑。另一個女騎手是94年的,很高大,也留着短髮,一開始我都不知道她是女生。她也不亂花錢,家裏還有一個弟弟。
第一次見面,她遞給我一根煙,我當時好害羞,臉都紅了,從來沒有人遞過煙給我。
從女工到騎手「這是命運的安排」
干外賣確實很辛苦,但在這個城市裏,我還是得到了很多。我有時回想自己的經歷,覺得這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吧。
我是1975年出生的。老家在湖北的一個縣城。我父親是鎮裏的物理老師,母親在學校食堂幫工,有兩個哥哥。初中畢業後,家裏安排我進了當地一家國營紡織廠,幹了十年。
那時我算是修布工,要把前一車間生產的布修整好,才能出廠。當時每天都有任務,要修多少卷布,班長當天把布分配給你,和她關係好的就分到容易的,干不完就加班。就像作業一樣,每天都有,要一直站在那裏做完。
加班沒有錢。我每周倒班一次,白班是早上8點到下午4點,晚班從下午4點到晚上12點。有時候做不完活,要整整站一天一夜。那是我做過最痛苦的一份工作,當時才十五六歲,都恨不得去自殺了。我覺得人生看不到一點希望。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人活一輩子是為了什麼?我開始想這些問題。
找不到答案。我回家說不想幹了,爸媽說這份工作很難得,別人想進都進不來。實在沒辦法,他們請人吃飯,給我換成了練布工,有機器配合操作,再也不用加班了。有空餘時間之後,我就拼命找書看,有個同學書柜上擺滿了書,《紅與黑》、黑格爾,佛教的、道教的,我都看了一遍,不過現在都快忘光了。
我記得很清楚的一部小說叫《假若明天來臨》,一個命苦的女人做小偷,看到別人家裏很豪華,她說上帝啊,為什麼讓我在這裏做小偷,而她住這麼華麗的房子,為什麼給我這樣的命運。
後來工廠倒閉了,我也遭遇了其它的一些打擊。後來我就去福建打工。在一個餐館認識了我前夫,他們家是農村的,我是城裏的,他可能覺得我條件好一點。我並不在意這些。他會吹笛子,當時給我吹了一首歌,說話也挺幽默的,我覺得還可以,就這麼走到一起。
結婚的時候,我32歲,他23歲,我比他大九歲。跟他結婚前,我做了一個夢,夢到我提着一個夜壺,嫁到深山裏去了。他家是山裏的,夜壺就是業孽,意味着我要吃苦的。
第二年孩子出生,問題也來了。他不帶孩子,只在生產當天用心過。我是剖腹產,生完不能動,他忙碌了一天,給女兒換尿布、沖奶粉。那天他特別累,之後就把他爸媽叫過來,隨之而來的是一大堆矛盾。
孩子出生前十多天,我爸去世了。坐完月子,我媽又診斷出帕金森綜合症,我就帶着孩子回了老家。沒有收入,他出去打工,結果被騙去傳銷。他讓我把家裏的貴重物品賣了,給他寄錢。在那之前,他在我心裏像一根柱子一樣,但那一刻徹底看清他了。我要靠自己獨立起來。後來我就抱着孩子找工作,開始賣治療儀。為了工作,我拜託樓下快80歲的老太太幫我看孩子,我每月800塊錢工資,給她400塊。等我休息的時候,她就把孩子送來餵奶。中午我還要回家一趟,給生病的媽媽做飯。
後來我又做過印染廠的實驗員,三年後,又換到當地的私立學校,教了兩個學期書。我修過師範中專的成人文憑,才謀到這份工作。我沒想過老師的工作是這樣的。第一個學期很輕鬆,到第二個學期,分給我的學生數量多了幾倍,每天改作業、備課,我都要批到深夜才能完成。那段時間把我累壞了。
女兒四五歲時,我提出離婚。和前夫已經很少聯繫,對方很高興地答應了。之後我去民營服裝廠做會計,早上8點上班,下午5點回家,還有午休。很輕鬆,不過沒有五險一金,每月2000塊,每周休息一天。三年後,工廠倒閉了,又不發工資,我和其他職工一起告到勞動局,把薪水討了回來。來上海之前,我做過薪水最高的工作是打字員。我給順豐打寄件地址,一條兩毛錢,一分鐘能打七八十個字,一個月能掙3000塊錢,我做了半年。
為了生活,我還曾在學校門口擺攤,賣壽司。城管很嚴,做了兩年,沒賺到錢。在我快撐不下去的時候,我第一次向前夫開口,讓他給個2000塊錢的學費。他給了,還把孩子接到他老家上過一年學。但那一年,他老說他媽媽生病了,讓我打錢。我不想虧待孩子,又把小孩接了回來。最終,為了孩子,為了生活,我還是來到了上海。
跑外賣兩年換了三輛電瓶車
跑外賣雖然比做家政工辛苦,但我還是更喜歡這份工作,可以看到別人多姿多彩的生活。
送外賣的這兩年,我已換了三輛電瓶車。我被別人撞過。有一次一個騎手從行人路上衝下來,把我車子撞壞了,我的腳也腫很高。但我以為沒多大事,就讓他走了。
我也撞過別人。那天手上掛着9個單子,手機卻突然沒網。我連忙騎車去修手機,原來是欠費。充錢出來後就要超時,我慌慌張張地,在路口撞上一輛轎車。我當時買的一輛新車,杆子都撞歪了。
這份工作是沒有保障的,不交五險一金。壓力大的時候,超時、被差評都提心弔膽。有心態好的同事說,我一點都不擔心,能不能見到明天的太陽都不知道,想那麼遠幹嘛。
我的心態也有變化。剛開始看見交警,心臟都要跳出來。我在一個路口被交警罰了三次,每次50塊。他都化成便衣,藏在人群里。我還被交警追過兩次。他攔下之後,我假裝老老實實地推過去,等他不注意我立馬上車,馬力扭到最大,他差一點就薅到我衣服了。
我希望能改善我們的工作環境,尤其是路權。現在送餐的地方,不設自行車道,去了就面臨罰款,不知道為什麼這樣設計道路,太沒人性。五一新規出台,我們的空間更小。交警限制電池大小,覺得我們跑得慢,事故就能減少。但這並沒有從源頭上解決問題。騎手競爭大,平台增加配送時長,停止無限的激勵,我們的壓力才能減小。
最開始送外賣的時候,爬6樓,我都缺氧。現在身體倒變好了。有時候下雨趕時間,根本來不及穿雨衣。一個單子37分鐘內要送達,時間都是以秒來計算,沒法顧及別的。雨過了又吹乾,我倒是沒感冒過。
送單的酸甜苦辣,我有時會拿筆記本記下。有一次送一箱礦泉水上六樓,也沒法提。等我搬到5樓,男顧客像老爺一樣,站在6樓看着我,我都是一格一格往上挪。還送過大酒店的外賣,有一個醫院的科室,點了七十幾份餐,打包成電視機那麼大的盒子。酒店的人打包好,就扔給我,「你自己拿吧」。我把它推到電梯裏,再拖在車旁邊。沒法運,我只好把箱子拆掉,再一盒盒放到送餐箱裏。
有些店出餐特別慢。有的時候催急了,騎手和商家打起來的都有。我一般都會跟商家、客人好商好量。比如茶百道,前面排幾百個人的單子,等到我肯定超時了。我就打電話給客人,客人等不及自己取消,就沒有我的責任。客人要等的,我就跟他商量,能不能先到他的位置點送達,等做好了再送過去,這樣就不會超時扣錢。客人都挺好說話的。

阿瀟在店門口等餐/蔣芷毓攝
我的後備箱裏,必備的是充電寶、工作服、雨衣。平時我不穿工作服,之前很多商場不讓騎手進,現在好一點了,但是頭盔必須摘下來。就算不穿,工作服也得帶着。美團有「微笑行動」,為了監測是不是本人跑單,有沒有穿工裝,每天都要拍照打卡。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拍照,我都把衣服放後備箱裏。如果沒有工裝、頭盔或者拍照模糊,認證失敗的話要罰500塊錢,還可能被開除。
「女兒給我發短訊:我夢見你s了」
來上海兩年,我只逛過迪士尼和海洋水族館,都是陪女兒去的。女兒第一次來上海,問我,怎麼沒有山呀。我說這裏沒有山,她說沒山的地方沒有靈魂。
大城市有更包容的地方。在這裏,沒人會說一個單身的女人。我的室友和同事,好幾個都是不婚族。相對異性來說,我覺得同性之間的關係更細膩一些,什麼話都可以說。我曾經和那個抽煙的女同事找房子合租,但沒找到合適的。現在住的四人間,850塊錢一個月,包充電,離上班近,很難再找到更好的了。現在我有時候中午回來做飯,更多時候在附近餐館吃10塊一份的騎手餐。

阿瀟經常光顧的一家餐館,10元一份
每天送外賣,和同事的交流很少。平時在路上碰到打個招呼,大多時候在微信上聊兩句。有的同事經驗豐富,了解系統的特點,會給我講一些避免超時的操作。上一次吃飯,我才知道他們男騎手還會去ktv,我們幾個女騎手也開玩笑說,下次我們也去點男模。之前和那個女同事一個月沒聯繫,一天她突然給我發了一張圖片,路上有一個女騎手被撞了,她說以為是我。我就知道她還是關心我的。
我想過讓女兒來上海上學,但是太難了。就算她能過來,我也沒時間照顧。小學她寄宿過,現在不願意,我都是請我哥帶她,每年給他們兩人生活費3萬。
我跟我媽媽沒有任何精神上的交流,她養我就像養一個物品,好像是一種責任,要把我養大。在家裏,我媽、我哥對我說話都是高高在上的,居高臨下地訓斥,所以我在家裏很內向。但直到她去世,我覺得她還是對我付出了感情,只是沒有表達出來。
現在我跟我女兒之間經常表達愛意,她會說媽媽我愛你,我說寶貝我也很愛你。她的成績越來越下降,不過我不太在意。我說只要盡你自己的努力,以後過什麼生活,還是靠你自己。想讀大學就努力一點,不想的話,也可以學個技術。她怎麼樣都可以,我不會限制她任何事情。
她不怕我。有一次我回老家,接她下晚自習,看見她跟一個男生一起走過來。她一看到我就飛跑。等回到家,她就把我一推,「你破壞我的好事,為什麼要去接我?」等我回上海,她在微信里跟我說,媽媽我分手了,你放心,我會好好學習,我只是看中他的容貌。
今年春節,我沒回家。房東說,到時候回來要隔離的話,要自己找地方。能去哪裏隔離呢?我就沒回去。
以前我做那麼多工作,雖然舒服,但是工資不高。現在的生活算不上喜歡,但也沒辦法。上次回家我買了一個哈密瓜,女兒突然說,媽媽我們家是不是有錢了?我當時很意外,我說你怎麼會這麼問?她說以前你都給我買爛水果吃,這是第一次買新鮮的。以前超市裏促銷水果,一兩塊錢一大包,我經常買,裏面很多是快爛了的。
不過有時候想,這麼拼命掙錢,又能怎麼樣?我也想回去過平靜的日子。我女兒都夢見我死了。去年,女兒有一天突然間跟我發微信,媽媽你沒事吧?我那幾天正好也不舒服,我說怎麼了。她說,我還是告訴你的,我夢見你s了,打了一個字母s。
也有想法不一樣的人。有一個眾包的同事,每天送餐像小孩一樣,蹦蹦跳跳的。他說我一個月就跑1萬塊,多一塊錢我都不跑,他不羨慕樂跑的高單價。
我哥也讓我回去,他也想賺錢,不想給我帶孩子。如果回去的話,我啥也不想幹了。
(應受訪者要求,阿瀟為化名。)
感謝播客「打工談」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