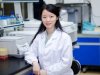多年以後,我會想起那個肅殺的殘冬,草木伏霜,殘陽滴血,逃亡路上的每一棵樹木,都像是扛着長槍的行刑隊。
好久沒寫公號了。前幾天有讀者質問我:年過六旬的方方即將寫下她的第60篇封城日記,不知原叔摟着老婆孩子過得可好。這話擊中了我。首先,我過得不好,時常失眠,在悲傷的夢境中醒來,其次,我並未忘記一個寫作者的良心,不會在這場巨大的災難面前裝瞎。
2020年1月20日,陰雨,我臨近中午才起床。本來這天我們是預備駕車從長沙回南寧的,但兔媽前一晚在單位的年會上喝高了,而我在10多個小時的車程中是需要她替換開車的,所以我說推遲一天才回吧。
因為醉酒而耽誤行程並不是第一次。前幾年有位朋友從加州回南寧,我們就着豬大腸喝XO,大醉,翌日我醒來準備按計劃開車回長沙,發現已是下午。
但20號那天兔媽說她還行,我確認她不會在車上像害喜一樣亂吐,遂開車南歸。半路上我在服務區倒車時發現,左右停着的車,都是鄂A車牌。
我或許算是最早注意到武漢疫情的人之一,大概是去年12月初,第一條肺炎新聞發佈之後,我幾乎每次看到武漢這類的新聞必轉,而且都在質疑。
我和一位前同事,時常在微信上交流對武漢疫情的觀點。我們不是先知,但都經歷過非典劫難的廣州歲月,我和他對這類的消息都有本能的敏感。
正是1月20號那天,跑在高速路上的我在微信里看到,北京已經對武漢疫情作出了批示。我鬆了口氣,心想,這個蓋子終於揭開了。
那天深夜,我們在暴雨如注中回到南寧,在大排檔吃了老友粉和田螺。沒想到的是,從那夜到現在,我們再也沒在外面的館子吃過哪怕一碗粉。世道驟變。
回到南寧的翌日,我去藥店買口罩,得知全被搶購光了。
我當時的臉色,綠得像初春的禾苗。
有一天,我走了幾公里,到所有的藥店去問,都說沒有。我兩手空空,疲憊地在南湖邊的石椅上發呆了很久。最懊悔的是,我最早注意到了疫情,也從海外公佈的數據中研判出武漢已經處於爆發期,我不瞎也不盲,甚至後來還有老同事說我是朋友圈裏最早的吹哨人,可是,我怎麼居然忘了應該囤點口罩?

我悔得腸子都青了。但我是真沒想到武漢會嚴重到這個地步、物資會匱乏到這個地步。總以為自己是快手,可以眼看形勢不對時再準備物資,其實你在10多億人當中,哪能搶到什麼?
母親重感冒了,聲音喑啞得說不出話,她擔心自己染上了病,堅持不出席我們和姑姑家幾年來例行的年夜飯,所幸後來證明是虛驚一場。幾十年來,我第一次不和自己的親娘一起吃除夕的團圓飯。大年三十下午,我和姑父在廚房裏忙活,他是廣西一家最著名的醫院裏的專家,我們邊做菜邊聊這次疫情,他淡淡地說:這種傳染病,對搞醫學的人來說是家常便飯,反正都逃不掉,只有他們上。
在南寧時聽說,我表妹的同學援鄂,我老友的妹夫援鄂。古時是湖廣填四川,如今是全國填湖廣。
我活了40多歲,這是最憂傷的一個春節。
兩個娃兒根本就不出門,他們惟一的娛樂,就是跟我上頂樓放衝天炮。城裏是禁煙花的,我們也許是全南寧惟一放炮的人。在無邊的黑暗裏,在死寂的城市裏,在望不見的冠狀病毒里,我帶着兩個長沙崽,在南寧的夜空裏放着湖南產的焰火,假裝無憂無慮,假裝國泰民安。我抱着三歲的流氓猴一次次點煙火,他拍着肉乎乎的小手歡呼,絲毫不知人世的悲哀。
新聞里的病例人數每天都在猛漲。據說武漢上空的二氧化硫濃度也在上漲。我每天都去藥店,站在門口遠遠地問一聲「有口罩賣嗎」,平素低眉順眼做促銷的店員把頭仰起來,傲慢而嫌惡地說:沒有。
8歲的流氓兔和3歲的流氓猴每天趴着陽台欄杆貪婪地看樓下的滑滑梯,但我不讓他們下去玩。我每天深夜都在看來自武漢的各種消息,有一晚,我看到李文亮醫生去世的消息,忽然鼻酸,眼睛濕了。他並不是大英雄,他只是低聲而急促地向自己的親友們吹着哨,提示一下風險,可是,這世間容不下他這點卑微的良心。
一個小人物竊竊私語說幾句真話,會被單位領導痛斥,會被派出所訓誡。如今成千上萬的人在李文亮那哭牆般的微博下每天留言,他們哭的何嘗只是一個早殤的醫生,他們哭的分明是這現世。
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學過一篇課文,叫《獵人海力布》。海力布得到一塊寶石,令他能聽懂鳥語,但他不能泄露秘密,否則就會變成石頭。有一天他聽鳥兒遷徙時說即將山崩,於是趕緊勸村民逃難,村民不信,他被迫說出了秘密,自己變成了石頭。
瞞騙者侯,死諫者誅。
除夕那天,我手機里收到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湖北的一名記者呼籲立即換帥,當時我正翻飛着菜刀在做白切雞檸檬鴨香辣蝦,沒空看。閒下來時去看,已刪,我都不知道文章說的啥。後來才知道作者是我多年前的熟人張歐亞,他因為這篇文章而被封口面壁。
你如果公開呼籲撤掉你所在城市的一把手,會有什麼後果?不知道,反正你家的水錶會接受輪番的檢查。所以,張歐亞很生猛。他和我是同一代的體育記者,那代足記中出了許多膽兒巨肥的人,出了許多有勇氣的良心寫作者,因為罵足協、罵國足成為習慣,所以,他們覺得天底下沒什麼是不能罵的,就算,你是那誰,川普。
烏雲壓城,但我們終究決定回長沙。雖然長沙距離武漢僅300公里,很兇險,但兔媽要復工,流氓兔隨時準備開學,還是得走。家人反覆叮嚀:如果長沙大爆發,就趕緊逃回廣西。我苦笑着想,倘若那天到來,我們這湘A的車早就在湘桂邊界被廣西赤衛隊攔住了,哪還能回來。
在暴雨中一路向北,路面死寂。除了加油,我們連服務區都不敢進。入夜時,經過衡山,沿途的村莊燃起清冷的焰火,我想起這是元宵之夜,整個春節都過完了,我才第一次感覺到年味。
然後,我帶着娃兒,在長沙家裏延續着漫長的自我幽禁。我迄今沒見任何一個朋友,沒赴任何一個飯局,出小區的次數不超過5次。趁着不用見人的這個機會,我甚至完成了一個多年的心願:剃了個光頭。活了46年,我終於第一次看到自己光頭的模樣。
但模樣佛系了,內心卻無法佛系。每天深夜在微信上看到無數的消息,我心如刀割,憤懣而無力。
武漢發生了什麼?武漢人自己並不願說。除夕那天,家裏給武漢的一位9旬親戚打了電話,她什麼都不願說,不願提,想是有無限慘痛。我朋友圈裏的武漢朋友,從不訴說自己的遭遇,從不哭慘,甚至很少發朋友圈。而我從潮水般的信息中,知道他們的困厄和絕境,但他們就是這麼硬氣,不需要任何憐憫和同情。換了別的城市遭受這種天塌大災,市民早就崩潰了。
在網上聽到一首不知名字的歌,特別喜歡。聽了幾十次。一位我很喜歡的女演員,用獨特的唱腔演繹了刻骨的淒涼。像素衣的女吊飄蕩在曠野的墳場,咿咿呀呀地泣訴着百年家國。每一次聽,都五雷轟頂。
特別喜歡裏邊的詞,她寫的歌詞,連許多著名的詞人都寫不出來——
那年的呱呱墜地啊
那年的老無所依
那年的滿心憤恨
那年的生死轉機
那年的萬人空巷啊
那年的小心喘息
那年的鐵欄罩住傲慢人
那年的生靈哭晚清
一遍遍的悲從心來。
這次大災能讓我們記住什麼?
我們會記住顢頇冷血的官僚和專家,他們在疫情已經爆發時辦萬人宴,他們告訴大家疫情可防可控人不傳人,他們訓誡吹哨的8個醫生,他們假手紅會打壓報復同濟協和中心醫院讓醫護人員連口罩都領不到,他們把山東無償捐助的蔬菜賣到了超市,他們用垃圾車和靈車給隔離的市民送生活物質,即使在災後,他們公佈的數據依然被公眾一次次地質疑。
我們會記得在這個冬天死去的人。有個重症患者,治癒後出院,才知道家人全都已經去世,他不願活了,吊死在高樓頂上。我看過視頻,他懸在空中,像一棵輕飄飄的蘆葦。昨天武漢市民排着長隊領骨灰盒,而他們並不是最悲慘的,最慘的是,那些無人領取的骨灰盒,這意味着整個家庭的覆滅。絕戶,滅門,這些久違的詞語,一次次在我們眼前浮起。
我們會記住那些孤兒。一個七八歲的男童在社區工作人員指引下茫然地獨自去領父母的骨灰,一個襁褓中的湖北男嬰被無力餬口自身難保的父母遺棄在汕頭一家醫院裏,而32個0到17歲的孩子被集中安置在一個隔離點,他們的所有直系監護人——包括父輩和祖輩,全都去世,他們也許還不會說話,就已永遠喊不出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這些詞,他們今生只能提着小小的燈籠行走在長夜般的人世,無人理會,無人憐愛。
我們會記住出生入死的醫護人員,戰戰兢兢吹哨的李文亮醫生,「早知道這樣,老子到處去說」的艾芬醫生,千里援鄂卻在曙光前夕在荊州被醉漢駕車撞死的王爍醫生,以及,來自南寧橫縣貧困家庭的援鄂護士梁小霞,據說突然昏厥的她還在死亡線邊緣,祈禱奇蹟出現,祈禱她還能回到北回歸線以南,重新見到邕江上的霞光。
我們會記住方方,以及和她一樣努力為蒼生發聲的人,硬骨頭的武漢人,硬骨頭的中國人,從未死絕。我很清楚方方為這60篇日記所付出的代價,遠不止於花甲之年的她每天用皸裂的手指忍着疼痛敲打鍵盤,她承受的還有無數的攻擊和打壓,謝謝這位大姐,謝謝不斷封號不斷轉載她日記的湘妹子「二湘」,謝謝隱忍但始終不屈的武漢人民,我們都知道你們身處這場曠世之災,有多麼絕望,有多麼悲痛,死神壓頂,彈盡糧絕,這不僅僅是武漢之殤,這是國殤,甚至世界之殤。

我們還會記得那些攻擊方方的蠅營狗苟之輩。其中一個出語惡毒的專欄寫手,這兩天被罵上了熱搜,自己還恬不知恥沾沾自喜,這廝去年污衊港人是納粹,如今攻擊方方之後,竟然還說君主比民主好。1912之後,這一百多年來,除了楊度等少數幾個三姓家奴,貌似沒人敢說這種封建復辟的話了吧。10多年前,我的專欄和此人經常同時出現在不同的報刊里,如今,我感到深深的恥辱,怎麼就和這種叼屎盆子的人為伍了呢。鼓浪嶼長蛆了。
當然,我也會記得寥寥無幾的良心媒體。財新、三聯、人物、新京報等幾家媒體,一直努力地報道最真實的疫情。作為前媒體人,我知道他們有多不容易,也許一篇報道的背後,就是一次訓和無數誡次的檢討。
友情推薦一下財新剛推出的《新冠時刻特刊》,這是財新匯集36名記者,歷時100天,用多篇重磅報道和近200幅照片集結的精華版。胡舒立和她的團隊,竭盡全力記錄下了這場曠世之災。
就在昨天,財新的記者還深入漢口殯儀館,去數骨灰盒。這是真正的良心媒體。全中國就剩這麼幾家了。
我們該記住的,還有許多。在圍城中心力交瘁的方方,在第60篇日記後疲倦地放下了筆。但我們應該接過她手中的筆,延續她反覆的吶喊:追責!迄今沒有一名官員對這場疫情負責,而我們都等着那一天。
最近接連看了兩部方方小說改編的電影,一部是《萬箭穿心》,一部是《埋伏》。
在《萬箭穿心》中,顏丙燕飾演的寶莉,丈夫有外遇後又下崗,跳了長江二橋,她為了養家,扛着扁擔每天給人挑貨,10年後,她含辛茹苦撫育的兒子成了高考狀元,卻要和她斷絕關係。

片尾,她沒有哭天搶地,只是踢了一腳熄火的麵包車,罵聲「個婊子養的」,揚長而去。武漢的女子就是這麼硬氣。
武漢於我,多少是有些緣分的。上中學時,發現武漢的大學在廣西的招生人數是最多的;直到這次疫情爆發,才知道武漢的在校大學生數量居然是全球第一。我高考時也不可免俗地填了那裏的院校,是武漢糧食學院。最近據說今年全世界會鬧糧荒,我囤了一堆大米罐頭壓縮餅乾後,忽然怔怔地想,當年倘若讀了糧院,去守了糧倉,也許,心裏就不會慌了吧?
曾經駕車陪長輩去武漢,去看望長輩的長輩。
曾經三次在命運的拐角處,被武漢大學的三個畢業生改變。
曾經出差武漢,那是2010年,我剛定居長沙,準備要個娃了。同事帶我去漢陽的歸元寺,說求佛特別靈。我在送子觀音佛像前拜了一下,同事望見一片樹葉打着旋落在我的頭頂,說一定靈驗。翌年流氓兔出生,如今他8歲半了,上三年級,我一直沒告訴他今年武漢的慘劇,武漢滿城的生離死別,因為我沒想好該怎麼說,雖然,他與那座城市有今世的緣分。
但我一定會對他說的,老子必須要說。這兩個月固然是孩子們囚禁家中的童年陰影,但又何嘗不是父母們此生最大的陰影。如果轉眼就忘,轉眼就若無其事,那我們跟一條鹹魚又有什麼兩樣?
想起了多年前復旦詩人陳先發的詩:
兩陣風相遇,有死生的契約
雨水赤裸裸,從剝漆的朱欄滑下
從拱橋之下離去
那時的他們,此時的我們
兩不相見,各死各的
兩不相見的,豈止是那些逝去的人。還有國與國的關係,族群與族群的冷眼,以及你和我,各自分道揚鑣的表情。我們有可能,剛剛過完了今生最好的日子,接下來只剩壞日子了。死去的人很痛,活着的人更痛。
我的前同事馮翔(「8字路口」創始人),在北京的公車上拍下了這幅圖,一個戴口罩的女孩在讀余華的《活着》。多麼真實的寫照。

恰似我們昏庸而怯懦的生活。
恰似我們深夜裏的悲從心來,淚流滿面。
個婊子養的,我們先前不是好好的麼,怎麼就遇見了這正月里的雷,那昆明湖裏的錢塘潮,以及,千里江山的無數新墳?
這個世道,這片山河,你能告訴我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