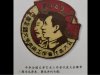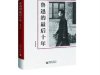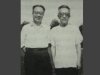本文為聶錦芳老師今年度《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課程的期中命題作文。文章構思良久,但還是沒能克服拖延症,直到交稿前夜,才與俊容兄約在知島咖啡廳起筆。兩周後再看,自覺雖然倉促就稿並未破壞文章的總體思路,但也有虎頭蛇尾之憾。一方面是缺少了大二時候校內「馬會」興衰的見證,那裏我第一次認識了一群非官方的、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活動者」;二方面對馬克思研究在後極權體制下的意義,也並未表達清楚。這些以後有時間再補上吧。
一
我有口無心地讀着語文課本里魯迅的作品,從小學讀到高中,讀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魯迅寫下了什麼?我覺得魯迅的作品沉悶、灰暗和無聊透頂。除了我在寫批判文章時需要引用魯迅的話,其他時候魯迅的作品對我來說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說,魯迅作為一個詞彙時,對我是有用的;可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時候,讓我深感無聊。因此,我小學和中學的往事裏沒有魯迅的作品,只有「魯迅」這個詞彙。——余華:「魯迅是我這輩子唯一討厭過的作家」,2011年。
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長大的「理科生」。
「社會主義」,意味着馬克思主義是這個政權宣稱效忠的對象,也意味着它教育的終極目標就是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因此,在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就從一本花花綠綠的《思想品德》教科書上學到了這樣的知識:經英國某報在世紀之交的評選,馬克思當選為上個千年最偉大的思想家。然而,在踏入中學以前,我對這位百餘年前的德國人的了解也就僅止於此了。
不久,甚至在還沒結束小學生活的時候,我就被告知自己將成為一名光榮的「理科生」了。據考證,一說,這是因為我從小就被劃界為「理科思維」,在圍棋和奧數這種「智力遊戲」上頗能展現點小聰明;二說,也是我認為更有說服力的解釋,就是在我爹媽看來,學理科才能有光明的前途。我爹90年代初從大學畢業,到南方闖蕩一番後,又隻身回到武漢,投入澎湃洶湧的股民浪潮。不巧,他才剛一入場,中國股市就開始了快20年的停滯不前——可惜他知道這一點的時候,時間已不允許他重來了。因此,干會計的我媽就成了全家收入最穩定的來源。在我們這樣一個典型的城市小中產階級的家庭的眼中,「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文科呢?只是那些「學不來理科的女生」才會被迫去學的。
總而言之,作為「理科生」的直接後果就是高中的政治課程並非必修(眾所周知,必修約等於不修)。順帶提一句,這一點曾讓我爹非常驚訝:在我們這個「政治掛帥」的國度里,如今高考的必考科目里竟沒有政治!以至於直到高考前的一個月,他還小心翼翼地要我再三確認,是不是我因對「政治」的厭惡而少報考了一門考試。
然而,在眼下的教科書體系里,在初中及以前,所謂「政治」教育基本是以社會常識為主,而不會涉及什麼「馬克思主義」的內容;無論是唯物史觀、社會主義,還是勞動價值論、經濟決定論,亦或是認識反映論和辯證法,都屬「高中政治」的一部分。因此,我在中學校園裏的「馬克思主義」基本都是「道聽途說」的。至於是如何「道聽途說」,我可簡舉兩例:
其一,「辯證法」。「辯證」這個詞,想必是早就聽過了。畢竟「要辯證地看問題」已成了句口頭禪,與「要科學地看問題」「要正確地看問題」這樣的空洞句子沒什麼兩樣。不過,在作文課上學寫議論文的時候,卻總是被語文老師指責:「你們政治里不是學過辯證法麼?寫作文也要用辯證法」。一開始,大家都聽完都覺得很羞愧,仿佛有什麼重要的思想方法是文科同學獨佔的,從而高出我們一截;然而,聽了幾次之後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辯證法」就是把問題正着說一遍,再反着說一遍,最後再搞搞調和得出個「中庸之道」的萬憂解啊!自此,我也自忖是學會「辯證法」了。
其二,「事物是普遍聯繫的」。我從前沒接觸過什麼哲學,也不了解馬克思主義,更枉談什麼「馬克思主義哲學」了。因而這句話可以是我的「哲學入門」了。當時是隔壁文科班在上一節政治公開課,課後一位同學很激動地向我們這些「哲學盲」進行了一番「哲普」:你們想想蘋果和宇宙飛船有聯繫麼?想來沒有吧!但是蘋果像小朋友的臉蛋,而小朋友的臉蛋又像太陽;太陽在宇宙中,而宇宙飛船也在宇宙中——蘋果和宇宙飛船聯繫起來了!據這位同學所言,他們在政治課上就樂此不疲地開展了20分鐘的&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