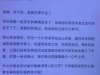各位同學、各位家長、各位老師:
早上好!首先,請允許我代表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熱烈祝賀各位同學完成學業,順利畢業!
每年站在這裏,我都如履薄冰,戰戰兢兢。
一個多世紀前,卡夫卡寫信給他妹妹說:「我寫的不同於我說的,我說的不同於我想的,我想的不同於我應該想的,如此下去,直至最晦暗的深淵。」其實同樣,
在我們這個不確定的時代,我想要說的話越來越多,但是我能說的話越來越少。我張口的時候,總覺得空虛,因為常常言不及義;而我沉默的時候,也並不覺得充實,我常常因為不能仗義執言而心懷愧疚。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哪一句話說得口滑,就會被網上的好事之徒斷章取義,自己就會墮入幽冥的深淵。
我最近一直聽說,在進入新時代新征程之際,等着我們的是浪急風高甚至驚濤駭浪。如果時代向我們提出了底限思維的要求,我當然會隱隱然擔心,將有什麼大的壞事情發生。
現象級災難其實已經發生過了,比如新冠疫情。我曾經too simple too naive地相信,該死的瘟神送走之後,我們的經濟會迅速逆轉,超越三年前的發展水平。但很遺憾,現實很骨感。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今年四月,24歲以下的青年人失業率突破了20%。即便是我們國漢院,就業率也不再能回到原先百分之百的那種持續輝煌。

雖然我深信,諸君未來肯定會幸運地擺脫靈活就業的命運,但很可能我們的微薄薪水配不上我們的消費激情,我們的工作條件配不上我們的事業雄心。如果內卷的競爭過於殘酷,如果996的壓力讓人處在崩潰的邊緣,我們有什麼資格譴責人們把小確幸當成人生的大目標呢?
兩個多月前,一位出租車司機告訴我說,網約車太多,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客源,如果不將工作時間延長到極限,比如十二小時甚至更多時間,就無法在繳納公司管理費之外有所盈餘。
他告訴我,有一次他在高速路上看到一位出租司機邊慢吞吞開車邊打瞌睡;他還告訴我,有一次由於解決內急而來不及按規定停車,被罰款二百,他忍不住嚎啕大哭。
也許,這樣的悲劇日常只是發生在小部分人身上的極端。但是,
展望未來之路,有幾人能夠鮮衣怒馬看遍繁花?又有幾人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
李白曾經慨嘆行路難:「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誰能向我們保證,這樣的人生浩嘆我們可以無需重演?
很抱歉,在同學們慶祝畢業的大喜日子裏,我不合時宜地跟大家說這些令人不快的事。我當然祝願而且相信所有的同學們會前程似錦。但不管怎麼說,憂患意識是我們這個民族精神血脈的一部分。
作為一個文學從業人員,我認為文學的優點在於提出問題,而缺點在於它不負責解決問題。但如果我們作為書生不能進入社會機制內部,不能現實主義地解決「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的宏大問題,我們依然可以積極地考慮解決個體的焦慮問題。
這裏我斗膽推薦的一款療治時代憂鬱症的藥方,或者一道讓人安身立命的心靈雞湯,就是孔子的教導:仁者不憂。
這個命題簡單來說就是,
無論窮達,尤其是萬一我們處境窘迫,我們還是要堅持做一個仁者,由此我們試圖達到不再焦慮的境域。
講到這裏,我要嘚瑟一下,我去年獲評了上海市「四有好教師」的提名。雖然是個提名,當然意味着我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但重要的是,我欣喜地發現,「四有」中的一有即「有仁愛之心」,如今是黨和國家現在所提倡的積極價值。
在我未成年的時候,孔子是孔老二,仁愛是被批判的東西。老師告訴我們,元宵節的燈會活動,是宣揚封建迷信的活動,應該予以無情打擊。我就夥同小夥伴,撿了一些瓦片,看到比我更小的兒童興高采烈地拉着兔燈,就商量好了一起投擲瓦片,迅速逃跑。然後躲在遠處,看到焚燒的兔燈和孩子哭泣的聲音,頓時就有點後悔,但內心另一種聲音很快制服了我:我的革命意志不夠堅定,不能壓倒小資產階級的人情。
老師教育我們,要嚴防壞人壞事,遇到形跡可疑的人要匯報。有一回我在如城的北門大橋上看到一個人鬼鬼祟祟,時不時東張西望一番再低下頭做些什麼。我心驚膽戰地跟蹤過去,突然發現有一股輕煙冒出來了,我立刻意識到階級敵人試圖炸毀大橋,於是不顧一切,一個箭步撲過去,結果發現並沒有發生同歸於盡的爆炸事件,人家其實是在吃烤紅薯,他只是吃東西不想被人發現。
這是我童年時期對社會世界的感知方式。不過,對陌生人的普遍懷疑,不一定始自當代。明人洪應明《菜根譚》中有一句名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就表達了這層意思。
我們的處事哲學好像是,假如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但假如你對我並無滴水之恩,我又何必對你親近信任?當然,我這裏絕不是說,對於境內外敵對勢力,我們還可以假以辭色;敵人來了有獵槍,對他們我們要勇於鬥爭、善於鬥爭。但是,如果我們想構建和諧社會,想把我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搞得少少的,我們就不必每一分鐘都繃緊神經。
即便在烽煙四起的春秋時代,孔子還要求弟子們「泛愛眾而親仁。」即便命途多舛,陶淵明還吟誦出「落地皆兄弟,何必骨肉親」的詩句。
我時常會想,如果一個社會對立加劇、戾氣橫行,如果容錯率降低、極端事件頻發,撇開其他原因,是不是也因為我們遺忘了先賢們關於仁愛的叮嚀呢?
那麼,什麼是仁愛呢?孔子說的「吾道一以貫之」的道即仁,也就是忠恕。根據傳統的解釋,忠是中和心的合成,朱熹說:「盡己之謂忠」,就是《禮記•大學》中講的誠意正心,換句現代的話說就是守住我們的初心;恕,是如和心的合成,朱熹說:「推己之謂恕」,不是指寬恕,而是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這讓人油然想起康德著名的絕對律令:「你要這樣行動,就像你行動的準則應當通過你的意志成為一條普遍的自然法則一樣。」
但是,在人的本性中,利己的衝動遠比利它的願望要強烈得多,因此,仁的實踐似乎是難的。如果我們看過韓國的電影《寄生蟲》,我們大概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家裏有餘糧的地主,比處在窘迫的生活壓力之下的底層人民更容易好善樂施。
但這並不是孔子的看法。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我們未必有能力改變外部世界,但仁愛,我們依靠自己的主觀意志還是可以接近的**
。**孔子讚揚他首座弟子顏回的話我們大家都是熟知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對仁者而言,不僅貧賤不能移,而且履仁蹈義本身還能獲得至樂。
根據新儒家徐復觀先生的說法,仁者之樂,來自於義精仁熟,來自於對社會責任的慨然擔當,來自於「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的揮灑自如,來自於生命力量的跳躍與升華:因為在踐履仁愛的過程中,人的精神超逸出身體自然的約束,而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從而自己的心性境界得到擴大,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安頓和圓滿,這就是為什麼孔子會說「吾與點也」,為什麼會告訴我們「仁者不憂」。
但仁者的果位,連孔子也自認為難以企及,那為何我還要向大家提出這樣似乎不切實際的建議呢?
我想引用朱光潛先生的一段話:
「聖·奧古斯丁的一個門徒波林納斯敦促諾森布利亞國王愛德溫改宗基督教這種新的信仰。國王召開一次會議,問計於他的謀臣們。其中一人直言道:『王上,人的一生就好像您冬天在宮中用餐時,突然飛進宮殿來的一隻麻雀,這時宮中爐火熊熊,外面卻是雨雪霏霏。那隻麻雀穿過一道門飛進來,在明亮溫暖的爐火邊稍停片刻,然後又向另一道門飛去,消失在它所從來的嚴冬的黑暗裏。
在人的一生中,我們能看見的也不過是在這裏稍停的片刻,在這之前和之後的一切,我們都一無所知。
要是這種新的教義可以肯定告訴我們這一類事情,讓我們就遵從它吧。』」
我不是基督徒,當然不會規勸大家皈依基督教。作為無神論者,我也不相信基督教能給我們帶來某種堅實可靠的確定性。但這裏的道理是一樣的:
前面的道路究竟如何,我們是茫然無知的。但如果我們立志於做一個仁者,我們可以無待於外物而追求內心的澄明和對他人的關愛,我們就在一個不確定的時代為自己樹立了確定性,這不再是小確幸,而是懷抱信念的大歡喜——是否達到仁者的某種段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有仁愛的大方向。
由此,我們也戰勝了焦慮和煩惱,我們可以不怨天、不尤人、不疑懼、不憂鬱。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