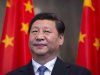一場「白紙運動」,以行動反抗慘無人道的「清零」抗疫措施,令中共手足無措,最後鎮壓不成,巨大民怨防不勝防,只好全力疏導,再秋後算賬,但足以反映當局落後於社會形勢,尤其是青年一代,敢於挺身而出而且站得最前,完全超出統治官僚只懂「愛國」宣傳和鐵腕控制的想像。
其實不少細心追縱青年動態和社會發展的專家學者,早已指出隨着中國社會出現重大轉型,新一代的心態和價值觀亦發生劃時代的更替。例如復旦大學社會學家桂勇等人的研究便指出兩大趨勢,一是青年人的個性解放,二是他們對社會難以放下的憤怒,兩者將構成不可忽略的潛在力量,就如「白紙運動」那樣,將促使更多人以行動捍衛自己的權利和尊嚴。
個性解放首先是自我觀念的改變。中國人由過去是社會主義集體的一分子,凡事遵從國家界定的規則行事,但四十年來社會轉型,新一代正大步走向個體化,以個人的興趣及價值決定思想取向、職業以至行動選擇。
上述的研究指出,社會轉變的最大驅動力就是經濟的高速及持續增長,當中市場經濟起了史無前例的作用,個人身份尤其突出,因為由求學進修、求職擇業到投資創業等等選擇,大都出於對自身條件、興趣、工作及生活期望的個人考慮,多於國家決定一切。與此同時,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力下降,社會福利功能同步減弱,更令九十後的一代更相信自己是不折不扣的經濟個體,靠自己的能力過活,按自己的想法行事,為自己而活,甚至不少人早已看透「財富不過是追求夢想、自我實現的副產品」。
不過,追求非物質的個人生活理想,不等於可以逆來順受,對令人失望的經濟遭遇,不會感到挫敗。相反,上述研究指出,在以資產增值推動經濟發展的中國社會,正大幅拉開貧富懸殊的差距,令後來者亦即青年一代感到無力從後追上,因為單憑學識及工作能力所賺得的報酬,永遠追不上資本的增值,也只因為他們是後來者,不論怎樣努力,收入增長也追不上樓房價格的漲幅,一生不過「為房東打工」,也因此不管學歷有多高、收入有多高,他們依然深感不公,覺得自己不斷向下流動,處身社會的底層而無法翻身。
面對經濟機會不公平引起的挫敗和不滿,新世代在一黨專政下,沒有政治方法可以解決社會矛盾,只有心懷怨憤和自求多福。既然無法追上,倒不如首先保存自己,盡力實現個人的興趣和價值,只求個人福利,放下其他責任,不被工作奴役,不被結婚生子拖累,甚至生活上「躺平」也可。至於傳統家庭倫理訴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集體主義社會觀念(「艱苦奮鬥」)、企業合群精神(「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大福報」),大可置諸不理,人人為自己的生活負責,其他角色和責任一概可免則免。
另一方面,儘管沒有公開表達的機會,新世代將不公平的遭遇看在眼裏,便如桂勇所發現,把問題歸咎到社會結構和制度。例如,把社會經濟問題看成世代之間的矛盾(「房價就是中年人對年輕人的剝削」)、資本的壓迫(「資本利用我們創造了更好的世界,我們卻被驅逐了」)、自由經濟的略奪(「自由市場就是自由地炒作房價」)等等。由此延伸下去,世代、資本以至市場之惡,當然離不開國家政策缺失,以至政治制度的毛病。
無疑,九十後新世代喝愛國主義奶水長大,一向標榜中國取得巨大成就,道路與別不同,其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舞台舉足輕重,更加重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因此面對不公平的經濟現實,至高無上、永遠正確的國家,自然被看成可倚靠的力量,以解決世代矛盾、對付資本惡行、修復市場偏失等等。不過,當國家對這些不公平的根源無能為力,甚至逐漸被看成是問題的一部分,過去對國家的熱切期望,只會徹底失落,甚至走向反面,嚴厲批評國家的不足。
可見,新世代的個性解放卻遇上令人窒息的社會經濟現實,愛國主義的熱望又碰上束手無策的國家機器,群體的不滿亦只能通過非常的政治渠道排解。所以「白紙運動」雖然告一段落,但由新世代與統治當局的價值差距引發的緊張和矛盾,將是了解今後政經發展的重要線索。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