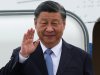"政治少數派頓悟系列No.13:我最應該支持許志永和他的同伴們的時候就是現在,把他們的事跡傳達給更年輕的人的時候就是現在。毫無保留、毫無矯飾地說出我對許志永的了解與不了解,就是現在我為許志永他們、我為我自己、我為年輕人、我為文明史中國所能做的最恰如其分的事。
作為一個關注中國公共事件超過20年的人,我自然很早就聽過許志永這個名字。4月10日,他和他的同伴丁家喜因"顛覆國家政權罪",分別被判處了十四年和十二年有期徒刑。這個意料之中的壞消息傳來的時候,我去讀了許志永的法庭自辯詞,去迎接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痛苦。
上一次我聽說許志永的消息,是他2020年因為和跟其他政治異見者聚會又被抓了。再上一次,是他發表了給習近平的《勸退書》。至於丁家喜,很慚愧,他的名字都是在我了解許志永2020年被捕原因的時候才知道的。那個時候,或者在那之前的什麼時候,我就知道許志永肯定會被逮捕,大概會被重判,或許不會有被釋放的一天。然而,壞消息真正到來的時候,我還是不能不比我預料中更痛苦一些,也不能不感到應該說些什麼。
我在2003年就通過孫志剛事件第一次知道了許志永這個名字,但並沒有特別關注或支持過許志永此後組織的公民行動。
這並不是因為我反對他,或者我當時還"不關心政治",而是因為一些現在看來恍如隔世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許志永當年只是龐大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中的普通一員。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評選了"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這個榜單當時並不包括許志永,也不包括梁文道,更不必說後來被網民視為著名公共知識分子的柴靜、羅永浩、韓寒、姚晨等人了。這固然是因為這份榜單自身的局限性,但也是因為可供選擇的候選人實在太多,領域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
如果說現在的中國找不出一個可以關注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話,當年的中國就是公共知識分子多得關注不過來,因此沒有哪個關心社會和民生(用《南方周末》的說法就是"國脈與民瘼")的網民會只是某一個名人的粉絲。刻薄一點說,成為某一個人的粉絲簡直是種不入流的表現。因為那時吸引網民關注的是公共事件,而當時的大量公共知識分子都會積極圍繞公共事件發表言論,甚至展開多輪論戰。人們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只靠關注某一個人、某一個渠道去了解相對完整可信的事件全貌和背景知識。
如果說現在的公共事件必須依靠無數網民同時關注,與刪帖員拼人數、拼手速,絞盡腦汁編寫隱語黑話,不斷把事件頂上熱搜,才能得到寥寥數語藍底白字官方通告的話,當年公共事件的解決其實並不特別需要網民的大量關注。因為只要媒體集中報道,公共知識分子紛紛發聲,有關部門自然會立刻回應。假如這份回應過於拙劣,就會迎來更多媒體追問和專家駁斥,更上一級的主管部門就坐不住了,會出面提供更能服眾的回應。直到這時,事情才能告一段落。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早早放棄了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支持政治改革的希望,而許志永早年則屬於溫和改良派。
我前面提到的曾經短暫存在過的"輿論監督—當局整改"模式,在新生代政治少數派看來或許美好得如同中國夢,只要堅持下去,完全沒有必要反黨反政府,我們寫在憲法上的公民權利就能落到實處,中國社會就會變得更加文明、更加和諧。
抱着這種理念的許志永在《2003:孫志剛案開啟的公民權利道路》一文中提到,當時公共知識分子的努力目標不僅是解決具體的"冤案",更是為了推動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消除侵害公民權利的制度存在。具體到孫志剛案,其目標不僅是追究毆打孫志剛致死的兇手的刑事責任,甚至也不僅是廢除收容遣送制度,更要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從源頭上阻止違反憲法精神、侵害公民權利的法律法規繼續出現。
我並不懷疑以上目標的正確和必要,然而,我很懷疑可以通過輿論監督甚至是參政議政,讓共產黨放棄自己的絕對權力,哪怕只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我的理由很簡單:巴金老人和無數有良知的中國人希望建立的文革博物館在哪裏?1989年的學生運動,乃至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歷次運動的完整公開記錄在哪裏?涉密的東西不讓看,那曾經印在《人民日報》上的那些東西為什麼也不讓看呢?過時的東西不讓看,那某位藏族作家和某位土家族作家新編新寫的東西為什麼也不讓看呢?當這個政府連發生過的事情都不願意承認的時候,一個具備基本思維能力的人怎麼去相信它會為發生過的事情承擔責任?又怎麼去相信它會為今後將發生的事情承擔責任?
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政黨,在對前述任何一起大規模悲劇負有直接責任的時候,唯一符合文明社會標準的擔責方式就是下台。倒不是說人民或別的什麼勢力一定有辦法讓這樣的政府立刻下台,而是說,出了這種事還不下台的政府絕對不可能"汲取教訓,永不再犯",只可能"就這樣吧,下次還敢"。
也許這個政府有時會表現得像個"明君",然而它還是把自己當作毋庸置疑的"君"。只要在這一點上沒有改變,所有接受批評、接受監督的表現就都可以是毛澤東式的"引蛇出洞"。我沒有許志永那樣捨身開路的覺悟,也無從預知他將來會從政府與民意的協調人轉變為公開勸退的顛覆者(至少這是當局的看法),遵循本心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第三個原因,在意識到需要去做的事太多,我能做到的事太少之後,為了避免無所作為或是陷入絕望,我選擇只專心去做不會對自己產生負面影響的事;許志永所做的那些直接跟當局對話或對抗的事不在其中,自然也遠離了我的關注中心。
我這裏說的負面影響,不只是被約談、家人被威脅之類的影響,還有我本人承受不了英雄包袱的因素。舉例來說,我做過的事有長期獻血,還有通過自己信得過的渠道給貧困學生捐過一些小錢,均攤到每個受捐者身上就更少了。我反覆衡量過,覺得這樣的付出是我可以接受的:我不需要知道對方是什麼樣的人,也不會產生什麼期待,無論對方將來是輟學了還是怎麼了,我都不會感到他們對我有所虧欠,或者自己做了無用功;就算某一天出於偶然或對方的善意有機會再打交道,對方頂多再請我吃頓飯也就扯平了,不至於給Ta構成什麼負擔。
我這樣的人,跟以天下為己任,不怕為他人命運負責的許志永,從行動邏輯就開始出現分歧了,對他關注得越多,我心裏的懷疑和憂慮就越多。只有選擇被動關注,必要時聲援,才能維持我自己的心理健康。
這就說到了第四個原因,毋庸諱言,我當年不能認同許志永的一部分言論和行為。
跟很多關心政治的年輕人一樣,我曾因為某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某些言論,對那個人"一票否決",哪怕沒到那個程度,對那個人的認同度肯定也會下降。在我看來,許志永在幾件事上或者表現出了不專業,或者表現出了思想上的極端保守:
影響最大的一件是《公盟"錢雲會之死真相"調查報告》。我的看法與郭玉閃《公民社會該如何行動?——對許志永調查報告的簡單診斷》中的數位公共知識分子基本一致。另一方面,滕彪在《誰是許志永?》中針對此事的批評和辯解,我也都同意。許志永是一個英雄主義的人,這是他的行動動力和人格魅力之一,也是他有時會犯錯、犯錯之後有時不能及時改正的原因之一。在當年的我看來,許志永認為公民調查團應當發佈非正常死亡案件的"真相",僅這一點就離法治原則相去甚遠了。毒樹的果子不能吃,程序正義是最大的實體正義,不能堅持不違背這兩條基本原則的人,無論主觀意願如何善良,在法律和政治上都是不專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