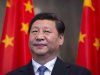今天,9月21日,既是「靜默管控」的拉薩封城41天,也是我母親離世42天。
預先設好的手機鈴響,提醒供酥[1]的時間到了,
我放下奧茲的《愛與黑暗的故事》[2],
起身走向門口,將糌粑和特殊藥粉攪拌的酥,
均勻地撒在熏黑的不鏽鋼盤子上,
打開電爐,烤出的香味隨煙飄散[3]。
已值正午,烈日當空,白雲寥落,
點開噶瑪巴念誦《極樂淨土願文》的視頻,
卻聽見不遠處傳來救護車的鳴笛聲,
很急促,催命般,又時斷時續,像是不只一輛,
像是滿載了不少病人,需要快快地送走。
送往哪裏?聽說拉薩的方艙已增至八、九個[4],
而方艙這個詞沒譯成藏語,若漢語發音不準,
就成了藏語諧音的豬圈或乞丐的房子[5]。
這些日子,這三十多天被「靜默管控」的日子,
救護車的嘶鳴是這座空空蕩蕩的城市
唯一的最強音(想起新話「時代最強音」),
還有什麼聲音呢?啜泣,呼告,誰聽得見?
院子的四面牆頭有雀鳥啁啾,盛開的
月季紅得像鮮血,被小蜜蜂無聲地吸吮;
長得像花豹的野貓躍下堆滿朽木的房頂兀自離去。
越蓋越高的世俗居所遮擋了頗章布達拉,
也遮蔽了原本可以隨風傳來的風鈴聲。
我靜下心,舉起金剛鈴,朝着香煙裊裊的
酥,搖響三次,並須念誦三次:嗡啊吽
多麼盼望走了整整一個月的阿媽會聽見,會再來……
然後,我會沿着那個永別的深夜,我消瘦的阿媽
被年輕力壯的天葬師放上擔架前,給她穿上
她喜愛的那套綠襯衣、綠條邦典[6]的藏裝,
從剎那空寂卻殘留香味的臥室抬出的路線:
穿過用一條條挽結的白哈達隔出的通道,
兩邊是殘花凋落的紛亂枝條出自她的栽種;
繞過供着美麗佛陀塑像和大桶清水的木桌,
桌下用糌粑畫了古老的雍仲符號,而窗戶上
映出幾十盞點燃的酥油燈,搖曳着,如同照亮莫測的中陰;
依順時針方向轉一圈,再依逆時針方向轉一圈,
這是讓亡靈找不到回家之路的意思嗎?
不料,緊攥着拴在擔架上的哈達走在前面的我
一個踉蹌,是阿媽不願離去嗎?淚水奔涌,
走出大門……不,我不能走出大門,據說奧密克戎
仿如可怕的巨獸,張開血盆大口,蹲伏門外!
是的,我們都不能走出大門,所有人;
我們都要乖乖地聽話,所有人;
我們都須隨時聽令,所有人(新話稱「不漏一人」)
或者排長隊做核酸,或者等大白[7]入戶做核酸,
有天半夜還做過什麼抗原,就像某種被操控的遊戲,
人們啊,要活着還真是花樣百出,心存僥倖,
最多隱約地感覺到有些深淵早在暗夜挖好,
對了,我們還要雙手接過恩賜的連花清瘟[8],
我們還要感激涕零,三呼萬歲……
但我此刻不關心疫情,我已深陷生離死別的疫情!
啊,我的阿媽,你走過的這條離開我的,
離開你多年前一手蓋起來的這座宅院的路線並不長,
如今我每日三次供酥都會反覆地走來走去,
會邊走邊念六字真言,聲音很大,如同呼喊,
就仿佛,被打動的觀世音菩薩會垂憐喪母的人……
而我抬頭,深邃、碧藍的天空一縷白雲飄來,
於是我再也、什麼都聽不見:救護車的不停
哀號,金剛鈴的三聲脆響,法王聲若洪鐘的救度,
以及這些日日夜夜我的祈禱……我啊我
什麼都聽不見,只聽見那個生養我的親人
最後的嘆息:「來不及了,已經來不及了……」
2022年9月12日寫,15日改,於拉薩
注釋:
[1]酥:གསུར་是一種煙供。傳統上,須用特殊藥粉及「三白三甜」(酥油、牛奶、酸奶;冰糖、紅糖、蜂蜜)與糌粑攪拌,點燃後或烤出的香煙是某種食物,以求上供下施,以及親人亡靈享用。
[2]《愛與黑暗的故事》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1939-2018)寫的長篇自傳體小說。
[3]傳統上,是在陶罐內放置點燃的牛糞,再撒上酥,以供亡靈七七四十九天享用。
[4]修改這首詩時得知在拉薩蓋好的、或臨時設的方艙不止八、九個,而是二十多個,甚至更多,並擴延至附近的墨竹工卡縣等。另外,將核酸檢測為陽性、甚至也有陰性的人們拉往方艙的車,除了救護車,更多的是公交車,因為常常是深夜拉人,被拉薩人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戲稱為「恐怖片:拉薩午夜的公交車」。
[5]藏語的豬圈發音「帕倉」,乞丐的房子發音「邦倉」,與漢語方艙諧音。
[6]邦典:པང་གདན།,藏人婦女藏裝裙袍上的圍裙。
[7]大白:也是中國發明的一種新話,指參與疫情防控的人員,因穿白色防護服被稱為「大白」。
[8]連花清瘟:中國發明的用中藥材製成的以對付新冠病毒的藥,是中國衛健委的推薦用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