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的說,國王路易十六這人,其實蠻有進步思想的。但畢竟太天真,一看這個問題難辦,就發表了一個最高指示:「沒錢啊,那就開會吧」。然後就去忙活他更心愛的鎖匠行去了。

當然這種具體事務本也不該由國王操心。應該由宰相負責。
1614年的三級議會後,法國確立的體系是紅衣大主教相當於事實上的宰相,相繼出現了黎塞留、馬扎然等權傾朝野的名相。
而到了路易十六這一代,輔佐他的這位老宰相名叫布里安,這個人在退休前一個月,提出了一個在世界憲政史上都異常開明也異常奇葩的想法:邀請全法國的社會賢達一起給國家上書,一起討論三級議會怎麼開。
這個「百家爭鳴」的號召一出不要緊,國王在布里安卸任後相繼收到了2500多份「陳情」,議題絕不僅僅涉及三級議會怎麼開,還有法國未來的政治體制怎麼設計,哪些苛政需要被廢除……等等等等。
這麼多的信件,路易十六不知有沒有經歷仔細看過沒有,但托克維爾是不辭勞苦的將存留下來的「陳情」一一詳讀過了。
讀過之後的托克維爾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帶着一種恐怖的心態認識到,這裏所要求的是對國家整個法律和風俗習慣在瞬間同時廢除。我看到的問題是,法國即將迎來的,是世界上曾經發生過的諸多革命中最危險的革命。」
也就是說,如果路易十六真看過這些信,又足夠聰明的話,他應該知道即將召開的這場「三級議會」將要打開是一個「潘多拉魔盒」:與會的各階層代表們此次前來,不是來尋求共識的,而是競相表達各自的利益訴求的。所有人都把「三級議會」當做了一台「許願機」,一旦願望得不到滿足,會議立刻就會破裂——畢竟,此時的法國,除了「都認國王」這個還在被迫接受的唯一共識之外,已經沒有任何共識存在了,連會要怎麼開,權利該怎麼分,都沒有達成一致。
於是通往法國大革命的路就這樣被鋪就了。
1789年7月15日的早晨,法國大臣迪克·德·利昂古爾走進凡爾賽宮,向國王匯報了前一天巴士底獄被攻克的消息。
路易十六聽後十分吃驚,困惑地問:「怎麼,造反啦?」
大臣微施一禮,說:「不,陛下。這是革命。」

4
那麼,什麼是「革命」?
美國歷史學者蘇珊·鄧恩在《姊妹革命: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啟示錄》中曾經對相繼發生的這兩場革命做了一個有趣的比較和二元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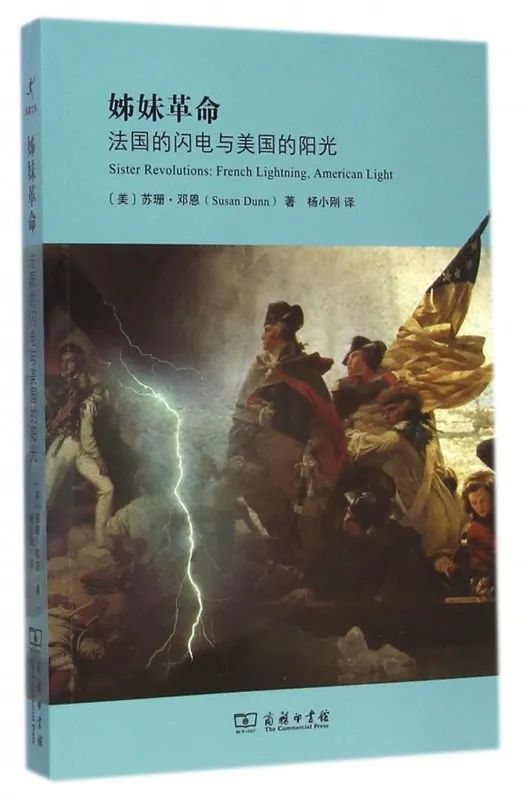
按鄧恩的說法,美國革命是一場參與者尋求共同底線的革命,參與者是在求「最大公約數」。
終整個美國革命始終,都似乎「卑之無甚高論」,革命前托馬斯·潘恩的那本《常識》小冊子,講的只是無代表不納稅等等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識,1776年的制憲會議最後形成的憲法也非常保守,主要就是講了講聯邦和州要怎麼分權。
這種現象的理由很簡單,因為當時美國各州精英們能達成的共識總共就那麼多,說多了就吵起來了。
而與之相比,法國革命則是一場參與者各自闡述理想上限的革命,參與者是在求「最小公倍數」。
所以你看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比美國的憲法寫的帶勁兒多了。美國吉倫特派、雅各賓派、保皇黨,米拉波、丹頓、羅伯斯比爾,所有人在革命開啟之後,也都爭相闡述自己理想中的政治體制應該是什麼樣子。
但這種唱高調的結果,革命後的法國議會永遠是吵作一團的,議長甚至必須做出規定「同時只能有四個人一起發言」——因為想要表達不同觀點的議員永遠多於這個數量。

而當議員們在議會裏語言說服不了對方,「物理說服」就開始了,無休無止的街壘、運動、政變、派系互鬥、屠戮由此產生。
誠然,在這兩種革命當中,後一種似乎更帶勁一些,從一開始,所有人都興高采烈的將這場變革當成了自己的許願機,期望社會呢朝着對自己階層分配有利的那個方向走。
但這個所有人都興奮迎接的變革,最終一定也讓所有人都失望、甚至受難深重。
因為大家在謀劃革命前景時,都只記住了自己夢想中所想的美好未來。一旦別人心目中的未來與你不同怎麼辦?那就只能殺了,用肉體消滅的方式屏除異見,所以法國大革命從一開始就註定血流成河,重演當年宗教革命黨同伐異的悲劇。
如果做更深一步的思考,你會發現,美國革命聽上去雖然沒有法國革命那麼「來勁兒」,但反而是更幸運的——革命綱領能基於參與者們的「底線共識」,因為有參與者有這個「最大公約數」可以求。
相比之下,法國因為之前兩百年裏國王對民眾信任的長期透支,各階層間的底線共識其實已經蕩然無存了,所以在革命發動時,為了調動大家的熱情,不得不追求「理想高線」,宣稱要同傳統完全的、徹底的決裂,建立一個嶄新的新世界。
當然,我們要報以同情之理解,正如托克維爾所言,法國當時的問題,在於因為亨利四世之後歷代王權的有意調配,導致法國社會各個階層之間如托克維爾所言,既互不往來、互不理解又彼此仇視。
用數學的語言總結,就是這個社會所有階層彼此都是「互質」的,根本沒有「最大公約數」可以求取。
於是求取一個其實很大的「最小公倍數」,成為了法國大革命的唯一選擇。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喊的那麼漂亮,宣稱要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新世界——因為在這個公倍數之下,法國人已無法再達成任何共識了。

而這樣的願景,固然能讓所有人都興奮期待,卻註定是一個悲劇——大家的各自美夢,都在革命開始提前做好了,而社會必須面對的共識撕裂、底線被突破的風險,則都藏在興奮的人們看不見的幽暗之處。
最終,如同兩百年前人們懷着對宗教的熱忱興高采烈的走入宗教戰爭的地獄一樣,法國人再次興高采烈的走入了「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人間地獄之中。
「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不會吸取歷史教訓」——至少對當年法國人來說,這個魔咒應驗了。

這就是法國大革命那總被人遺忘、卻決定了一切的前史,
這樣的故事,昨天發生過,今天仍在發生,明天——我們希望——它不要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