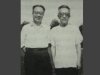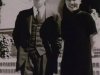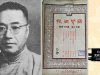為什麼我一再強調要有客觀的了解呢?因為這個時代的人最無法度,最不客觀,所以最須重新正視。首先是要了解自己的本,中國古人講學,是有規模,有法度的,這個法度軌道,在明朝亡國後就消散了,清朝接不上,民國以來離得更遠,所以病痛到來,沒有觀念,無法應對。因為學問傳統是整體的,既無法了解自己,更無法了解別人。像梁先生、馬先生、熊先生等都不能完全相應於前賢,何況其它?至於胡適者流,以其不平不正之心態,又焉能了解西方?學風如此,中華民族憑什麼來指導他的生命方向,憑什麼來應付時代呢?所以先客觀的了解是很重要的,第一步了解自己,第二步了解西方,然後尋出中華文化的出路,我們希望年青朋友要接上這個責任。這個責任簡要地說,就是要恢復希臘哲學的古義。古希臘"哲學"的原意是康德所規定的"實踐的智慧學"。什麼叫做"智慧"?"嚮往最高善"才叫做"智慧"。一般人都知道哲學是"愛智慧",而所謂"愛智慧"之"愛",即是"衷心地嚮往那人生最高之善而且念茲在茲的要去付諸實踐"的那種愛,所以希臘"哲學"之古義,康德名之曰:"實踐的智慧學",這個詞語用得很恰當。但這樣的哲學古義,在西方已經被遺忘了,現在的哲學只剩下高度文明下的語言分析,講邏輯變成應用計算機,這其實不算是哲學,只是哲學之淪落為技術。若要進入哲學之堂奧,就必須有以上所說的"愛智慧"—"嚮往最高善"之嚮往。西方既已遺忘,而這個意思的哲學,正好保存在中國的哲學傳統中,即是中國古人所謂的"教"。"教"的意義,佛教表現得最清楚,儒家也有,就是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的"教",也就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教"。此教的意思不是現行學校教育的"教",學校教育以知識為標準,而這個"教"的意思則是"哲學",亦即是"嚮往最高善"之實踐的智慧學。
6.西方哲學
西方現在是英美分析哲學當令,歐陸最出名的是海德格的存在哲學、胡塞爾的現象學,這些都是二十世紀的"纖巧哲學",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什麼叫做聞君子之大道?凡是能上通Noumenon(本體)的,才算是聞君子之大道,而這兩個人並沒有Noumenon的觀念,所以我看胡塞爾之現象學,寫來曲曲折折,煞有介事,可是終究貧乏得很,可謂一無內容。因為他把智慧的法度給喪失了,哲學的本分放棄了,只好說空話。他們那些問題,歸到科學也就可以,何須哲學家去做拉拉隊?所以當今要講真正的哲學,不能靠西方,而是要好好回歸自己來了解中國的哲學。我一生的工作也很簡單,只是初步的客觀的了解,但也已超過前代,所以我曾寫信給我一位在大陸的學生說我一生平庸,只有一點好處,即是我客觀了解的本事,在當今很少人能超過我。我沒有什麼成見,馬克思資本論我也部分地看過,我也能虛心地去了解,經濟學我也並不十分外行,只是不是我的專業而已。所以我的討厭馬克思,是我了解後真的無法欣賞,不是我的偏見。又例如我了解佛教也是下了苦功,熊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天天和他在一起,他天天批評唯識宗這裏不對那裏不對,於是我就拿玄奘《成唯識論》加上窺基的述記及他人的註疏,一句一句的好好讀了一遍,是很難讀,很辛苦。讀完後,就跟熊先生說:老師,你的了解不大對。熊先生把我教訓了一頓。因為熊先生有一些偏見,一個人不能先有偏見擺在胸中,一有偏見,凡事判斷皆差,這時須要有明眼人一下點出,而且最好是師長輩。告訴他:不贊成可以,但不可做錯誤的了解。可惜當時沒有人能說服熊先生。熊先生讀書時心不平,橫撐豎架,不能落實貼體地去了解對方,首先把人家的東西弄得零零碎碎,然後一點一點來駁斥它。他對儒家的文獻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干元性海,體用不二。這是不夠的,所以幾句話就講完,而量論作不出來。我曾寫信給他,說:"老師的學問傳不下來,您要靠我去傳您,否則您是傳不下來的。"後來我寫成《認識心之批判》及《現象與物自身》,大體可以稍補熊先生之缺憾——《量論》方面之缺憾。
先了解古典,看看古人進到什麼程度,還能不能再進一步,如魏晉名士復興道家,對玄理之開拓很具規模,但到現在我們發現還不夠,所以現在要接着重新講道家。又如佛教在以前法度很嚴謹,有思路,但現在都荒廢了,而且其論說方式也不適合現代人,所以我寫《佛性與般若》,重講天台華嚴。不管和尚居士,沒人講天台華嚴能講到合格的,因為那是專家之學,不是一般隨便讀幾句佛經即可了解。我雖不是佛弟子,但我比較有客觀的了解而能深入地把它們重述出來,這於宏揚佛法不能說無貢獻。唐君毅先生力贊華嚴,其實華嚴比不上天台,唐先生的客觀了解也不太夠。唐先生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是停在他二、三十歲時的程度,他那時就成熟了,後來雖寫很多書,大體是量的增加,對開拓與深人沒多大改進。我講佛教是五十餘歲,理解力當然比較高,我是經過許多磨練才能下筆的。我再舉一個故事:當時我整理宋明理學,整理朱夫子和胡五峰的文獻,在《民主評論》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對唐先生的生命起了很大的震動。有一天我去看他,唐師母告訴我說唐先生在睡覺時還在念胡五峰,這表示他知道我的了解已經超過他了。有的人對我之那樣講朱夫子不服氣,學問是客觀的,不服氣也不行呀!
我們第一步要靜下心來好好了解古典,然後按照"實踐的智慧學"這個哲學古義的方向,把中國的義理撐起來,重鑄中國的哲學。"重鑄"要適應時代,要消化西方的哲學智慧,看西方文化對世界的貢獻是什麼,我們如何來消化它,安排它。我認為做吸收西方文化的工作,康德是最好的媒介,西方哲學家固然多,但我們不能利用羅素,也不能利用海德格,更不能利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繼承而重鑄,這要年青人的氣力,我所能做的不多了。我最近把康德的第三批判翻譯出來了,康德三大批判我都已把它翻成中文,我不是康德專家,但我自信我比較能了解康德。要了解康德先要了解他的本義,第一批判講的人比較多,大家知道得多一些,第二批判講的人比較少,大家就知道少些,第三批判根本沒人講,也沒人了解。我一面翻,一面用心去了解,了解他的本義,才能消化它。以我的看法,康德確實在談問題,想解決一些問題,但他的解決問題之限度在那裏,卻只有依據中國傳統哲學之智慧才能把它看出來,中國哲學可以使康德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若康德專家只看康德,西洋人只讀西洋哲學,便未必能懂得康德的本義。英美人翻譯康德,每個批判都有三個人翻,就沒有一個人翻三個批判,他們都是康德某方面的專家,而他們不一定懂康德。我不是專家,因為我有中國哲學之基礎,所以能看出康德的本義,而且能使他更進一步。
為什麼說康德對我們重新鑄造中國哲學是最好的媒介呢?我常說"一心開二門"是哲學共通的模型,西方古代就開二門,康德也開二門。而現在西方哲學只剩一門,可以說是哲學的萎縮。"一心開二門"之工作,在西方,Noumenon方面開得不好,到康德雖稍知正視,但也是消極的。維特根什坦《名理論》又順康德的消極再消極下去,只剩一點餘波。到羅素手裏,連這點餘波都消散了,他在給維特根什坦寫《名理論》導論時,根本不提,所以維特根什坦認為羅素不了解他。因此我翻《名理論》時,羅素的導論不翻。維特根什坦的意思是凡屬於善、美等價值世界是神秘的,不可說,而凡不可說者就不說,這種態度當然消極到了極點。順此而下歐陸海德格、胡塞爾對Noumenon根本不接觸,"二門"是哲學本義,現在只剩Phenoumenon(現象)一門。中國哲學正好相反,在Noumenon一面開得最好,現象這一門開得差,這也是中國之所以要求現代化的真正原因。現代化所要求的科學民主都是屬於現象門的事,中國人以往在這方面差,我們就吃這一點的虧,所以現代人天天罵中國傳統,罵孔子。孔子那管那麼多,孔子受帶累,就是因為他沒有把現象這一層開好。其實古人把本體那門開得很周全就很不錯了,你也不要只想吃現成飯,要古人什麼都給你準備好才行。所以如果對事理有正解,就不會怨天尤人,心就會平。沒科學沒民主,科學民主也沒什麼了不起,努力去學去做就行,罵孔子反而於事無補。胡適天天宣傳科學,為什麼不去念科學,而偏要去考證紅樓夢?殷海光崇拜科學,崇拜羅素,為什麼不好好研究羅素講羅素,而只藉一點邏輯知識天天罵人?現在既然知道民主政治可貴,應好好去立法守法,不要天天在立法院瞎鬧,瞎鬧出不來民主。革命是革命,不是民主,民主是政黨政治,要守軌道。總之,科學民主都是做出來的,所謂"道行之而成",不是去崇拜的。上帝是崇拜的物件,科學民主不是崇拜的物件。中國宣傳科學民主的人把它神聖化,以為不得了,去崇拜,這些都是因無正解,故無正行。無正解正行,文化出不來,也沒有科學,也沒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