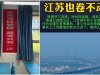人生中,有些東西像博物館的藏品,是不輕易示人的。但一遇到合適的展出機會,它便不那麼淡定了。高考於我便是如此。雖然它已遠離我近40年,其中那些讓我倍為感慨的往事,隨着歲月的流逝,也早已如同碎玻璃板中的恍影。是摯友的呼聲,喚醒了沉眠於我內心深處的點點滴滴。
一、動力
我的高考動力,源自我的童年。
我在母腹中只有17天,父親就因車禍去世了。所以,我打小頭腦中沒有「父親」的概念。稍大點後,聽見鄰居家小孩一口一聲地叫「爸爸」,我頭腦中偶爾會閃過「我的爸爸呢?他在哪裏?」的念頭。大約在我5歲時,我從來家拜年的父親的學生口中,得知父親曾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其實他們弄錯了,我父親194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機械工程系)。
這些大哥哥、大姐姐談起父親時,那一臉崇敬又痛惜的表情,開始在我心中烙下了「父親」印記,也讓我在父親與大學之間劃上了等號。從這一刻起,我對父親那種似有若無的淡淡念想,轉化為心中極為懵懂的「讀大學」念頭。這,便是我參加高考的最原初動力。
我10歲那年,大哥考上了清華大學。記得那是一個盛夏的午後,當郵遞員在樓下大喊「拿錄取通知書」時,樂開了花的母親一反平日的嚴肅,站在走廊里大聲說着「第一張表第一志願第一專業」,深怕左鄰右舍聽不見。
父親去世後,母親獨自挑起了撫養我們兄妹五人的重擔。母親的辛苦和家中經濟的困難可想而知!然而,她卻在為大哥置辦赴京的衣被時,為我們四個當弟弟妹妹的,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大哥臨行的前晚,母親讓我們穿上新衣去照相。
我好奇地問母親:「媽媽,還沒有過年,為啥要穿新衣服?」母親說:「哥哥考上了大學啊!」哦,原來上大學可以有新衣服穿,可以照相,可以一年過兩次年。要是哥姐們都考上大學多好,我就可以多過幾個年了。
大哥到北京後不久,給家裏寄來一張照片。照片上天安門背景前的七個人,清一色的補丁衣褲,全都咧着嘴笑。第二年寒假,大哥回家過年,看見他衣服上別着的校徽,我就想着戴上該有多體面。
一天,母親叫我上街交信,我悄悄取下哥哥的校徽別在棉襖上就出了門。一路上,迎着大人們疑惑的目光,我胸脯挺得老高,朝他們傻傻地笑。我纏着大哥要他講「大學」,問「照片上你的同學,他們的爸爸媽媽是幹什麼工作的?」。大哥說:一個當工人,兩個當農民,一個殺豬的,一個剃頭的,另外一個跟媽媽一樣——當老師。
大哥向我們描述清華園,學蔣南翔校長的開學辭,講70歲的體育老師馬約翰,可以一口氣做幾十個掌上壓,說學校的口號是「健康地為祖國工作50年」,因此同學們每天下午都去操場鍛煉。
大哥的講述,又勾起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化學系的母親,對自己大學生活的美好回憶:皇宮般的校舍,動作極慢但事必求精的同窗好友沈譜,課堂上提問不斷以激發學生穎思的洋教授,立志「教育救國」而獨自終身的校長吳貽芳……這一切,讓我對大學感到既親切又令人神往。
文革中斷了我的大學夢,高考自然無從談起。1969年2月,響應偉大領袖的偉大號召,全國66—68屆的初高中生(俗稱老三屆)離別故鄉,一股腦去廣闊天地「大作為」了。新三屆適時填補了校園,在演出新一輪「複課鬧革命」情景劇的同時,總算能夠坐在教室讀幾本書了。
我的兩個發小也是新三屆。每天早上,看着她倆背起書包有說有笑地奔向教室,我心裏除了倍為羨慕,就是無限惆悵。母親懂我的心思,當過英語老師的她,找出《許國璋英語教材》,從ABCD教起,還給我佈置作業,要求我每天必須完成幾道練習。
因為我家住在學校,文革來時,母親作為批判對象,抄家自然難免,熊熊燃燒的革命火焰,把哥姐的高中課本燒得乾乾淨淨。母親只好帶我到她朋友家,我鑽到床底,挑揀出一捆包括語文、史地在內的初高中課本。這一切,多少滿足了我的求知慾,也為我日後的高考墊了底。
哥姐上山下鄉三年後,我進了麵粉廠。每天早出晚歸,沒有多少時間可以看書學習。但我也不甘心一輩子再也沒有書讀,便每天背個放着書本和練習簿的包包,利用上下班的路上或午休時間,背背單詞,做做習題。
後來,廠里也曾下達過一個推薦「工農兵」大學生的名額,並動員大家報名。不明就裏加盲目激動,我很快向廠領導交了一份申請書,並表達了自己的願望。
沒有想到,在那種知識分子是「臭老九」,必須夾着尾巴做人的社會氛圍中,像我等生於「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家庭的小螞蟻,是不該心存奢望,也毫無資格和權利表達訴求的。
不甘寂寞還不自量力,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也罷。讓人鬱悶的,是隨之而來的挖苦、諷刺、奚落、惡語。嗚呼!我的大學夢,看來今生永遠是夢了。
二、備考
人的一生中,命運的轉折往往來自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機遇。1978年的高考,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機遇。我慶幸自己抓住了這根救命稻草。
1977年底,得知全國恢復高考的消息後,對大學的極度渴望,使我的內心再無片刻安寧。當時,我正參加市中區糧食公司宣傳隊的匯演,每天的「下基層」,讓我根本無暇撿起書本。焦灼中的我,天天盼着宣傳隊儘快解散。好在兩個多月後的1978年春節,我終於回到了所在單位,有了雖然有限但相對穩定的複習備考環境和時間。
我1960年6歲半上小學,1965年11歲半進初中。1966年,席捲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學校全面鋪開。我所在的重慶41中(現為巴蜀中學)是幹部子女學校。我們班的小青果們,因根紅苗壯而總是革命氣勢勁爆。但由於年紀小,他們在澎湃的革命激流中唯一能想出的造反絕招,便是控訴校領導「把我們當修正主義的苗子培養」,強烈要求「衝出牢籠,到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面」。
於是,那年的6月初,我們到近郊農村住了近一個月。這樣,我掌握的中學知識,滿打滿算也不夠一年。薄弱的知識底子和殘缺的知識結構,對於想跨越五年系統學習階梯而登臨大學門檻的我,難度可想而知。好在我平時利用點滴的時間,積累了一些知識,這讓我的複習備考有了一定的底氣。
母親得知我準備複習應考後,內心的第一反應是我沒有考上的可能。儘管如此,她卻沒有對我說過半句泄氣話,反而總是把那句「只要自己盡力就可以了」天天掛在嘴邊。母親知道我不可能報考理工科而只有報考文科,又想方設法幫我找到了兩冊老三屆的高中語文課本。
不僅如此,她還第一時間從大哥所在的自貢市趕回來,為我和二哥的備考提供後勤保障:每天早上一人兩個水煮雞蛋(她說這種吃法最科學,蛋黃的卵鱗脂能增強記憶力),每天晚上一葷兩素(母親以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們:備考也是體力活)。母親的鼎力支持,增強了我赴考的信心。
撿起常讀常新的書本,我開始了緊張的複習備考。最大的攔路虎是數學。雖然母親告訴我:數學需要系統學習,短時間內很難補起來。一想到二哥1977年參加高考,總成績雖然遠遠超出了錄取分數線,就因為數學吃了鴨蛋而鎩羽而歸,我心裏就十分惶恐,怕自己重蹈二哥的覆轍。於是,備考之初,我便將全部心血都傾注到數學上。
大姐是數學老師,我每天一下班,就趕到她家去補習。儘管如此,我的數學仍然是「扶不起的阿鬥」,近三個月的補習,仍然連最基本的數學公理都不甚了了。二哥見我滿懷焦慮,說「時間只有不到三個月了,我們要把重點放在其它文科科目上,數學只要不是零分就可以了,否則得不償失。」多虧二哥的及時點撥!戰略全局的調整,阻止了我頭撞南牆。
我所在的工廠專門生產麵粉。工廠雖然小且舊,卻事關百姓的飯碗。尤其在計劃經濟年代,糧食統購統銷的大佬地位,使麵粉廠「三班倒,班班見領導」幾乎成為工作常態。經常的加班加點,讓我複習備考的時間極其有限。
好在我的師傅比較理解我,在我備考的那段時間,她從不干預我在工作的間隙時間捧起書本。儘管如此,時間於我仍然顯得可憐,只好每天幾乎雞鳴即起。家裏就一間房,中間用上下鋪隔開,一人咳嗽全家人都會被驚醒。
怕打攪家人睡覺,公共廚房便成了我最好的晨讀場所。天氣一天天地轉熱了,鄰居家上早班的也起得早了,廚房不再是我的專利,我便轉戰到同層樓的公共廁所,雖然那裏的味兒讓鼻子受委屈,但因為氨氣能吸熱,所以廁所比廚房涼快多了。心理作用下,我感覺頭腦反而清醒,複習效果也更好些。
每天下班後的回家路上,更是我背書的絕佳時機,邊走邊背不僅腦洞大開,而且心情愉悅。於是,原來只需要45分鐘便到家的路程,便成了馬拉松漫步,一小時、兩小時,甚至三小時……
晚飯後,又是一通夜讀,結果常常是夜半還捧着書本的我,被母親反覆催促着上床睡覺。「聞雞起舞」加「鑿壁偷光」,那時的我,自感除了有懸樑刺股的辛苦,更有一種老愚公的豪邁。
三、應考
終於到了「畢其功於一役」的時刻。
1978年的高考在7月20至22日,正是「火爐」發飆的時節。一大早,母親給我和二哥煮了雞蛋和粽子,一定要讓我們都吃下去,說是怕到時肚子餓血糖低影響發揮。
早早地來到位於重慶市委對面的六中(現求精中學)的考場。時間還早,坐在操場邊的樹蔭下打開書本,想抓緊時間再背兩道題,哪裏看得進去!因為我與大姐在同一個考場,我開始朝校門張望,盼早點看到她的身影。快到進考場的時間了,終於看到姍姍遲來的她,心裏頓時踏實了許多。
三天的考試像是一場與火神的搏命,緊張、慌亂、熱得昏頭昏腦,是彼時的真實寫照。不記得心緒是何時平寧下來的,只記得試題都快答完了,手都還在抖。不記得一場考試下來用了幾條手絹,只記得來不及揩掉的汗水落在試卷上,立馬化成了一朵花。不記得到底做了些什麼題目,只記得每天考完回家後與二哥復盤,心情總在對與錯的波峰波谷之間起起落落。
記憶尤深的是,考政治,錯把「矛盾的普遍性」看成「矛盾的特殊性」,洋洋灑灑寫了半頁紙,還自鳴得意連標點符號都沒漏;答「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個理論來源」,死活想不起黑格爾,模糊記得有個黑字,靈機一動填上北約盟軍司令黑格。考歷史,不知「官渡之戰」,只好用「淝水之戰」假冒。考語文,不知「毀」應與「譽」搭配,想也沒想就寫了「毀滅」。
考地理,為答那道「一個人春天從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發,秋天到了厄瓜多爾的基多,問兩地此時各是何季節及其原因」(大意)的題,以手指為太陽鋼筆為地球的比劃,讓監考老師莫名其妙,直接給予我五分鐘的高度關注。
考數學,照着二元一次方程式解了第一道題,用時十分鐘,做對了,拿到了8分的極限分;用餘下的全部時間解第二道三角函數題,畫了一張半紙,沒有答案,得了6分。
最後一天下午考外語,想到萬里長征總算快到陝北了,心情輕鬆不少。正因此,最後那道「蘋果園」的閱讀選擇題,我沒有看仔細明白就匆忙作答,可惜了,20分的題丟分一半,否則成績該是59分了。好在外語考試不計入總成績,因此心情沒有絲毫沮喪。
考試過程中,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鄰桌的一位男士,大熱的天仍然長衣長褲,更離奇的是,他的衣袖一直覆蓋到手腕。考試進行到第二天上午,忽然教室里一陣小騷動。原來那位仁兄將答案用圓珠筆密密麻麻地寫滿手臂,被監考老師有禮貌地請出了考場。這算是我的考試生涯中,見到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小抄冠軍。
我不知道嬰兒吃奶是否要舉洪荒之力,但我能確定自己為了高考,的確拼盡了全力。繃緊的神經終於鬆弛後,我狂補瞌睡三天。
四、夢圓
考試完了,接下來的事情就只有等待,等公佈成績,等錄取分數線。當高考成績單發下時,我知道自己距離夢圓大學,只有一步之遙了。大半年「兩頭只見星星月亮」的辛勤付出,頃刻幻化為挑開生命前路中濃雲迷霧的利劍。此時的我,唯一的企盼便是能像母親那樣,實現當老師的夙願。
填報志願時,我不假思索地寫了四川省內所有的師範學院:西南師範學院(如今的西南大學)、重慶師範學院、南充師範學院。當收表的工作人員提醒我「重點大學一欄不能空着」時,我問同去的二哥怎麼辦?二哥說:寫四川大學吧。於是,照着報紙抄下了四川大學。川大不是師範,寫什麼專業好呢?迷茫之際,看到川大文科的專業目錄中,哲學系赫然列於位首,心想反正自己考不上重點大學,於是,又照着報紙抄下了哲學系。
沒有想到,僅僅過了20多天,我就收到了《錄取通知書》。那一刻,我正在車間裝麵粉。那一晚,我睜眼到天亮。那一年,我24歲。我的大姐和二哥,與我同年考上大學。
就要給自己的過去畫上句號,給未來打上破折號了。離別時,廠團支部為我們考上大學的兩位同事開了歡送會,拍了照。好友則在老舊的廠房頂,為我和師傅留下了共事五年半的歷史畫面。
踏上西行列車的那個傍晚,夜幕降臨之際,望着窗外飛掠的動景,想像未來的大學生活,心情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桃花開」。高考讓我迎來了決定自己人生命運的根本性轉機。那個終日被人牽着走,對自己的命運完全無能為力的年代,終於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