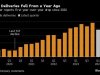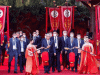脫口秀演員依然孤獨,但不再惡毒

最近,《脫口秀大會》第三季火了,倒不是因為它比前兩季好笑,而是因為為數不多的女選手講了一些女性視角的段子,讓女觀眾很解氣。是的,解氣,而不是好笑,但這已經很珍貴了。如果他們講得要是真的太「好笑」,這節目就活不下去了。這正是國內脫口秀的尷尬之處。
國內現在的脫口秀,其實是一個誤會。國內所謂的脫口秀,都是一個人站在台上表演喜劇的形式,應該叫Stand-up comedy,即單口喜劇,而不是」脫口秀「。脫口秀並不是」脫口而出的段子秀「,而是talk show——談話節目,比如奧普拉的節目。不過,為了符合大家的習慣,我們還是且將國內的這些單口喜劇稱為脫口秀吧。
從發展歷程來看,脫口秀進入中國,也遵循着所有西方大眾文化東進的規律。脫口秀從誕生之初,就深深嵌入於社會文化之中,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英國,喜劇演員在酒吧里表演,大家喝得微醺,演員也不用那麼紳士,以刻薄的方式講自己的有趣故事、以及對於政治和社會議題的見解。這種鬆弛好玩的表演很快病毒式傳播。後來傳入美國,代表人物就是馬克吐溫。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適逢香港娛樂黃金時代,脫口秀被引入香港;九十年代,正是中國台灣解嚴、社會轉型時期,脫口秀被引入台灣。在那些風起雲湧的時代,遍地都是題材,無論是香港的黃子華,還是台灣的豬哥亮,都是在針砭時弊、呈現社會百態中展露才華。可以說,政治性和公共性是單口喜劇的天然內涵。在本世紀初,脫口秀漸漸進入中國大陸,到2010年左右,誕生了《今晚80後脫口秀》等綜藝節目,再後來就是《吐槽大會》、《脫口秀大會》,脫口秀演員越來越紅,脫口秀綜藝越來越多,脫口秀自然而然也就」本土化「了。我算是這個過程某種意義上的見證者,一切還要從三年前說起。
那時,我剛到北京,人生地不熟還不闊綽,娛樂活動不多,所幸住在二環邊,距離不少平價演藝場所很近,其中一個知名單口喜劇場子就在我家馬路對面的一個胡同里,幾乎每周都有兩場,大多數時候50元一張票,開放麥(新人試練專場)的時候由於車禍現場頻發,還免費。那是個街道辦文化中心提供的小空間,滿座也就百來人,用腳指頭算算也知道,在北京,他們很難靠脫口秀生存下去。於是,他們的窘迫生活,往往就成為他們的創作靈感,他們在自嘲自黑中惡毒,也在自暴自棄中陰暗,觀眾的笑聲也充滿惡毒而陰暗的痛快。著名喜劇演員威爾.法瑞爾說:」單口喜劇是辛苦、孤獨而惡毒的「。形容那時的他們剛剛好。
這種惡毒有強烈的傳播性。我第一次去看他們演出那天,穿着休閒西裝和靴子,戴着寬檐帽,像宋莊街頭的落魄藝術家,一進去就被摁到第一排。我不知道,那是他們的」行規「:第一排觀眾都會被演員們互(tiao)動(xi)。
第一個上來的演員看着我,問:你是搞藝術的嗎?
我說:我是你們同行。
他說:怪不得單身。
我不是最慘的,我旁邊的一個女孩被調戲了一晚上,倒不是因為她是個美女,而是因為她旁邊恰好有個單身男青年,他們把」你倆湊合一下「的梗用了數十種姿勢玩到整場表演結束。
男人的性苦悶和女性的單身問題是國內脫口秀長盛不衰的題材,因為具有冒犯性,卻又不容易觸及政治敏感,有着廣闊的惡毒空間。那個現在紅出圈的女演員,有個習慣性動作:每講完一句話總是縮着脖子看着大家,生怕不好笑。當年她就是這樣的,而且當年也確實不好笑,但她的特長是靠着惡趣味和油膩,讓人迅速記住她。她像個勇往直前的女流氓,講述着生猛凌厲的屎尿屁:在擁擠的地鐵上揩身旁陌生男子的油:」小伙子,我的卵子活性很強哦「;她還學男生站着撒尿,並頂起胯部衝着觀眾來回」噓「……還有一個女演員稍微」優雅「一點,只是在台上重現自己做婦科檢查的場景。她更符合我對女性視角喜劇的想像,大概因為她主業是律師,節奏感和邏輯性非常優秀,可惜也大概正因如此,她沒有上節目。可是大多數時候,兩性的話題在脫口秀中,大概就是沒頭腦和不高興,男人諷刺女人拜金、追星、無理取鬧,女人則控訴男人不解風情、直男癌、自以為是,而男女的共同交集就是貧困和單身。
除了婆婆媽媽的生活瑣碎和兩性控訴,他們偶爾也有冒犯紅線的時候,在我印象中,有且只有一次。
那個男演員講了個這樣的段子:
」曾有一位幹部模樣的人,對我提意見:你們敢講點與時俱進的嗎?
我看着那個幹部,問:我講了你敢笑嗎?
幹部:怎麼不敢?
我說:比如,我講了,要是不好笑,我下不來台。要是好笑,回頭你一回味,說「哈哈哈那個反腐倡廉最搞笑」……卒。「
那一場表演,是我笑得最開心的一次。現在那個演員也火了,還走到了決賽,卻再也沒有」與時俱進「過。
但漸漸的,我很少再去看現場了。除了笑果乏味和越來越收縮的素材邊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們每個人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重複講老段子。他們的調戲對象,依然是第一排面善好欺的單身狗;那個男演員永遠在講停電,只不過家越搬越遠;那個女演員永遠在對着觀眾頂起跨部」噓「尿;……屎尿屁不要緊,不好笑也不重要,我困惑的是,仿佛經過這個街道辦提供的小場子的錘鍊,他們已經獲得了終生成就,再不需要新的思考和創作了,而他們也仿佛相信,前來觀看的觀眾口味獨特並且要求頗低,能被同樣的梗逗樂一萬次,不值得花心思取悅。好像以廉價的創作和拙劣的技藝,就能贏得連綿不絕的喝彩。這對於同為創作者的我來說,是非常痛心的。此外,畢竟我也窘迫,在大多數時候,窘迫者的互相厭棄遠大於互相同情。50塊錢啊,我可以花到更好的地方,可以多買幾袋螺螄粉做宵夜,或者在視頻網站充VIP,可以看到海量的國外單口喜劇。
我真的看了很多國外單口喜劇,然後更憤怒了。
在我們的刻板印象中,美國大概遍地都有政治正確的紅線,你可以罵總統,但不能取笑有色人種,不能性別歧視……可是在脫口秀里,這些紅線反而成為創作核心,什麼種族問題、性別問題、政治問題……隨手拈來,自由冒犯,往往因為發人深省的思考和成熟到位的演繹,而引發廣泛的共鳴。在國外的脫口秀中,我第一次知道原來衛生巾一直被收很高的稅,原來男人的腎結石等於痛經,原來懷孕造成子宮脫垂的人這麼多,而且這些關懷女性的段子還有不少是男演員講出來的,幽默且傷悲。他們讓我知道,其實惡趣味和屎尿屁也不一定是低級的表演,關鍵是最終抵達什麼樣的思考。我特別欣賞一位表演者黃阿麗,她是越裔美國人,天生擁有種族問題、移民問題、性別問題的題材優勢,可她要是來我們的綜藝,恐怕得從頭到尾」嗶嗶嗶「,你還以為她在表演B-box,因為她的脫口秀以肆無忌憚的屎尿屁著稱(做母親本來就是屎尿屁啊)。可她總是能適時拋出高級的總結——生活的殘酷本相,世界的荒誕,以及自由與愛。
當然,在中國當前的言論機制下,冒犯即自殺,創作只能內卷化,只能自我消耗,能冒犯的只有自己,以及自己的愛人和家人。於是國內脫口秀的主題就是:直男屌絲大戰無腦怨婦;父母皆禍害VS巨嬰我快樂;這個社會真特麼的消音消音消音……可就這麼點創作題材,稍有一點花心思的抖機靈,仍然在原創水平低下的國內綜藝界贏得滿堂掌聲。
三年前我看的小場子裏的演員們,如今都上了綜藝,粉絲也很多了。在殘酷的賽制下,他們的段子終於不再重複,但也不再野蠻生長。那個女演員不再挺起胯部噓噓,卻只因講了一個無比溫柔的吐槽,就贏得全網歡呼」快看,快看,他們終於冒犯男人了!「那個」停電男「估計也已經搬回了四環內;而那個曾經拒絕」與時俱進「的演員,開始小心並刻薄地講述人生的瑣碎,每次有一丁點越線,還會被消音。他們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躥紅了。經過《今晚80後脫口秀》《吐槽大會》《脫口秀大會》這些綜藝的努力,脫口秀終於逐漸有了大眾認知度,中國的脫口秀演員們也走出去,開始準備全國、甚至全球巡演了。他們」成功」了,這是實用主義的成功。
最近看見評論者說:中國的脫口秀要發展起來,需要1000個李誕這樣的行業領軍人物。也有人說:其實,只要少一個XX局就行了,可不知道李誕能不能活到那一天。我想李誕並不擔心,據說這個曾經的文學理想青年並不喜歡脫口秀,因為他自己也知道,那離嚴肅文學太遠,或者說,離嚴肅的思想太遠,不過,離掙錢很近。只要不油膩,也不要太真誠,更不要得罪觀眾,便能活得很好。創作者們似乎都心照不宣:脫口秀在中國,不過是這個碎片化時代爆紅和賺錢的捷徑,是實用主義的載體,它不負責傳達價值,更不需要像國外脫口秀那樣具備政治和公共性。OK,散了吧。
可是,政治和公共性並不會放過他們。就在他們借着節目大火的東風,隊伍壯大、酬勞翻倍、演出排滿的時候,疫情來了,國內外演出全部取消。他們一直逃避談論的宏大政治命題,這回一舉將他們打回原形。而他們一向奉為圭臬的實用主義,也成了拆散他們的推手:公司跟大牌演員因為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鬧上公堂,上了熱搜,解約得很難看。他們自我保護和隔絕的自黑、自棄、佛系和喪,也終於保護不了自己的靈魂——脫口秀冠軍吸毒了,永久退圈。於是,今年他們不得不更加賣命地、小心地演出,人人都謹慎且焦慮,因為他們幾乎只有這一個渠道可以掙錢了。喜劇的內核,全是悲劇。出來混,終究要還。他們依然辛苦、孤獨,但是不再惡毒,甚至也不再賺錢。
那麼,在鐵幕之下,真的不能開出喜劇之花嗎?我特別喜歡一部電影叫《笑之大學》,講的是日本二戰時期劇本審查員與喜劇編劇之間較量的故事,故事發生在七天的時間裏,每天審查員的惡意刁難都層層升級,而編劇在見招拆招努力應對的同時卻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精彩喜劇劇本。連一向厭惡喜劇、希望喜劇從地球上消失的審查員都迷失了初衷,漸漸陶醉在編劇的搞笑故事中,甚至幫助編劇修改劇本,使劇本的搞笑程度達到新的高峰。
這部片子很容易擊中這個時代的中國創作者,至少我看完之後如鯁在喉。創作人是否真誠,近了說是保持創作的生命力和初心,遠點說是在亂世中給人短暫的精神安慰,再往深了說是保持一個民族思考的活力和生活的希望。如果在至暗時刻,人人都在泥沼中掙扎,卻仍有人仰望星空,以滿腔的熱忱,為苦難中的大眾創造笑、美與善,你難道還不肯相信自由的生命終究會衝破牢籠,戰勝時間嗎?你難道仍然不覺得人間還值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