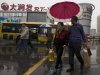作者圖|老家的胡同
故事時間:1997-2019年
故事地點:山東菏澤
一
1997年冬天,父親所在的拖拉機廠面臨清算,他選擇了買斷工齡。辦妥手續,拿到錢後,父親成為了萬千下崗工人中的一員。
父親下崗後,嘗試做起小生意,他不知從哪學了一門手藝,買了傢伙什,走街串巷賣起了冰糖葫蘆。
冰糖葫蘆並不暢銷,加之他性格木訥,不善言語,生意還沒摸清門道就黃了。這次失敗的經歷,似乎預示着父親不適合自主創業,後來他又嘗試賣水果、蔬菜,無一不以灰頭土臉告終。
那時母親剛完成了她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躍遷——由農村嫁入城裏,又順利生了個大胖小子。本以為人生就此高歌猛進,誰料風雲突變,問題一個接一個暴露。
父親失業,原本不富足的家庭一下變得拮据,生活上的壓力誘發爭吵,爭吵又升級為武力。母親不是父親的對手,每次爭吵,都是一場單方面的制裁,母親常常被打得鼻青臉腫。
那時電話還沒流行,母親挨了打,只能偷偷抹眼淚。娘家距離城裏二百里,她回不去,於是她把姥姥接到城裏,企圖給自己壯勢。
姥姥到了城裏,沒幾天就收拾包袱回去了。臨行時,她眼淚鼻涕抹作一團,哭訴道:「我一輩子沒被人這樣罵過,今天被女婿罵,真是作孽!」
母親說,就是那時,父親的病症嶄露出了苗頭,或者更早一點,只是沒有表現出來,是精神病。大家都說不清他到底有什麼毛病,總歸是精神出了問題,既然是精神上的問題,就統統算作精神病。
父親異於常人的暴躁,發起飆來六親不認。我小時候愛哭,父親對此很反感,一次我的哭聲引得他震怒,差點因此丟了性命。
「他抱起來你,就要往樓下扔,我抱住他的腿才把他攔住。」母親回憶起這段經歷心有餘悸,她補充道,「我要不攔着他,他真的會那樣做,他就是那樣的人。」
奶奶對父親的病症不聞不問,她只當他脾氣暴躁,家裏出了一個精神病是件極不光彩的事。在這樣的縱容下,父親變得更加肆無忌憚。
1999年的年關,奶奶和鄰居撮合了一桌麻將,從下午玩到了天黑。父親回來,看見母親在牌桌上,罵了兩句,動手便打。
一圈人嚇壞了,拉也拉不住,嬸嬸跪在一旁磕頭,邊磕邊哭:「哥,求求你了,別再打了,再打嫂子就死了。」奶奶和鄰居上前去拉,也被推倒在地。
那天母親被打得沒了人樣,頭髮被抓掉大片。在嬸嬸家躲了一夜後,母親決定離開這個家,回到老家去。
這一年我三歲。落寞的清晨,母親牽着我坐上了回鄉的依維柯商務車。依維柯跑得很快,二百里路,只要兩個小時,母親什麼也沒帶,我是她唯一的行李。
許多年後,她再向我說起這段過往時,我仍能真切地體會到她的絕望和恐懼。父親不光是她青春年華里的劫數,也是我年少歲月揮之不去的陰影。
二
在鄉下生活了九年後,母親還是和父親離婚了。
我在鎮上的小學讀五年級時,一輛大卡車突然來到了我家門前,車屁股後頭,兩條深且長的碾痕看不到頭。
車的主人,是我素未謀面的姑姑,她的到來是為了一件事,就是把我接回城裏。母親顯然已經跟姑姑交涉過了,我看向她,她點頭,意思是「沒錯」。
我自小在農村長大,上樹掏鳥窩,下地逮螞蚱,野慣了。聽說要進城,一百個不願意,試探着使了一通小性子,意外的是,母親沒有生氣。一陣安撫後,她平靜地看着我說:「你到了城裏,要好好讀書,考個大學。」
「我啥時候回來?」
「在城裏好,就不回來了。」
我還想多問,沒說出來的話便被轟鳴的引擎聲打斷,我祈求地看着她,問:「那你啥時候去?」
「你想我了,我就去。」母親說完,開始往我兜里塞錢,我低頭一看,是百元的面額,才意識到這一切很真實,不像在開玩笑。
「我的書還在學校。」
「書不要了,到了城裏咱買新的。」這次說話的是姑姑,她一手挎起我的書包,一手摟住我的脖子,把我塞進了駕駛室。
大卡車突突突啟動。我沮喪地蜷曲在車裏,透過窗看見母親站在大門口。夕陽下,她的身子緩緩垂下去,像五月風吹過的麥子。
車上,姑姑憐憫地看着我:「她要喝敵敵畏,把你也一起毒死。」我不願意搭話。西山的太陽落得真快,一墜一墜的,很快就掉到地裏面去。
我躺在顛簸的駕駛艙里,腦海中全是母親哭着打電話的場景。母親回村里後,父親並沒有放過她,除了隔三差五的電話騷擾,他隔兩年會回來一次。每次回來,母親都會鬧着上吊。
我知道母親不會輕易離我而去,但每次看到繩狀的物體,我仍會一陣犯怵,仿佛母親某天就會用它吊死自己。
母親從村里嫁去城裏,又從城裏逃回來,想要的無非是內心的安寧,但這份安寧不受保障。積蓄多年的怨念,終歸讓她得願以償。
她還年輕,和父親糾纏下去不是辦法,離婚是她唯一的出路。我知道她要走,心裏卻為她高興。
再見到母親,是簽離婚協議的時候。破舊的縣法院,我應要求到場。場上人很多,叔叔、姑姑、爺爺奶奶,都到了,母親只有伶仃一人。她身穿一件紅白相間的短袖衫,兩月沒見,臉又瘦削了幾分。
我站在人群里,透過來往的身影偷偷看她,她也回望我。許久,我被帶走了。臨走時,她跑過來,握住我的手問:「中午吃了麼?」我點頭回應。她又問吃了什麼。我如實回答。最後,她說:「你別恨媽媽。」
我怎麼會恨她?彼時我對離婚的理解,就是兩人分開過日子。我印象中,父親和母親一向是如此,離婚無非是給這段若即若離的關係蓋了章,大家從此了斷。
我也知道,我是母親交換自由的代價,作為一代單傳,爺爺不會放棄我,父親更不會。
那天我告別了母親,又折回城裏。車上,我和父親並肩坐着,他那時正在服用治療精神疾病的藥物,我知道這一點,所以很怕他。
父親一路沒說什麼話,倒是叔叔和姑姑說個不停,他們商量着送我去離家最近的學校讀書,問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書包。我說我想要米老鼠的。緘默的父親突然開口:「米老鼠好,我給你買米老鼠。」
三
我和父親的相處不融洽。我對他的認識,局限於母親常年在我耳邊的苦訴。她經常在夜裏抽泣,調子拖得很長,像唱戲。
我和她睡一張床。每到這時,我都會醒過來,問她怎麼了。她說沒怎麼,就是人這一輩子太苦了,接着囑咐我好好上學。有時她會講上一兩段父親的惡行,我不愛聽,但也全都聽了進去。
父親自母親走後,開始四處打工,大多時候都在飯店,做切配、傳菜,但他的確是一個沒有廚師天賦的人,在飯店混跡良久,做的菜仍色香味一樣不佔。
2006年的夏天,父親決定去外面闖一闖,他從沒出過山東。這一次,他選擇了心目中最偉大的城市——北京。但不到一個月,父親就灰頭土臉地回來了。在北京,他的手機、錢包和身份證都沒了,爺爺托在北京做事的親戚找到他,給了他回來的盤纏。
回來後,父親跟爺爺奶奶講他差點被人迫害:在北京、火車上以及回家的路上,都有人盯着他,只等他一個不留神,就要結束他的性命。
父親不吃飯,把自己鎖在屋子裏。奶奶做了飯,將碗放在門外,他動也不動。他懷疑飯裏頭有毒,認為奶奶要害他,站在陽台上破口大罵,罵得街坊鄰里引頸側目,才肯罷休。
父親的情況屬於躁鬱症,他開心的時候就像孩子,不開心的時候像個瘋子。更多的時候,他是沉默的,就像一塊沉在水底的木頭。
到2008年,和母親離了婚後,父親的性情才穩定了一些。夏天,我在電視前看奧運會,他就在一旁寫毛筆字。正楷,他寫得很工整。逢年過節,父親慣例寫一些紅底黑字的對聯貼在門上,餘下的會送給叔叔。閒暇之餘,他也畫水彩畫。
我們兩個話都不多。我原本性格內向,來到「新家」後,變得愈發沉默。初來乍到,我沒有玩伴,也沒有同學,每天靠着一台舊電視殺時間。電視只有三個台,兩個地方台,一個中央台,內容反反覆覆。
有一天,我在胡同里撿到一隻狗崽。這隻狗被人虐待過,尾巴上已經沒有了毛皮,沾滿了灰土。它瑟瑟地蜷在牆角,兩隻眼睛血紅。我用手去摸它,它只一個勁地顫抖。
我用衣服把它兜起來帶回了家,用紙箱子給它做了一個窩。看着它,我心裏難受極了,對它說:「土狗好養活,你也要堅強一些。」
父親回到家,發現了它。我還沒開口解釋,它便被他一隻手抓起,舉過頭頂,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呆住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狗很頑強,被摔了一記後仍吭吭唧唧,不肯死去。父親見狀,拾起來又是一記重摔。這下它死了,在地上翻滾一下,再沒了動靜。
我不知道一隻狗何以引起父親的暴怒,從他的罵聲中我得知,它太髒了,得處理掉。我說讓我來。
我從地上撿起狗放進紙箱,觸到它的肚皮時,還有鮮活的溫度。端起箱子往外走,出了門,我的身子止不住地顫抖,眼淚撲簌簌往下掉。看着箱子裏面的狗,我張着嘴想:「下輩子再來找我吧,等我有了自己的家,就能養你了。」
那天我迎着夕陽走了很遠,走到了一處大堤,堤兩側都是不具名的墳頭,我放下紙箱,用手扒開一處泥地,用樹枝刨了一個坑,來往的一個大爺見我在埋狗,說:「這麼淺可不行,埋得深一點,它下輩子就能做人了。」聽得我眼睛又一酸。
埋了狗,謝過大爺,我漫無目的地往回走。夕陽掛在我身後,把影子拉扯得很長。對夕陽,我滿心恐懼。當太陽落山,父親就要下班回家,我們要共處一室,並且躺在一張床上睡覺,對此我本能地抗拒。
回到家,我才發現丟了鑰匙,父親開了門,問怎麼回事,我說鑰匙不知道丟在哪裏。沒等我說完,父親就開始罵罵咧咧。罵了幾句,又揚手一下、兩下地往我的腦袋上打。那是我第一次被父親揍,打完他就轉身鑽進屋子裏做飯。
以往我也常被母親揍,她的巴掌決不亞於父親,我從不覺得難過,但這次我感到委屈。這時我才意識到,原來我對父親天生就帶有敵意,母親多年的屈辱,更滋養了它,讓它在我的血液里肆意流淌。
從那時起,我有了個念頭,我認為我來到父親身邊,就是為了一雪母親的深仇大恨。我突然接受了父親的確是個精神病人,母親敗給了他,我該帶着她的意念繼續跟他抗爭。抗爭的方式,就是互相折磨。
我開始刻意抗拒有關父親的一切,被他打罵,我故作雲淡風輕;外人談及父親,我閉口不提;緊急聯繫人、親屬一欄,我寫上的只有母親。後來母親改嫁了,我又把聯繫人改回父親,只是手機號碼永遠填錯一位。
四
暑假過後,我就讀於一所離家很近的小學。城裏的教學比農村先進,我卻被遠遠落下了,幾門功課一塌糊塗。
父親對我的成績並不關心,在他看來,世上沒有穩定的工作,但真正餓死的人不多。他總有意無意地催促我儘快為家裏掙錢,常說:「你畢了業就去飯店端盤子,干久了就轉到後廚,從切配,到廚師,飯店裏頭吃喝不用愁。」
我不敢反對他的任何意見。曾經有一次,我頂撞了他,他指着大門說:「滾到外面去,不要回來了。」我被趕出門,從黑漆漆的胡同走到路燈底下,又沿着燈光走到了一處公園,在公園的長椅上躺了一夜。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學,放學後父親已經等在門口。他看見我,滿臉怒氣地走過來,啪的一巴掌蓋在我頭上:「你覺得自己牛逼了是不是?」我不敢說話,也不敢動。來往的同學很多,對着我指指點點。
記得從那以後,我開始厭惡上學。一開始我不明白,以為這是學生必有的心理。後來,我走向社會、與人打交道,才緩緩從那一記巴掌里回過神來:我並非討厭上學,只是討厭一切人多的場合。每每遇到,我都會壓抑得像馬戲團里鑽火圈的獅子。
彼時我生活中唯一能感受到的溫暖,來自爺爺。他是個老工人,多年的勞作在他的手上留下了永恆的記號,他常用那雙槐樹皮般的大手抓住我的手腕,給我講林衝上山的故事。
但我為爺爺的婚姻感到悲哀,因為奶奶十足霸道。她對爺爺的統治,無異於父親對我。我經常能從爺爺渾濁的眼神里看出壓抑和無奈。
即使強勢如奶奶,也拿我的父親沒辦法。父親肆意而為,完全不講倫理和章法。一次吵架,父親指着奶奶鼻子破口大罵,她氣不過,揚手給了他一記耳光,卻被父親抓着頭髮扯倒在地。
我站在一旁,看見奶奶無助地躺在地上,突然想到了母親,恐懼使我動彈不得。
我試着拿捏父親的性子,規避和他發生矛盾的任何可能。他一回來,我就靜靜呆坐着。有一次他下班,一進屋就開始罵:「狗日的東西,要你有什麼用!」他給了我一巴掌,我才知道原來是水龍頭沒有擰緊。
等他罵完,我才鬆了口氣。洗把臉,照了照鏡子,我躡手躡腳地出了門,去路邊的小賣店給母親打了個電話。母親在電話里問:「你爸打你沒有?」我說沒有。她說沒有就好:「有的話就告訴媽媽。」
我知道,我們都拿父親無可奈何。「他要是打我,」我打斷母親的話,「我就還手跟他打。」
母親突然沉默了:「那你不就跟你爹一個樣了。」我聽罷,掛斷了電話。付錢的時候,淚突然掉了下來。電話鈴聲在我的身後不停地響。老闆說:「快接吧,接電話不要錢。」我吸了吸鼻子說:「不用了,讓她打吧。」
那個周末,母親過來看我。她穿了件寬鬆的黑色外套,卻沒能掩蓋腹部隆起的事實,我不知道該怎麼問。當然我不問,她也不會主動說。
我在汽車站等她。出了車站,我們沿着馬路走了很久,去一家麵館落腳吃了面,在街邊買了兩件新衣服,又折回車站。
她說:「你回去吧。」我問她:「我去哪兒?」
「回家吧。」我從她手中接過袋子,轉身往候車廳外走。走到門口,我回頭看她,她也在看我,我沒有說話,徑直走出了大廳。
袋子裏塞着新買的衣服,底下是兩個蘋果,一瓶酸奶。走了沒兩步,我突然停住腳步,拿出較大的那個蘋果啃了起來。
候車廳有很多台階,我儘可能讓自己站得高一些,這樣母親就能看到我。我期待她走過來,問我為什麼還不回家。如果她這麼問,我就會告訴她,我不想回去。
我啃得很慢,啃完了蘋果,我又不緊不慢地喝奶。等到奶也喝完了,我開始不安。心想,這會她一定已經走了,我懊悔自己沒有站得再高一些。走到門口,我順着來往的人群往裏張望,剛才分別的地方已經空了出來。
五
高二那年,我輟學了。
有兩天時間,我沒去學校上課。早晨出了門,我便騎車去學校附近,鎖了車子後,就在周郊溜達。第三天,我又去了學校,跟班主任說我要走,今天是來跟他告別的。
班主任人很和善,任教語文,我私下裏常寫一些作文給他,他每次都寫很長的評語。這時他問我要去哪兒,我說我也不知道,就想離我爸遠一點。
但輟學後,我並沒有離開父親。我發現我沒有足夠的錢,也沒有足夠的能力,甚至沒有足夠的年齡。
我在父親曾經工作過的飯店打工,工資一月900元,後來又去一家洗浴中心擦皮鞋,一月拿1500元。每次發工資的時候,我把錢如數上交,以換來短暫的平靜。多年的相處,我已經適應服從他,表面上越來越溫順。
父親常說:「我現在養你,我老了,你就要養我。」我說我知道,但扭過頭,就在心裏多次把他拋棄,我沒法想像和他糾纏一生。
那時我已經長到了一米八,足足比父親高出一個頭。他的脾氣仍舊古怪,嘴上罵罵咧咧,巴掌卻不再夠得着我了。
望着逐日矮小的父親,我常想,或許是搞錯了呢?或許我根本不是他的種?這種罪惡的念頭讓我既興奮又羞愧。當我站在鏡子前,我又安慰自己:「他是愛我的,只是用錯了方式。」
我學着像父親一樣寫日記。他每天都寫,有時是洋洋灑灑的一篇,有時是三言兩語。不少時候,我都會想一睹他的生活中究竟都發生了什麼,讓他脾氣如此惡劣,言語刻薄。
有一次我偷偷翻開,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寫的不過是生活種種,如「某月某日,交電費XX……」我在父親的日記里既看不到他生活的瞬間,也找不到他對人生的任何感悟,只有一頁頁枯萎的昨天,乾巴巴如一捏便碎的秋葉。
在日記里,我除了記錄自己,也常記錄父親,記錄我與他之間的不和睦。我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與自己對話,為生活中所有不期而至的壓抑找尋出口。寫着寫着,我們的嫌隙仿佛變小了。
譬如我常這樣在筆下問自己:試問天底下有哪個父母不打罵孩子?答案當然是沒有,我於是開悟般點頭,父親的行為便仿佛合乎了常理。
2015年除夕,父親突然興致沖沖地要我喝酒。我們兩個圍着一盤餃子、一碟花生米和一道黃瓜豬耳默默苦飲。我喝的少,父親喝的多,喝着喝着,父親就醉了。
他面色潮紅地胡言亂語,說對不起我們娘倆。我說:「你喝醉了,不要再說這種話。」夜裏,我站在陽台上抽煙,父親在屋裏看春節聯歡晚會,他被小品逗得頻頻發樂,我突然想起了母親,給她編輯了一條問候短訊。
等父親睡了,我照常提起筆,打算告別一年的種種。思索良久,卻不知該從何寫起,我輕輕取出牆角的不鏽鋼盆,將日記一頁頁撕下,不消兩分鐘,火萎了下來,紙灰就着水被衝進了下水道里。
年後的春天,我成為了一家工廠的業務員。工廠的業務遍佈南方各地,我第一次離開了父親。他說要騎車送我,我沒同意,自己打車去了車站。
躺在火車的上鋪,我的身心莫名感到愉悅,當晚一夜無眠。燈早早熄了,車廂里很安靜,窗外是飛馳的萬家燈火。
我想起那天分別的時候,班主任對我說:「你不能帶着恨意去生活。他畢竟是你爸,你不能這麼恨他,你該試着去愛他。」
我可以不去恨他,但他愛我嗎?記得上初中那會,父親雖然工資不多,但我喜歡吃肉,他就每天買一斤,牛奶也沒斷過。基本上的,我喜歡吃什麼他就會反覆地買。大概也算是一種偏執的示好方式。
成為親人我們無法選擇,他並非天然會愛人,卻永遠知道你身上最痛的位置。那種惡毒,就像飯里的砂礫,「給人一種不期待的傷痛」。
如今我很少和父親聯繫,他百分之八十的來電,我會不接。其實我從來沒跟他達成和解。乖巧是假的,乖張是真的,每個人有不同的人生軌跡,設身處地的理解,是一件奢侈的事。
我們是父子,但關係也僅限於此。
-END-
作者王陽,自由職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