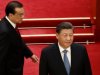故鄉利川,看地圖在中國的中部,但給人的印象卻是十分偏遠。它是鄂省伸進渝界的一隻腳,且是湖北海拔最高的一個縣治。在古代,這裏乃巴國的腹心,也因此民俗至今猶帶巫風。巴國亡得太早,沒有留下什麼太值得一說的典章文明,於是自古以來,這裏的人民就被視為化外蠻夷。
我在最近所寫的利川賦里,這樣描述它的區位——荊南重鎮,鄂西雄關;土苗邊城,尊名利川。河山橫斷,北枕峽江夔門之險;風物卓異,南控瀟湘武陵之源。巴人祖居,西鄰涪萬峻岭;楚國故地,東下江漢平原。天接湖廣以遠,南北植物交匯;地托雲貴之高,東西經濟界連。人文介乎蜀楚,民俗肇自夷蠻——看上去似乎不免有因故土情懷的溢美,但仔細考察,卻也能大抵坐實。
我出生於本地汪家營鎮屬下的魚泉口村,那曾經是川鄂兩省的界碑所在。據說從我家賃居的老宅走出去百步,就進了渝地的石柱縣。可是我在利川生活了二十幾年,竟然卻從未去看過那個傳說中兩省趕集皆匯於此的老街。我大約兩歲多便被父親用籮筐挑出了那裏,因此記憶中毫無屐痕。也因為即便在利川,它也算艽野僻地,所以一直到背井遠遊,都未曾去回顧過那個民間稱為「西流水」的小村。
去年返鄉,兩個姐姐和我要走一趟重慶,不經意間開車忽然就經過了這裏——全家一別45年的地方,大姐還依稀能辨認。她急忙叫停車,大家一起下來站在公路邊。路畔是向西流的河道,卻已枯瘦如淚痕;河對岸便是一排老式的土家吊腳木屋,大約也就只剩百米長度了。看得出來,幾乎每一家都是頹壁殘垣,全無人間煙火象。不到半個世紀,一個曾經喧譁的古鎮,就這樣悄然地土崩瓦解了。
隔着時間的暗流,大姐遙望着風物迥異人事全非的對岸,眸中含淚喃喃自語——我們家就是那個老屋,那是甘家的大宅,那時是這裏最好的吊腳樓啊!完全看不出來了,那些人呢?他們去了哪裏?怎麼會整整一條街就搬空了呢?河水怎麼也不見了,童年上學,爸爸每次都要目送我過那個橋,那時覺得這是好大的一條街一條河的,怎麼現在完全不像了呢?
對於有記憶的兩個姐姐來說,目睹這樣滄桑的故地,遙想那些艱難卻舉家齊全的溫暖日子,此際必定是殘忍的。而我,似乎連夢境中都未浮現過這個陌生的荒村,幻想過多年的小橋流水人家,突然直面的卻是這樣的一片荒涼,心底竟有幾分不敢相認的漠然。
但我深知,曾經的合家居留是命定的存在。我的胎盤肯定按鄉俗,也曾懸掛在對山的某棵樹上;襁褓中的初啼毫無疑問曾經喧囂過這個死寂的夜空。而今中年還鄉,早已無從辨認哪一棵樹是父母的手植,山谷中怎麼也無法聽見昔年純淨咯咯笑聲的餘響了。我更無法想像,外婆父母的亡靈,如果真如傳說需要回收他們在人世間的腳印,他們又該怎樣再次翻越千山,來重覓這個黑暗的青石深巷啊。
二
不管怎樣變遷荒蕪,我以為,有故鄉的人仍然是幸運的。
許多年來,我問過無數人的故鄉何在,他們許多都不知所云。他們的父母一代是有的,但到了這一代,很多人都把故鄉弄丟了。城市化和移民,剪斷了無數人的記憶,他們是沒有且不需要尋覓歸途的人。故鄉於很多人來說,是必須要扔掉的裹腳布;仿佛不這樣遺忘,他們便難以飛得更高走得更遠。而我,若干年來卻像一個遺老,總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詩酒猖狂之餘,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鄉愁。
故鄉一詞所能喚起的溫馨,非僅其風景全殊,乃因那一曾經的所在,有着自己牽腸掛肚的故人。即便歲月淘換,如杜詩所說「故人日以稀」;甚至還鄉的道路盡頭,最後只剩下你自己悽惶的影子在夕陽下捲曲着往事;那故鄉依舊還是足資埋骨的。我的故鄉過去傳說的趕屍佬,就是要把那些充滿鄉思而流落異鄉的遊魂,千里迢迢也要接回家山。可見從屈原開始,我們那一帶的人都有懷鄉癖。
楚文化向來巫風很盛,與齊魯的史官文化對應,可以稱為巫官文化。溯其源自,這種巫風大抵應該出於山地民族的巴人。巴巫並稱,就像今天地名存留的巴東和巫山相對一樣。巫是一種神媒,可以通過歌舞而溝通自然與神靈。巴人【今土家族】的巫風傳承由來已久,雖經歷朝羈縻壓制,但在我的童年,還能在鄉下尋常感染到那些神秘民俗。
巫師在我們當地又叫端公,似乎是因為他們做法事時的一個重要儀程而得名——他們要把燒紅的犁鏵用赤手端起。端公有很多法術,於少年的我常常是無解的。但經常的耳濡目染,往往也深入心靈。記得有一個端公的兒子,因為時代原因不能繼承父業,只好當了工人。就是這個會念咒止血的大人曾經對少年的我說——如果你長大後不能讓家鄉揚名的話,那你就沒有資格埋葬在家鄉。
也許他原本只是在對我進行一種理想教育,對我而言,卻似乎被一個古老的咒語所鎖定了。若干年來,我幾乎行遍天南海北,用哥們馬松的詩句來形容——把天下道路走成了拖鞋——但是我依舊未能走出這一咒語的情結。如果我不寫出那片土地上的故人故事,有幾人曾知那一窮荒僻野,更有何人知道故土上那些真切的榮辱悲欣。如果沒人知道那些默默無聞而又可歌可泣的地名和人事,那我若干年的寄生和成長豈不是一種虛無和負罪。到真正樹老葉落之時,我確恐無根可歸了。
三
二十三歲的我自以為霜刃在握,可以問劍江湖了;收拾琴書,倉促揖別故鄉山寨,兀自闖入了別人的城市。那時的人知道敝鄉的甚少,不免要多費口舌才能說清洒家的來路。我曾經在一首詩里說——君問深山深幾許,無言我自上層樓。浮雲有盡家何在?曠野無垠望不收。落日猶從嶺樹墜,大江原自故鄉流。幾回遙指雁歸處,迷眼峰巒即首邱。
九零年代中旬,劫後孤身再來到別人的首都乞食之時,故鄉偶爾也曾遺忘在出逃的路上。那時確確乎只剩兩袖清塵了,胸中的萬古長刀早已為險惡世事所磨損。我借住在朝內小街南拐棒胡同某大雜院的一個偏房裏【梓夫說是肖復興的舊居】,初次深刻地體驗了北方冬夜的刺骨。那時,我常想起沈從文初來北平賣文時,郁達夫第一次去拜訪這個來自邊城的無名作者,看見他吸納着清鼻涕,用長滿凍瘡的手在抄寫稿子。郁達夫臨別不忍,掏出僅有的幾個大洋放在了桌上。每每在深夜想起這個故事,總要惹清淚幾行——人世間的滴水之恩,於異鄉人來說,都是可以濕透青衫的。
十年京華廝混的我,久疏了故人,故鄉也在望眼中迷離而稀薄。至於身經的故事,在一個杯弓蛇影的時代,只能悄悄地刨土埋存。楚人聞一多的詩句謂——有一句話說出就是禍,有一句話能點得着火,別看五千年沒有說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緘默?——我想那時首善之區的酒色燈影,正漸次漂淡着我的恩仇。
一個打小便奢望文章立命的男人,被青春革命的洪流所裹挾,幾番載沉載浮之後,在一個憲法號稱出版自由的國度,卻可能要以一個「不法書商」的身份終結餘年——這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都顯得荒誕而悲劇。出山又二十餘年,上半截心腦埋在故土,下半截身子飄蕩在異鄉;每每半夜酒闌,我像傳說中的某個厲鬼,要對廣場的華燈在心底高喊——還我頭來。
一轉眼驚青鬢雪,再回頭俟黃河清。轉顧半生來路,學殖荒疏而馬齒徒增,如何敢面對那一方日漸淪陷的故土啊;那些失散的親友故人,那些漫漶風化的人間故事,都在暗夜裏鞭策我幾近麻木的神經。於是,終於在零六年的國殤日,我決絕地揮別了京門。垂老投荒,原只為心中還耿耿然豎着一支狼毫鬥筆,那上面濃濡着的陳年血淚已然如漆。世道往還,該輪到我們這一代潑墨大書了。否則,歷史還將被他們再度姦淫且舉國旁觀而默默。
四
為了還債,終於完成了第一個散文集《江上的母親》。大陸祖國聽慣了廣場上整齊劃一「首長好」的歡聲,自然難以容納人民之一的悲語;好在台灣祖國還肯傾聽同胞的呻吟,於是才有了平生初選的這一部拙著。
同一個祖國,因為分居於各地,人民的權利便相隔雲泥。香港祖國的出版家,深知大陸出版的艱難,為了讓更多的朋友讀到我的故鄉,又再度編次了我的選集。原本叫《塵世輓歌》的這個冊子,增添之後更名為《拍劍東來還舊仇》——書名來自於我多年前的舊詩——兩袖清塵一枕愁,飄零身世等浮漚。白頭休廢名山事,拍劍東來還舊仇。成語中的野人獻芹,似乎確能暗合我此刻的不合時宜。
寫完了母親之後,我便開始寫父親。父親這個遭遇毀家滅門之痛的巴人之後,卻成了共軍土改剿匪的英雄——這在我的年輕時代看來,確實有些匪夷所思。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他飲恨加入的那個道門;卻在最後時光的探監時對我說——理解了我的選擇。而我,也在近年來對黨史的尋幽索微里,理解了他當初的抉擇。
命運從來都是不由自主的,況乎身在江湖。在拙著《父親的戰爭》裏,我想極力反思的土改,所要追問的匪患匪源問題,結果都在有司的閹割下,變成了一支荒唐的主旋律。我擔心父親的亡靈在天上不肯瞑目,怕他罵我作踐了這一堂好人物。於是,我不得不把劇本再次轉變為小說,藉以還原我的創作初衷和歷史真相。
就長篇來說,這是我的處女作。同樣的故人故事和故鄉,構成了我的敘事。筆下的每一個人物出於虛構,似乎又源於父親的身世和故鄉的種種傳說,源於我們漸漸釐清的鄉村史實。故而下筆有情,無論正邪敵我,我都把他們還原為人在寫——這個世界原本只有人,敵人只是各種時代的政治定型而已。我們時代的文學,只有在進化到一視同仁的時候,似乎才具備了人性和神性。
現在這部長篇也終於在大陸面世了,可惜由於受了劇本結構的影響,拙著在這裏顯得近乎通俗——不免沉陷於一些懸念衝突和對白之類的技藝。於純正的文學而言,我實感汗顏。如果有心的讀者仔細品味這些關於個體的悲劇和時代的厄運等等,也許還能諒解我的粗糙。在是非恩仇二十年的特殊年份,能夠同時推出這樣三本書作為祭奠,於我肯定是欣慰的。我相信我所有親長的亡靈,還有漂浮在祖國上空的無數冤魂,都會為此而略感慰藉。雖然還未報人間已伏虎,但總有那麼一天,他們會「淚飛頓作傾盆雨」的。正是基於這樣的堅信,我才願如此苟活於斯頹世。迅翁當年寫完一部書之後說——窗外是進行着的夜,無窮的遠方,無窮的人們。我在生活,我還將生活下去。——這樣的中年情志,我於現在,算是略能體悟了。
這個世界多的是著作等身的人,幾部微著的出爐,遠不值得囂張。之所以還要添足這樣一個註腳,的確是要向讀者諸君謝恩。說實話,沒有這些年你們的鼓勵獎掖,我真難有激情自說自話。迷失於這個時代的同道,往往只能拿文章當接頭暗號;仿佛前生的密約,註定我們要在今世扺掌,然後一起創世,或者再次站成人牆,慷慨赴死。
2010年6月22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