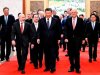2012年的暮春三月,地上還有積雪。17歲的男孩李夢南最後一次一瘸一拐地走進了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他來自內蒙一個偏遠的小鎮,到哈爾濱要坐十小時的火車。為了治療他的強直性脊柱炎——一種讓人備受折磨的炎症,這已經是他兩年內第六次來哈醫大一院,但是在看病的兩年間,他的病症日益嚴重。當天早些時候,醫生讓他穿過市區到另一家醫院去照X光並把結果拿回來,但當他回來後,醫生又告訴他由於他有肺結核病史,他的脊柱問題無法得到治療。李夢南白跑一趟,不得不徒勞無功地返回內蒙。
隔着幾條街的地方,該院的一名叫王浩的28歲實習醫生正匆忙趕往醫院。他離開公寓時,房東問他「去吃飯呢?」王浩說他晚些吃,因為還要趕到醫院去上晚班。他到達醫院後,他的朋友,風濕免疫科的護士張曉中正準備下班。王浩問她明天是否有空一起吃晚飯,他們經常約吃飯和唱K。兩人剛剛結束過年假期從家中返回,這正是聊聊近況的好時間。
與此同時,李夢南和陪他來看病的祖父李祿一起回到了醫院街對面的小賓館。李祿躺下小憩,而李夢南對爺爺說他想出去走走。實際上,他到了旅館附近一家雜貨店買了一把7公分長的水果刀,並再次返回了醫院。他坐電梯上了五樓,到之前被拒收的風濕免疫科。他沒有任何計劃。後來他說當時想找拒絕治療他的那個醫生。但當他走出電梯後,他徑直走向了他看到的第一個穿白大褂的人。他把刀深深地捅進了王浩的脖子,彼時王浩正坐在電腦旁。醫務人員圍了過來,李轉身朝他們走去,割傷一個醫生的耳朵和面部,劃傷了另外兩名工作人員。他隨即試圖自殺,但是這把廉價刀質量不好,他只在脖子表面劃了一道傷口,並傷到了自己的手。見自殺失敗,李轉身逃跑。
李祿後來記得,他的孫子從旅館房門走進來,捂着喉嚨,鮮血從指縫中湧出,浸濕了他的毛衣和牛仔褲。「我不想活了。」李夢南說着,倒在床上。他爺爺用衛生紙和床單給他包紮了脖子和手,並帶他回到了對面醫院的急診室。在他接受診治時,同在急診室的那個被他割傷的醫生認出了他,於是他很快被捕。同一時間,在醫院大廳另一頭的ICU病房中,王浩被宣佈死亡。
哈醫大血案震驚了全國。衛生部長要求嚴懲兇手。四個月後,李夢南接受審判時,政府罕見地向媒體開放了庭審。《財新》周刊談到了中國的「醫患衝突」,而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的一位編輯則警告稱,「中國的醫生正身陷危機。」
在中國,針對醫生的暴力已司空見慣。2011年9月,北京一個書法家對喉癌的治療不滿,連刺一名醫生十七刀。2012年5月,南京的一個女人持刀攻擊了一名年輕的護士,原因是她六年前做的手術現在出現了併發症。今年二月的接連兩周內,南京有一名護士被毆打致殘,河北的一名醫生被割喉,還有一名醫生被人用自來水管毆打致死。中華醫院管理協會的調查顯示,從2002年到2012年,傷醫事件平均每年比去年增加23%;平均每家中國醫院每年遭受27起襲醫事件。
隨着哈爾濱襲醫事件更多細節浮現,媒體對殺手的描述變得溫和了。李夢南不是瘋子,也沒有暴力史。他是一個完全被社會所拋棄的人,被絕望驅使着施暴。王浩的死象徵着醫患關係坍塌,以及中國醫療系統的基本運行出現了問題。
一位叫魏良岳的律師接手了李夢南的案子,我到他哈爾濱市區的辦公室拜訪了他。他的辦公室位於一棟褐色建築的四樓,前門十分厚重,大廳則配有一個保安。魏五十歲了,但看起來依然年輕。他任律師以來主攻人權方面的法律,為此他吃過很多苦頭。在李夢南案庭審期間,魏剛從被關了26天的勞教所回來不久。2009年,由於他擔任內蒙古法輪功參與者的代理律師,他和妻子被哈爾濱警察拘留了一個月。從那時起,他就對爭議性的案子很緊張,不敢接手。但是當一個同事問他是否願意為李夢南辯護時,他立即同意了。他說,當他第一次聽說媒體對此案件的報道後,他想:「為什麼這個病人會選擇這樣(極端的)手段呢?」
魏和李方平一起工作,後者也是人權律師,最近剛代理了一個維吾爾族學者的案子。魏和李只能在審判開始前的一點點時間裏見到他們的辯護對象。坐在看守室里,李夢南沉默無語,心事重重。李方平被這個青年沒有生氣的樣子震撼到了,他說:「我感覺他完全是一片空白。」
公訴方要求判處終身監禁,這是對未成年犯罪的最高懲罰。但是隨着魏和他的團隊對李夢南的案子了解越深入,他就覺得李夢南越像一個受害者。他們決定圍繞着醫療系統反覆讓李夢南失望這一點來辯護。儘管李夢南不應該起了殺心,但是「醫院的忽視、過度醫療以及糟糕的服務是這一悲劇發生的主要原因。」
李夢南出生於1994年,在內蒙古一個叫大楊樹的小鎮長大,該地以草原與煤礦聞名。父母在他一歲時就離婚了,隨後父親外出打工,他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三歲時,李的父親因為搶劫入獄。李夢南學習不好,他的中學老師就把他勸退了。15歲時,他到北京和姑姑一起生活。他向一個成年的朋友借了身份證,到一個澡堂給人搓澡,每個月最多掙七百塊錢。
幾個月後,他的腿開始疼。他去了醫院,但付不起全部化驗的費用,只好離開北京返回家鄉,但是鄉鎮醫院沒有專科治療,許多甚至沒有基礎的醫療設備。2010年9月,李夢南和爺爺熬夜搭乘十個小時的火車到哈爾濱,那是離他家最近的大城市。
像中國所有頂尖醫院一樣,哈醫大一院人滿為患。醫生診斷他的病為滑膜炎,並給李夢南注射了一套藥物。結果卻證明這是一次誤診,魏在庭審中辯護到這一錯誤的治療加重了李夢南的病情。
第二年春天,醫生開的藥很明顯沒有療效。正處在青春年華的李夢南走起路來像一個老頭。他的祖母后來告訴記者:「他上廁所的時候甚至蹲不下。」。4月,爺爺又帶他返回了哈醫大。這次的診斷是正確的:他得了強直性脊柱炎,這是一種長期炎症疾病,能導致脊柱的完全融合,形成「竹節脊柱」。
他的病無法根治,但是醫生說他的症狀可以通過靜脈注射藥物「類克」治療。對一個貧窮的中國家庭來說,一療程三萬九千元的注射費如同天文數字。作為一個北漂農民工,李夢南有一點保險,但是只能報銷不到一半的金額,他治療總共花了八萬塊錢,剩下的必須自掏腰包。他們從李夢南的福利補助金和爺爺的養老金中拼湊了一部分費用,並向家人和朋友借了剩下的錢。
在經過第一輪「類克」注射治療後,李夢南立刻感覺好多了。他在家中的院子裏奔跑,並對奶奶喊着:「看,我能跑了!」但是一個月後,醫生發現他患有肺結核——這可能是由於「類克」削弱了他的免疫系統導致的。醫生告訴他,他們不得不停止注射類克,直到肺結核治癒。在李夢南的辯護詞裏,魏認為醫院在給李夢南注射「類克」之前就檢測出了肺結核,暗示醫院之所以沒有事先說明這一點,是因為「類克」售價不菲。
在繼續開始治療脊柱之前,李夢南不得不住院四個月,口服抗肺結核的藥。據他爺爺說,在此期間李夢南開始表現怪異。他會突然大笑,在晚上遊蕩並大喊大叫。即便如此,當爺孫倆最後一次返回哈醫大一院時,他們是樂觀的。但是肺結核還沒有完全康復,「類克」的注射將再推遲三個月,這樣的消息絕對是一大打擊。所以醫生沒有直接告訴李夢南這一壞消息,他讓李夢南站在辦公室外等候,把消息告訴了李夢南的爺爺。根據魏的表述,這時候李夢南感到受了侮辱。他告訴我,「李夢南的想法是:『這些醫生在耍我玩嗎?』他只知道他已經來過這裏很多次,每次他得到的結果都是『不行,不行,不行。』」
扁鵲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醫生之一,他生活在公元前5世紀,是一個有神話色彩的人物,以其洞察人體結構,起死回生之術而聞名後世。但他在其所處的的時代並未得到賞識。有一次,他告知齊王面有疾色,齊王聽了,懷疑扁鵲圖謀他的錢財,就把他給打發走了。但幾天過後,齊王果然就死了。公元2世紀的華佗也是一位名醫,擅長外科,他曾向曹操建議做開顱手術切除腫瘤,後者卻懷疑華佗意圖殺害他,將華佗處死。這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暴力襲醫事件之一。
儘管中醫歷史悠久,從醫人員卻並未有良好的待遇。儒家思想認為君子都應當具備足夠的醫療知識,來照料自己的家庭,並且認為即使是最優秀的醫生都應當處於社會底層。清代醫學家徐延祚鄙夷當時的醫療水平,他曾寫道:「真病死的人不多,多數是醫死的。」
現代醫學發端於19世紀的歐洲和北美大陸,在中國的傳播相對滯後。到了20世紀,醫生使用的還是傳統中醫和現代醫學並存的治療手段。直到1949年共產黨執政,中國政府才挑起了建立醫療制度的擔子。普及疫苗接種,改善衛生條件,發起除四害運動(蒼蠅、蚊子、老鼠、麻雀),這一系列措施限制了疾病傳播,也降低了兒童死亡率。1965年「文革」前夕,共產黨發出倡議,為每個生產大隊配備一些經過培訓的醫療人員,他們一面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一面為社員治病。這些所謂的「赤腳醫生」以當地農民為主,也有一些是城市來的年輕人。以西方的醫療標準看來,他們不過是業餘水平,但至少這一制度給中國農村提供了基本的醫療資源。十年後,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51歲延長至65歲。
一些赤腳醫生日後堅持行醫,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劉國恩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北京大學中國衛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我便是在這所學府與他會面的。他的辦公室位於一幢金碧輝煌的清代建築內,一側鳥瞰庭院,另一側俯視河流。「這裏風景獨好。」他咧嘴笑着說道。劉國恩大部分職業生涯在美國度過,此時他身穿耐克運動褲,Boss牌休閒襯衫,以一種大學教授即興演說的方式侃侃而談,顯得自信滿滿。每次我問問題,他就會停下來,然後說「O.K.」再接着談,聽着像是我打斷了他的流暢發言。
劉國恩在四川農村長大,與多數文革時期的年輕人一樣,高中畢業後就下鄉插隊參加勞動。他還記得當時他早上6點就起床,在根本不適合種植玉米的土地上種植玉米。「我們每天都得幹這種徒勞無功的活。」他說道。有一天,村裏的領導把他叫過去,說讓他做村裏的醫生。而他的資質就是他的高中文憑。
「我對醫學一無所知,」劉國恩對我說。「我就這樣開始治療病人。我甚至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治療之後情況反而惡化,有多少人死了,我完全不知道。」儘管如此,赤腳醫生仍然是一個倍受尊敬的群體,病人也不對醫療水平怨天尤人。「當時的人食不果腹,」劉說道。「醫療保健甚至都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中國大學恢復招生,劉國恩考入成都的一所大學。1986年,他考入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攻讀衛生經濟學,隨後留美任教。而在此時,中國的醫療體系卻分崩離析。鄧小平設立制度,推動經濟自由化,但這也瓦解了原有的合作醫療制度。政府減少行政干預,一方面提振了製造業和地產業等行業,另一方面也瓦解了醫療體制。國家財政不再負擔醫療費用,公立醫院便走上了自負盈虧,追求利潤的道路。醫生收入微薄,其中許多人開始收受紅包。在舊體制下,會有城裏受過教育的醫生組隊到鄉下來彌補赤腳醫生的不足。如今,農村病患為了接受最佳治療不得不擠到省會,大城市醫院不堪重負。「政府基本上對醫療問題一拖再拖,」劉國恩說道。
到本世紀初,從病患到醫生,從平民百姓到政府官員,大家都明白醫療體制的弊病。2002年華南地區爆發「非典」疫情,更是加重了人們的危機感。2003年,政府提出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2007年,這一制度覆蓋城鎮居民。2002年,劉國恩正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任教,當時他接到一個電話,對方邀請他到北京大學協助成立衛生經濟學與管理學系。他接受了這個邀請。「那是我的夢想,」他說道。
在北京,劉國恩開始上書國務院。國務院是中國最高行政機關,負責起草法案,制定國家大政方針。2009年,國務院推出了一項改革計劃,包括以下五個方面:一、到2020年,將醫療保障制度覆蓋到全體公民;二、降低基本藥品價格;三、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如普及衛生知識與接種疫苗,尤其是在最貧困的地區。四、在農村地區投資設立醫院,以緩解城市醫院的就診壓力;五、重組大型公立醫院,使大型公立醫院專注於急診救治和專家診斷。劉國恩認為,其中最後一條要求病患從大醫院分流出來,實施起來最為棘手。「醫院不會自斷財路,除非從外部入手實施改革。」劉國恩說道。
這一系列改革計劃收效好壞參半,政府官員自豪地表示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已覆蓋全國95%的人口,遠遠超過2003年的30%。然而醫藥價格卻同時上升了,因此實際上,許多病患的醫療支出相比起之前並沒有差別。此外,類似於李夢南的情況,醫保中政府報銷的比例取決於病人的戶籍所在地。大城市醫院的就診壓力不減反增,原因在於新近參保的人群沒等到農村醫院建成便蜂擁到城市醫院。在美國西東大學研究中國醫療制度的黃延中教授表示,襲醫事件激增反映了改革計劃的失效,沒有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病患仍然寄希望於在大城市醫院接受最好的醫療服務,「一旦不能如願,他們便不知所措。」
去年夏天,我在趕往雲南這一中國西南省份的途中全身起了疹子,只好就醫。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中國的醫院。一個50多歲面相和善的醫生立馬給我診治。我掀開襯衫,給他看我患處變色的情況,這時周圍其他幾個病人和一個清潔人員也湊上來圍觀。醫生問我的住址,我說北京。他說,難怪了,雲南氣候跟北京差異大,最容易起疹子了。我跟他說我之前來雲南的時候也沒有出現這問題。「那吃的呢?」他說。「這裏口味相當辣。」我說,我吃得慣辣。他說可能是水的問題。我告訴他我還沒有喝過當地的水。他聽了一臉迷糊。最後我問他該怎麼辦?他建議我離開雲南。
我第二次上醫院時,有機會穿了一次白大褂。北京友誼醫院的外科醫生孟化40歲出頭,為人和藹友善。他同意我對他進行一天的跟蹤採訪,而我接觸的其他醫生都拒絕了我的請求。孟化近期建了一個網站推廣他最新的減肥手術的相關技術,他似乎把這次採訪當做了他推廣網站的機會。我坐在他辦公室的一角,觀察他診治。
「好久不見!」孟醫生對一個走進來的老年婦女說道。她長期胃痛,拿檢測結果過來給醫生看。「看來沒什麼問題,」孟醫生說道,拿着她的CT片子。孟醫生推測她胃痛可能是跟便秘有關。「我運氣好的話三天大便一次,」她說。「看,這還不夠,」孟醫生說。「要每天都有大便才行,你平時吃什麼比較多?」「饅頭,米飯,粥,」她說道。孟醫生建議她多吃蔬菜。他想開個單讓她去泌尿科拍個超聲波圖,不過她推辭了。
作為一名外科專家,孟醫生有時間了解他的病人,傾聽他們的憂慮。不過,這樣的醫生為數不多。打卡下班後,他帶我走過大廳到一個普通的住院醫師的辦公室。這個醫生飛快地給一個神情緊張的婦女開藥方。我問他今天看了多少個病人,他一聲不吭整理起散落在辦公桌上的幾十張單子,在我面前疊起來。
我聽過很多中國醫生工作量大的例子。上海一位權威的放射科醫生跟我說,他聽說過的最高紀錄是一天接診314個病人。「那是在上海兒童醫院,」他說道。「一個醫生,從早上8點到下午6點總共10個小時,2分鐘一個病人。」一項在陝西進行的研究表明,醫生接診一位病人平均花費時間是7分鐘,而醫生只花1分半鐘的時間跟病人交談。因此,病人往往很心急,堵在門道上,輪到了不敲門就徑直進去。一位曾在北京和睦家醫院任職的芝加哥醫生喬·帕薩南特(Joe Passanante)跟我講述了這麼一個經歷。有一次他在給一個婦女做心肺復甦,這時一對夫婦走進房間,說他們的女兒發燒了。「我在救一個將死之人的命,而他們卻走進來叫我去給他們女兒治發燒。」他回憶道。
和孟化一起待了一天後,我並未看見任何塞紅包的現象。他解釋說,重要手術會有人塞錢,我所見到的門診中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但是他也說,醫院賄賂現象十分常見,甚至沒什麼人會擺手說不。醫生薪水雖少,但往往還有獎金、開藥回扣、以及賄金。孟說,「我一個月工資總共一萬元,我還要買車、買房子。我需要其他收入。如果病人在術後給我紅包,我大概不會拒絕。」
大眾對醫生懷着極大的敵意,這已經司空見慣。哈爾濱殺人案發生後,人們對兇手表露出的同情幾乎和對受害者的一樣多。中國政府喉舌《人民日報》發佈了在線問卷,讓讀者從微笑、悲傷、憤怒幾種表情中選出自己對此案的感受,結果有65%的讀者選擇了笑臉。這一問卷調查後被關閉,但央視就此事發佈了一段報導:一名評論員發問,「我們是不是也有可能成為兇手當中的一員呢??」
似乎每個中國人都有過在醫院或醫生面前遭罪的經歷。多數大醫院都有客服部,病人可以向其申訴,要求賠償。如果醫院未能受理,病人可以以瀆職為理由對醫院提起訴訟。然而,大部分中國人並不相信法律體系,勝訴的幾率也實在渺茫。同樣,醫院出於對自身名聲的考慮,也希望私下解決問題,而不要鬧上法庭——當地政府會因其醫患紛爭過多而實行處罰。
如果通過官方途徑一無所獲,病人往往會發起抗議活動。2013年,一名34歲的母親聲稱剖腹產後發生醫療事故,並召集十餘名親友闖入北京第六醫院,最後要到了一萬元賠償金。今年(譯者註:本文發表於2014年)五月,昆明一男子因妻子及嬰兒死於剖腹產手術而懷抱自家另一個小孩爬上醫院房頂。他威脅要從上面跳下去,一大群家屬們擠在下面,致使交通癱瘓。有時,病人撒手人寰,而家屬認定醫生有錯,就會在醫院門口停屍,不拿到賠償不罷休。
我在北京見到了在中國發表過「醫鬧」研究的哥倫比亞法學院李本教授(Benjamin Liebman)。他告訴我,醫院為平息抗議所賠的錢一向比走法律程序要多。病人家屬甚至可以僱到專業的醫鬧。深圳一則報告中顯示,提供醫鬧服務的人平均每人每天賺50元。上海一名放射科醫生告訴我,「如果你母親死在了醫院,就會冒出來一個機構和你說,『我們可以幫你。我們可以找二十個人來醫院勒索,拿到的錢分一半。』這夥人太專業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這個國家,一場小小的公眾集會都能牽動政府神經,而醫鬧事故卻此起彼伏,無人干預。有可能官方認為這種事合乎情理,抑或認為這是協商賠償的有效途徑。有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政府在策略上鼓勵這樣的抗議活動,因為政府將之視為相對無害的泄憤渠道,同時也是更嚴重的社會騷亂的早期預警信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學家彼得·勞仁特曾(Peter Lorentzen在其專制政權的研究中就指出了這種「聚眾鬧事常態化」的現象。李本告訴我,「抗議成了提供社會保障和識別哪些群體需要幫助的機制。」但問題在於「人人都知道政府備好了錢賠給給請願的人和抗議的人,這就刺激了更多抗議出現。」
李夢南案審判時,李的律師試圖以治療效果太差最終失敗為依據,使被告判決減輕。可是李夢南在法庭上給人印象很差,似乎未表現出任何悔意。法官交叉質詢時,他只是從喉嚨里擠出一個字來回答。「你感到愧疚嗎?」法官問。「哼。」「向王浩的父母親還有其他醫生道歉吧。」「行。」王浩家人拒絕接受這樣的道歉。「我不相信他,」王浩的父親後來告訴我。「他並不是發自內心道歉。」審判歷時一天;三個月後,法官宣判李夢南無期徒刑。
在中國,刑事審判一般附帶民事訴訟,此案也不例外。王浩的家人通過這起案件附帶的民事訴訟要求被告賠償損失。李夢南被判賠償受害者家庭68萬元。但王浩的父親和我說,他不指望能拿到一分錢。
在這起民事訴訟中。王浩家人僱用的律師名叫李惠娟,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女人,她還曾做過發言人、公關代理和臨床醫生。前不久,我在北京一家書店咖啡屋與她見面,她穿着一件很大的紫色大衣,拎着一隻藍色普拉達包。她聲音輕柔,經常引用一些偏僻的中國諺語;我聽到這些諺語一臉茫然,她見狀便草草寫下給我解釋。李惠娟五十多歲,她讀過醫學院,在中學當過老師,後來做了律師。直到如今,她依然循循善誘。那次審判後她站在了中國反對傷醫案運動的最前端,飛往全國各地給醫生和醫院院長開講座,講授該如何預防醫患衝突。她拿出蘋果筆記本電腦,向我演示了一組幻燈片,其中有血腥的暴力場景和抗議事件的照片,還有希波克拉底、愛因斯坦、馬克思、彼得·德魯克等人的名言。每一位受害者都單獨列在一張紀念他或她的幻燈片中:受害者頭像位於幻燈片上方,下面有鮮花蠟燭的圖標,再往下則是一行大字,詳細記錄了行兇者的最終判決。
李惠娟對於中國醫療行業的狀況感到失望。「改革都已失敗,」她說。在她看來,改變現狀的決定權在醫生和醫院手中。她在講座中建議醫生小心細緻地記錄患者信息,確保病人理解手中的診斷書。而現在的醫學院也開始強調醫患關係。北京大學醫學院開設了說醫學人文概論「,在這門課上未來的醫生們將學會對病人懷有同情心。
如果醫療改革失敗,中國將付出高昂的代價。隨着老齡化人口增多,中國家庭的醫療開支占收入比重將會上升,而肥胖率和吸煙人口比例的增長則意味着青年一代也面臨着高昂的醫療賬單。這並非個體問題——整個國家的經濟都會受此拖累。在過去二十年裏,中國向世界其他國家出口商品,換來一片繁榮。然而,隨着全球經濟需求萎縮,中國必須越來越多的依賴國內消費以保證經濟增長。目前有着全世界最高居民儲蓄率(約佔收入的50%)的中國人開始購買更多商品了。但是除非醫保計劃給每一個家庭提供更好的醫療保障,人們還是會繼續把錢存起來,以防醫療花費傾家蕩產。
李惠娟說,她學醫的時候,人們還很尊敬醫療行業的人。現在,她說,」朋友家的孩子都不再從事醫療行業了。「比起醫療業的狀況,醫生的短缺和醫療費用的上漲讓她更為痛心,她說:」這將會削弱國力。「
4月1日是王浩去世的第二個農曆紀念日。他的家人來到了老家內蒙古赤峰郊外的墳墓前。王浩的父親王東清來到機場接我和李惠娟。」這些建築都是過去十年蓋的,「我們開車穿過赤峰市時,李惠娟解釋道。」赤峰原本是個貧窮偏遠、荒無人煙的城市——現在這裏發展起來了。「王贊同地點了點頭。他生長在鄉下,服了一段時間的兵役後到了市裏的銀行工作。他開着一輛豪華型的榮威小轎車。我問他住在哪裏。」他住在老城區,「李突然插了一句。她穿着黑色雙排扣外套,黑皮褲,戴着一副巨大的黑色太陽鏡,看起來像躲避狗仔隊的大明星。我注意到儀錶盤上方有一個迷你轉經筒,於是便問王是不是信佛。他回答不是。
我們在墓地邊上下車後,前面傳來了悲痛的哭聲。王浩母親趙春雲坐在墓地邊上啜泣着,他的叔伯姑姨及表親手無足措地圍在她身旁。」我的兒子走了,就那麼走了,「她哭訴道。一塊高高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愛子「的字樣,邊上擺滿了鮮花,供着水果、線香、啤酒和一罐紅牛。他的朋友們在一旁燃起了一堆火。李惠娟徑直走到趙春雲身旁,兩人相擁在一起。」我們來看你了,「李惠娟說,」有很多人在關注呢。他沒有白白死去。「最後,墓地的一名工作人員走了過來,告訴趙要稍微安靜一點。」對不起,這邊馬上就結束了,「有人答應着。
一行人在附近一家飯店的包間裏吃了午餐,李惠娟繼續安慰着趙春雲。男人們坐在圓桌的一邊,女人們坐在另一邊。我坐在王東清旁邊,看到他的黑色西裝上打了幾處補丁,也沾了些灰。喝了幾口辣辣的當地白酒後,我問起了他的兒子。」他特別踏實,「他說,而且」十分聰明「。父子兩人最後一次見面是在過年假期,當時年輕的兒子從早到晚都在學習。」他熱愛醫學,「王浩的弟媳說。」他的熱情高到不得了。他和他媽媽說過以後要拿到諾貝爾獎。「王浩去世前五天才剛剛拿到香港的博士錄取資格。而且,只要有親朋好友生病,王浩都會出面,大家連醫院都沒去過。王浩父親等人都想努力回到王浩和李夢南互不相識的時候。因為存在不可測因素,王浩之死基本上是偶然的,」就像晴天裏一道霹靂,「王東清如是說。那一天,兩個人里隨便哪位都有可能做出千萬個不同的選擇。
我問王東清,兒子的死他怪罪誰。」錯在醫療體系,「他說。」李夢南只是這一衝突下的一例典型。這樣的事故發生了太多。我們怎麼能只責備李夢南呢?」
阿波羅網編者按:美國「布朗大學」醫學院病理及實驗醫學系助理教授何邁表示,江澤民搞了醫療產業化。那醫院其它國家都補助來扶持這個醫院,來幫助老百姓。那中共它不給醫院錢,讓醫院從老百姓那邊巧奪名目的去從老百姓身上掙錢。老百姓這個醫療費用又是非常高。所以,國內現在醫患,醫生和患者的關係非常緊張,一方面就是醫生抱怨患者不尊重醫生;另外一方面,患者覺得你這個醫院,就是收這麼多錢,整天就是在收錢上下功夫。所以,導致關係非常緊張。我總覺得是這種制度和政府的問題,醫生和患者都是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