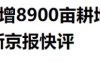採訪人:依娃 作家
姚監復: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著名公共知識分子、
時間:2012年3月12日、14日
採訪形式:面談、電話採訪

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姚監復(資料圖片)
依:姚監復先生,很感謝你接受我的採訪。請先說一下你的個人簡歷,好嗎?
姚:請上網查。
姚監復,1957年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曾任中國農機研究院工程師,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農業生產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協作研究員。
——摘自姚監復博客簡歷
依:你有哪些關於大饑荒的研究作品、論文等?
姚:《原河南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談:1958年的河南省「潘、楊、王事件」 》,是我在2007年的普林斯頓大學反右五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論文。《從烏托邦噩夢回歸現實土地》是我在紐約大躍進五十年改革開放三十年研討會上的論文,《1958年黨內高層反右傾鬥爭打開了大饑荒大浩劫的地域大門》是我今年二月在華盛頓召開的大饑荒五十周年紀念國際研討會的論文。我還著作有一些關於中國農村政策,對上層領導人評論的文章。
依:大躍進的親歷人噎不多了,請先說說你個人所經歷的大躍進,好嗎?
姚:一九五八年,一場「大躍進」運動在中國大陸轟轟烈烈的開始了。毛主席提出「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的目標。鄉下人砸鐵鍋,城裏人拆鋼窗、卸暖氣管,用「土高爐」煉出了三百多萬噸廢鐵。農民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人收穫,或者收割草 率而大量拋撒。
我是哈爾濱工大機械工藝系學鑄造專業的。我也就是多嘴,在那個大躍進、大煉鋼鐵時候,我是學鑄工的。我就多說了一句,我說:「大煉鋼鐵,煉土鋼,我去賣的,賣了十五塊錢。」然後交心的時候,我就說了:「我們研究院一千人,平均工資是多少錢?兩個禮拜這麼『炒鋼』,工資是多少錢?還有六個蘇聯教授也跟着這麼『炒鋼』,這個是多少工資?」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笑完了。後來批我了,沒有料到,廬山會議批彭德懷裏面有一條,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後來批我了,就說彭德懷還只定性的說一個,「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你姚監復膽子多大,還定量的計算出來,「大煉鋼鐵得不償失。」
怎麼辦呢?那現在給你一個重要任務,到劉胡蘭公社去勞動鍛練,你當副隊長。然後就到山西劉胡蘭公社,而且把戶口帶過去了。所以,現在我的戶口本上是山西文水、劉胡蘭公社從農村遷回北京的。
依:你去的時候剛好是農村大饑荒時期,請說說你所見、所聞、所知道的情況。
姚:那剛好是1960年,大饑荒年代,每個人定量只有五兩原糧,早晨一大碗稀湯,晚上也是一大碗稀湯,晚飯給每個人一個核桃大的小窩頭,是高粱殼做的,人吃了大便不出來,很痛苦。人開始浮腫,浮腫還得下地幹活,每天早晨五點鐘,隊長就喊:「出工了,社員們出工了。」我們新社員就出工了,老社員也來了,他們說:「你們北京來的,肚子裏還有油水,你們先幹活,我們要各就各就」我們也不懂什麼叫各就,後來知道是蹲在那兒。後來我們沒油水了,向貧下中農學習,也跟着各就。一天出工三次,早晨一次,吃過飯一次,吃完晚飯再出工一次,勞動十二個小時以上。
五兩糧食吃不飽,但是很平均。吃飯的時候,都是吃食堂,大人小孩都是拿個大碗,認識的人從下面一舀,就稠一點。不認識的人,上面一舀,就都是水。所以經常,開飯半個小時後沒有來打湯,不是不餓,是誰都不願意先打清湯,還有是不相信炊事員。最後讓我們北京來的新社員當舀湯的,我很榮幸的負責的擔任了這個角色。打飯的時候,不論是誰,認不認識,我都攪幾下,每個人稠稀一樣,我覺得我很公平,社員也很信任我,我覺得噎是「共產主義」了。
依:按理說你當時去劉胡蘭公社勞動,也還是國家幹部,有定量的商品糧供應,你的定量到哪裏去了?
姚:我們當時的定量是每個人每月36斤口糧,按理說是不挨餓的。當時由貫家堡大隊的支部書記給我們每個月從糧庫代取,拿回來的是全國糧票,但不經過我們的手,他交到食堂時只有每人15斤原糧。我是勞動鍛煉隊的副隊長,給我的主要任務是管生活,我就納悶了,我們其他二十一斤糧票到哪裏去了?二十多個人,四百多斤糧票到哪裏去了?
時間一長,就能發現貓膩。白天幹部社員都是喝稀湯,到深更半夜看就不一樣了,幹部家的灶房在舉炊冒煙,在偷偷做飯吃。大饑荒時期,餓不死的是村幹部、會計、食堂管理員。因為他們是用了我們的糧票去買糧食吃,讓老婆孩子吃。後來我就說:「不用麻煩你領了,我噎知道在大象糧管所領糧票,只有幾里路,我自己騎自行車去領。」這就把村幹部給得罪了,嘴上又不好說。等我們要回北京做鑑定的時候,給其他人都是甲等,給我評的是乙等,這條理由幾乎讓我回不了北京,原因是我不尊重基層黨的領導。最後我們剩餘的幾千斤糧票都被扣下了,留給村裏的社員。我和一機部來接我們返京的幹部辯論,「我們自己的口糧,節約應該歸己」。但是幹部說:「你們來了,就是社員,糧食就應該交給隊裏。」
但是那些糧食社員能不能吃上,能吃上多少都是未知數。在文水縣我親身體會到人民公社化帶來的飢餓和浮腫病,親眼看到老社員因疲累而衰弱多病,最後苦痛、掙扎、默默地告別人世的進程,也更深刻地感受到農民的純樸、善良、真誠、韌性……的高尚而可憐的本性。
依:當時全國多、快、好、省的大修水利,有許多都是「轟轟烈烈上馬,鮮血淋淋下馬。」請談談你所親自參預勞動的山西文水縣文峪河水庫的情況。
姚:大躍進除了大煉鋼鐵就是大修水利。文峪河水庫從1959年11月15日開工,1961年6月12日攔洪,1970年6月竣工。水庫大壩為土壩,垻長740米,垻高55.5米,垻底寬約500米,垻頂寬約6米。總工程量為972萬立方米,投工828萬個,投資0.6億元。水庫大壩右面建有出水隧道一個,直徑為5米,最大匯洪量297米/秒。水庫大壩左面建有溢洪道,長580米,寬24米,最大匯洪量971 米/秒。垻下建有水電站一座。這個工程還在山西獲過獎。(來自百度資料)
以上的資料是百度中可以查找到的資料,但是有些資料恐怕是永遠都查不到的,那麼我來告訴你,你將來可以寫下來。當時的施工都是人海戰術,用的都是肩挑背抗,水壩下面是山西省派來的直屬幹部,他們用皮帶傳送機運土,我們是生產隊派來的,是在上面拉車。正因為他們在水庫下面,水庫發生垮垻時,剎那間山崩地裂,跑根本跑不急,他們就通通被活埋了,來不及反應,來不及痛苦,我估計當時死亡超過一百人以上。整個水庫,幾個山頭突然平靜了,死一樣的寂靜,因為大家親眼看見人活活的被埋了。哪裏來的?多大歲數?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給多少父母妻兒帶來的痛苦是我們活着的人不能想像的。我就想,那時候,成千上萬的水庫工傷死亡的人數是相當多的。
為什麼會出現塌垻?當時施工是鋪一層土,築一個長方格子,澆一層水,再填土,由夯土拖拉機一壓,水庫的土層究竟應該含多少水,這需要非常的科學,因為中間水分一多,土層之間就會滑移,導致塌方。所以大躍進時期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邊修改的大型水庫死人很多。在大饑荒死亡人數中佔一定比例。

板橋水庫大壩(資料圖片)
一些質量不合格的危險大型水庫建成後會留下無窮後患。有名的板橋水庫大壩,位於河南駐馬店地區,就是大躍進的產物,工程質量粗劣,又無正常維護。 1975年8月,在一場由颱風引發的特大暴雨中,河南省駐馬店等地區共計60多個水庫相繼發生連環垮壩潰決,引發了一次世界上最慘烈的水庫連環垮垻事件。至災害發生時,17個泄洪閘只有五座能開啟。
幾天之內,1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60億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橫流。1015萬人受災,超過20萬人死難,倒塌房屋524萬間,沖走耕畜30萬頭。縱貫中國南北的京廣線被沖毀102公里,直接經濟損失近百億元,成為世界最大最慘烈的水庫垮垻慘劇,這件慘案一直被政府以「國家機密」為理由而禁止對外公佈,直到2005年,由於中央文件的解密,才被大家慢慢了解。
大躍進時期所修建的水庫到現在對中國都有影響,有三分之一的水庫都是危險水庫,有致命的危險。所以我說,大躍進水利化的偉大成就後面是血、淚、白骨,而且是累累白骨,今後還會有危害。
依:你在幾個場合都提到過關於「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翻譯來處,請再詳細說一下。
姚:後來我見到于光遠(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他說,我還把「共產主義」的定義改了,原來的共產主義翻譯的內容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毛主席說,于光遠,你得改一下這個翻譯的名稱,因為王明提出來:「各取所需」沒有「計劃經濟」味道,應該重新翻譯。因此,于光遠重翻德文就改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等到後來大躍進,于光遠也吃稀飯,也開始不行的時候,他說,翻譯錯了。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生產力高度發展、產品極大豐富了,才能「各取所需」啊。現在,就只能平均地稀湯,,翻譯錯了。他去找中央編譯局說:我翻譯錯了。因為按各取所需是要生產力極大豐富了,才能按需分配,還應該譯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中央編譯局說,這是黨中央批准的,你沒權利改。所以,于光遠說,我跟你們說了你們不改,但我向大家講出來,良心上平靜了,這個翻譯錯了。
所以說從上到下都有一系列的問題。好多我們念的「經」那個「經」,德文你又不懂,中文又翻錯了,翻錯了,還不改。那這下面的大和尚、小和尚不都糟糕了嗎。好多問題都需要好好研究。理想和現實,在物質那麼貧乏的條件下,統一向共產主義大躍進是非常可怕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東西離開了物質基礎必然帶來巨大的災難。
依:你當時知道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饑荒嗎?在那種輿論控制、思想封閉的情況下,你有沒有想過是因為毛澤東的個人意志、集權統治政策所造成的國難?
姚:不知道,當時一點都不知道。
沒有懷疑過,當時非常相信共產黨的宣傳,相信《人民日報》,相信是蘇聯逼債,相信全國有罕見的天災,完全相信報紙輿論的「正確」說法。就是現在,也還是有人相信是天災,就是知識分子群體裏對餓死人,對餓死四千五百萬人的數字仍有人是持懷疑態度。這和他們幾十年來所受到的教育和宣傳有關,沒有可能知道、了解真相。
依:從「三年自然災害」到「三年困難時期」的說法,這中間的變化說明當政者的什麼態度變化?
姚:你說從「三年自然災害」「到「三年困難時期」等多種託辭,說明當政者的態度有什麼變化,我說當政者沒有變化。從去年出版的黨史就可以看出沒有改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提到那個時期,仍然沒有死亡總數,只講1961年非正常死亡 1000萬人。國外有很大爭議,國內聽不到爭議,所以說當政者沒有變化,在《黨史第二卷》中,有關「大躍進」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數據表述是這樣的:「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 100萬,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563 頁)從這裏能看出變化嗎?
依:國際上有學者,比如香港大學歷史學教授馮客,認為執政者剝奪人的吃飯權——即殺人,用糧食作為殺人的武器。中國學者也有一種說法叫「餓殺」。我個人認為大饑荒即大屠殺,是不是偏激之言?你怎麼看?
姚:你說有學者說大饑荒是不是大屠殺,我說這是事實,也是罪行,是滅絕人類罪。危害人類罪(英語:Crimes Against Humanity),舊譯為「違反人道罪」,又譯為「反人類罪」,於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將該罪名中文譯名確定為「危害人類罪」。規約中的定義為「是指那些針對人性尊嚴及其嚴重的侵犯與凌辱的眾多行為構成的事實。這些一般不是孤立或偶發的事件,或是出於政府的政策,或是實施了一系列被政府允許的暴行。如針對民眾實施的謀殺,種族滅絕,酷刑,強姦,政治性的、種族性的或宗教性的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的行為」。「反人類罪」是指握有權力資源的人出於政治、軍事或經濟目的,以國家、種族、宗教或某種意識形態為界,對他們進行肉體上消滅或政治上虐待的暴行。
《國際刑事法院規約》1.謀殺行為(第7條第1款第1項)所謂「謀殺」,是指以故意殺害或致死他人的方式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平民人口實施的攻擊行為。2.滅絕行為(第7條第1款第2項)所謂「滅絕」,是指包括故意施加某種生活狀況,如斷絕糧食和藥品來源,目的是毀滅部分的人口。3.奴役行為(第7 條第1款第3項)所謂「奴役」,是指對一人行使附屬於所有權的任何或一切權力。(關於反人類罪的定義摘自百度)
(毛澤東製造的4500萬人口死亡的大饑荒完全附和謀殺行為、滅絕行為、奴役行為這三條罪狀——依加)
依:有些護毛學者強調毛澤東製造的大饑荒不是故意的,他的初衷不是這樣的,雖然結果是這樣,屬於是好心辦壞事。你怎麼看?
姚:他可以這麼說,斯大林、希特拉都可以說他是為了種族,為了國家,殺人的時候都是有他理直氣壯的動機。但是是看動機還是看效果?作為毛澤東的動機是為了趕超蘇聯共產主義,還是為了當國際社會的老大?這個動機到底是好還是壞?都是需要研究和批判的。
依:關於大饑荒的研究專著不能在國內出版,「事實向來不求是」,當政者害怕什麼?
姚:怕什麼?怕否定,怕否定黨是三個代表,有一種恐懼感,如果把這個事實肯定,那麼你就不是代表着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不是代表着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着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否定了共產黨統治的正義性合法性,威脅到他的統治,
依:你個人 認為大饑荒在中國大陸有多少人知道事實真相?
姚:我覺得全國有百分之五的人知道,或許更少,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事實真相,因為噎過了三代,沒有墓碑,沒有死者的墓碑。越戰,韓戰死了多少人,在美國的幾個地方都有紀念碑都有名字。《炎黃春秋》講了一些真相,它只有十二萬讀者,一個十四億人的國家十二萬算什麼數字,有什麼了不起。
許多人也不喜歡聽不想知道真相,那次我們在紐約開會,有一個老華僑就質問楊繼繩:「我們在外國一直受氣,被人看不起,現在國家富強了,你們又跑出來說中國餓死人,人吃人,你們為什麼說這些?」我就給他解釋:「我們是為了讓子孫記住歷史教訓,讓同樣的災難不要再發生。」其實,他是代表了不少人的想法,覺得「家醜不可外揚」,覺得我們是在告洋狀。年輕人一聽這些也認為我們是在憶苦思甜,是祥林嫂,總在嘮嘮叨叨的訴苦。對更多的人來說,大饑荒就像從來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依:大饑荒的研究不應斷層。你希望我們這樣沒有經歷過大饑荒的後代做些什麼?怎麼做?
姚:你們年輕一代要做的就是儘量保存真相。
比如人吃人了,我吃了我的小孩我願意講出來嗎?很殘酷的事情就很不願意講,你如果把這個弄清楚就很了不起,包括他們誰吃誰了?你當時為什麼吃,是怎麼想的。還有易子而食,你吃我的小孩,我吃你的小孩,我覺得這種殘酷比戰爭中殺人還殘忍,餓死的過程是可怕的。
我們在罵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不承認不懺悔的時候,我們自己對大躍進、對反右、對文化大革命懺悔了嗎?連事實都不承認。我估計得一百年以後,那時的歷史會有人重新書寫。你們現在的寫作就等於寫幾塊墓碑,能寫幾個就是幾個,幾千萬人,你能寫出十個、一百個就了不起,更多的人來寫就把這個歷史事實寫出來了,就完整了,最起碼讓當權者不敢也不能否認這個罪行。滅絕人類罪,反人類罪,這在國際上,人權公約,國際法庭就認定有這個罪。我們現在講的大浩劫大災難,要從法律角度去找,是什麼罪什麼罪行,讓歷史法庭缺席審判。像蘇聯人將1932年餓死一千萬烏克蘭人的罪魁禍首斯大林送上法庭一樣。
依:紅歌、紅色旅遊在國內還是很盛行,靠此升官發財。許多人還是盲目崇拜毛,把他當成聖人,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姚:大唱紅歌和崇拜毛,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拉開了序幕了,他們應該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還應該唱「不許放屁,不許放屁。」
我永遠不會忘記文化大革命把我打成現行反革命,每天用硬橡膠包着鋼絲的鞭子打我,打瞎了我的右眼,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費,受開除黨籍、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下放我到湖南西洞庭湖農場被隔離審查、勞動改造。四十多年了,沒有任何人出來向我道歉,他們的口號是崇高的,行動是殘酷的,後果是悲慘的,但所有人良心都是平靜的。他們認為,自己是按照最高指示,是按照毛主席的語錄進行的。單位上讓我寫一個認罪書,承認自己錯了,批評了江青,因為江青是政治局委員,我說江青有病,毛主席應該和江青離婚,是惡毒地攻擊敬愛的江青同志,這個材料一直留在我的檔案里,很晚才把它拿出去。
我的母親賀書華為退職小學教員,文革中慘死於北京八月紅色風暴紅衛兵手下。所以我的妹妹姚蜀平醞釀了二十多年,寫出了四十萬字的小說《悲情大地》,由明鏡出版社出版。因為那是刻骨銘心的不能忘懷的悲慘經歷,是一個家庭的浩劫,更是一個國家的浩劫。
文革中我的右眼被打瞎,看不見光明,此後看人世間一切事物和人物,只能一目了然。
依:網絡上稱您是公共知識分子,您個人怎麼定義這個稱呼?
姚:美國之音有一篇文章稱我是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我覺得是對我的鼓勵和鞭策,希望我成為這樣的知識分子。我個人覺得我不是公共知識分子,我沒有資格。加拿大的盛雪女士當面對我說:「你不是公共知識分子。」我說:「你這樣說我,我回去就安全了。」還有一篇文章說「姚監復是最狡猾的共產黨的辯護士。」 因為我講新民主主義。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應該非常勇敢,應該總是批判性的,不為任何名利所動,不為任何權威所屈。我沒有達到這個高度,我就是老老實實的講一點真話,無愧於心的話,轉述一些別人的真話,不說自欺欺人的騙人的話。如果這樣都有困難,我就沉默。
(依插言:楊繼繩先生說:「在中國一個人講真話就是英雄,這已是名言。)
我來美國的時候也感到恐懼,感覺到威脅,感覺到壓力。我感覺到無名的恐懼和有原因的恐懼,有人警告我回國時有可能不讓我進關,像余杰一樣把你趕回來,也有人說,你一進關,有關部門就把你叫到特別的地方審訊一番。我回去以後,有沒有人騷擾我的電話,干擾我的出行,查訪我的朋友查我的行蹤,都是可能的。他們警告過我,不能在網上寫笑話,不能幫助別人在香港出書,不能替胡績偉的書作評論,之前有以後也會有。在這個國家,每個人都有恐懼的自由,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很高興你能做這些事情,流亡者孤獨,但可以寫作。其實在國內我也感覺是生活在思想上的荒漠之中,我們也有一種思想上的流亡感。周圍的人,面孔是熟悉的而心靈是陌生的,不願意聽你講話的,是另一種流亡生活。有你這樣熱情的朋友來關心這個事情,明天我要走了,你還打電話來談,這至少讓我感覺到我不是孤獨的。一個人在荒原上大喊大叫,周圍沒有回音,沒有回應,這個孤獨是感覺非常可怕的,甚至會影響自己願意不願意繼續走下去,走下去有什麼意義。人家鞭策我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對我是一個希望,一個鼓勵,讓我覺得我不孤獨。
我們在寫在說的時候,我們會感到我們身後站着逝者,四千五百萬冤魂,還有那些受過迫害的人,我們是倖存者,代言人,所以應該勇敢地講。要儘量準確,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依:姚先生,謝謝你回答我的提問。祝你一路順風,多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