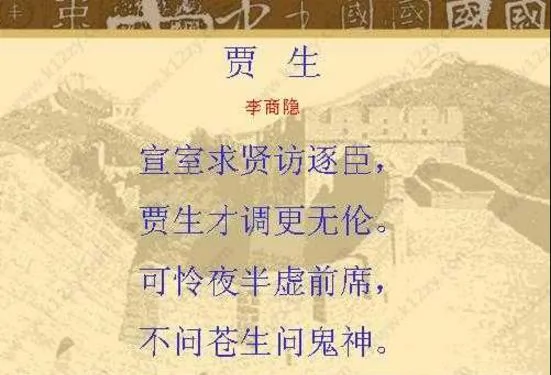中國的民間節日,只要是跟吃相聯繫的,都保存了下來。假若某個節日沒有吃的內容,在中國的民間就不把他當做節日來看待。新年,是吃的綜合,新年就被全中國人保留下來。中秋節吃月餅,中秋節就是很重要的一個節日。端陽節吃粽子,民間對於端陽節就樂此不疲。還有六月六,吃干餅,有的地方就把六月六當做一個節日。臘月二十三吃灶馱摞,人們就把這天稱為小年。久而久之,吃的節日就成為一種文化,在民間的血液里流淌,誰想剔除也剔除不掉。文化大革命是以改文化的命為前提的,但是在民間某些東西卻不是說改就改掉的。比如端陽節,文化大革命期間,民間一年也沒有落下過。
1.粽子
為了讓每個人端陽節都吃上粽子,生產隊每年都要種上十幾畝粳米。粳米的產量不高,一個人每年能夠分到15斤左右。正月十六包湯圓的時候,每家要在碾子上碾粳米或是在石臼里舂粳米,磨成米麵後,包出湯圓。剩下的粳米要放到五月端陽,才在碾子上碾了,包一年一度的端午粽子。至於屈原什麼的,平時鄉村里很少有人談到,只有到了端陽吃粽子的時候,人們才會說起屈原。最有意思的是,一個私塾先生說:屈原屈原,就是遇到委屈的時候,要圓通,不要方正。屈原方正了,就跳進汨羅江了。屈原的詩歌是文人詩,鄉村的人們沒有人懂得。但是鄉村裏的人們,只要識得幾個字,就知道李白和杜甫是詩人。
我們這兒包粽子不用竹筍的葉子,而是用胡葉。胡葉就是外國小說里的山毛櫸的葉子,長的很大,四月底就能夠包粽子了。端陽節即將到來的那個星期天,鄉村的孩子們雲集附近長滿山毛櫸的青龍山掰胡葉。胡葉上長滿了帶細小刺芒的東西,要先把胡葉煮熟,再拿起兩個葉子對着搓搓,直到搓掉上面的刺芒,才能包粽子。胡葉粽子煮熟後,滿院落都飄散着胡葉本身的香味,讓人饞涎欲滴。胡葉粽子耐放,那個時代沒有冰箱,放上七八天也不會變質。就是現在,端陽節前四五天,我們這兒的街道上賣胡葉的,依然是民俗一樣的風景。
那個時代,糖食很缺乏的,憑票供應。每一個農民在端陽節就是二兩左右,僅僅夠吃粽子時在碗裏放一點糖。粽子需要紅糖,但是那是供應的是古巴糖。黃黃的,吃起來有一些甜,後味裏帶着微酸。那時古巴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從他們國家進口糖,既是國內物質缺乏的需要,也是中國的政治需要。
端陽節早上,吃粽子的時候,有一邊吃一邊開會的習慣。隊長一邊吃着粽子,一邊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一個人還有二兩古巴糖,還有粽子吃。萬惡的舊社會,你們想吃粽子,吃個***毛不吃。最多吃個廣西糖廣東糖,哪有古巴這麼遠的國家的糖。就是糖從古巴運回來,國家也要花很多錢,沒有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做到?」
無論隊長說什麼,沒有人很在意聽,也沒有人敢站出來給他計較。每個人只顧吃自己的粽子。只有他的老娘說:「啥***古巴糖,吃着不甜,還有些酸,沒有過去的廣西糖甜。」隊長看看自己的母親,哈哈笑笑說:「國家哪壺不開,你提哪壺,你要是不是我媽,非鬥爭你不可。」隊長的母親說:「我不是你媽,我敢這樣說?」
我們這兒的隊長還是不錯的,每一年包括種粳米這樣的事情他都不會忘記,在那樣的年月人們還是很感謝他的。有幾年,端陽節吃粽子的時候,要開憶苦思甜大會,一邊訴苦一邊吃粽子。還有的時候,讓幾個地主分子站到村子的碾盤上,一邊吃粽子一邊鬥爭他們。地主一邊被鬥爭着,一邊吃着自己家的粽子。這天都是文鬥,紀念愛國詩人屈原,咋能武鬥呢?
現在,山毛櫸樹還有,但是村子裏的河水很小,引不到地里了,也就把秧地改為旱地了。種粳米噎成為村子的歷史,到了端陽節,村子裏的人想吃粽子,也要買東北的粳米。上歲數的人說,我們這兒的粳米才是貢米呢?比現在賣的粳米好吃多了。
2.插艾
端陽節家家門口都要擺放幾把艾蒿。端陽節的艾蒿有一種清新和略微苦苦的味道,家家都擺放的時候,一個村子都流淌着大地的芬芳。
擺放艾蒿的習俗,文化革命也沒有中斷。反正艾蒿又不值錢,也不要計劃,也不要票證。到田埂上割幾把,就行了。
村子裏老年人說,擺放艾蒿一是夏天來了蚊蟲多了,有驅蚊的功能。二是驅邪的功能,妖魔鬼怪來了聞到艾蒿的氣味就離開了。三是證明自己是漢族人,是從山西大槐樹下來的。四是艾蒿幹了,收拾起來,秋天腿疼的時候,用艾蒿熱水燙燙洗洗,腿就不疼了。
駐隊幹部也要求破除迷信,端陽節不要插艾,但是這個迷信很難破除,人們依然如故。
3.五色線
端陽節早上,村子裏的母親們都要給自己的孩子們的手腕上綁五色線。
五色線和陰陽五行,金木水和土、東南西北中,一色對一個方向,一色對一個五行。綁了五色線,孩子們的命里就什麼也不缺了。綁了五色線,孩子們就一年安穩了。另外我們這兒有一種蛇,叫桑樹根,紅紅的,像根五色線。孩子綁了五色線,蛇就不會咬孩子們。還有某一種說法,是綁了五色線,等於土地爺給孩子們做了記號,大地上所有的害蟲都不會咬土地爺的孩子。
綁了五色線,大人領着孩子們到河流里洗洗臉。端陽節大清早到河流里洗臉,一年不害眼病。
綁五色線的同時,還要給孩子的脖子上抹雄黃,同樣有驅邪的功能。
4.雞蛋
端陽節是要吃雞蛋的。
那個時候,雞蛋奇缺。每一家就是餵幾隻雞,雞蛋也是全家人的銀行。吃油吃鹽全靠雞蛋來換,雞蛋就顯得金貴了。
我們當時全家八口人,過端陽節的時候,母親為保證每個人一個雞蛋很是勞神。一般年景,母親都會保證端陽節每人一個雞蛋。但是也有幾年,母親無能為力,顯得很是無奈。
1970年端陽節,只有四個雞蛋,母親切得很均勻,每人半個雞蛋。放學後從母親手裏接到半個雞蛋,放在鼻子上聞聞,輕輕用兩個指尖扣一點放在嘴裏嘗嘗在嘗嘗,最後終於把半個雞蛋放在嘴裏,幾乎是一嘴咽了下去。隊長的母親說:「啥時候,一個人過五月端午,能夠吃上五個雞蛋,就是社會主義了。」全村人都把這句話記得一清二楚。
去年春天,和一個市里宣傳部長一起吃飯,有一盤春菜柴雞蛋。看見了這盤菜,部長說了一個比我的童年更為心酸的關於雞蛋的往事。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年端陽節,他們一家11口人,只有兩個雞蛋。他母親把雞蛋打碎,兌了很多玉米面,攤了一張雞蛋餅。吃飯的時候,切為碎片,在每一個人的碗裏撒一些。他的祖父祖母的碗裏多一些,孩子們的碗裏也多一些,而父母的碗裏,很少很少。現在他看見了滿滿一盤子雞蛋,很想哭。
往事如同煙塵,總會在某個時刻飄到眼前。懷舊與記憶里,總會有一些心酸,讓良知動容。寫下記憶碎片,或許就是民間歷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