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濃墨重彩繪儀式:從遊民搶親到帝王賞月
從《紅高粱》到《滿城盡帶黃金甲》張藝謀有一個延續的追求:他總能為自己的主人公設計種種出誇張、強化的儀式,這些儀式都十分新穎強烈,富有表現力。即使是回頭看看他擔任攝影師的《黃土地》,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人為打造的儀式化場景:那幾百人在一起打腰鼓的爆發力段落和那農民戴着柳樹枝條帽子跪在地上求雨的場景都是對陝北農民真實生活情形的強力改變。同時我們還可以發現,從《紅高粱》經過《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到了《英雄》和《滿城盡帶黃金甲》,張藝謀影片還有一個明顯而有趣的變化:影片中主人公的身份地位呈現一個明顯的上升曲線。《紅高粱》是為一個鄉土遊民設計性感的搶親儀式和超人式的奇怪造酒儀式,而《大紅燈籠高高掛》就開始給一個山西城鎮裏的財東設計儀式。那個陳老爺訓練成群的妻妾互相爭寵,以此滿足自己那充滿得意的欲望並躲避心中的恐懼。影片成功地渲染了那每晚四院呼喊,巡幸點燈的儀式,牆上的巨大京劇臉譜也和四處高掛的燈籠一樣在無聲地宣示着那大院裏的規矩。現如今,張藝謀正在枕戈待旦隨時準備着披掛上馬掛帥奧運開幕式總導演,在電影裏,他還是在表現反叛與規矩。繼承了《英雄》的創造,他給帝王設計粉碎政變的暴力團體操,他為帝王營造出勝利後立刻在鮮花叢中重述規矩的豪華賞月儀式。《英雄》、《黃金甲》這類影片被人欣賞的場面和遭到詬病的色彩鋪陳都是物有所值、歸於一統的,這些絢麗色彩和巨大場面都達成一個重要的效果:把帝王的日常享受和非常時期的應變措施都拍成一場又一場的華美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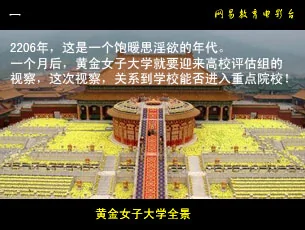
二、欲望場景:豐乳肥臀列隊和鋪陳裝飾的政變
《滿城盡帶黃金甲》把一個家庭亂倫故事與一個宮廷政變故事焊接在一起,在這個故事線上串着的是一系列用誇張的程式、亮麗的色彩和放大的佈景呈現出來的帝王儀式。所有尋常百姓家的瑣事和帝王的宮廷傾扎、篡權爭鬥都被在敘事上加以演繹了,被視覺手段加以鋪陳了。筆者認為影片中瀰漫着一種替帝王設想欲望場景的聰穎智慧,從中還可以看到編劇、導演為帝王設計完美儀式的那份辛勤和才華。我們看到:成建制排列的酥胸美女恭迎帝王歸來;誇張鋪陳的製藥、逼迫人吃藥的場面讓人心寒膽戰;恭順的藥師隨時伺候帝王,他會細心安排座椅下的藥液香氣熏蒸帝王,還能察言觀色、適時適度地替帝王錘背舒心;我們還看到,七、八米見方的大桌子和幾十米高的賞月觀花台;最後,我們還看到慈眉善目、文武雙全的周潤發以神機妙算的智謀和團體操一樣的整齊有力無情地鎮壓了反叛。所有這些都沒有那種故事的偶然走向帶來的趣味和結構上精心編織中顯現的不確定性,卻只見到豪華的展示和金錢、力量的炫耀。這些金黃與粉紅參雜的連環畫中,絲毫找不到人性的光芒和個體的尊嚴,卻只是透射出些許陰森之氣。在我看來,本片在視覺處理上還不如《心不在焉的理髮師》、《晚安,好運》那一類黑白電影顯得富有美感。在這些黑白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嚴謹、控制和動人的美和華貴。但是,面對《滿城盡帶黃金甲》中這些具有強大視覺衝擊力的畫面,我感受到一種儀式的威嚴和高高在上的莊重壓力。但是,有些意思的是,用華麗誇張鋪陳手法呈現的這個平息政變的緊張一刻並不是影片華彩樂段到來之時。
三、 血腥儀式與六四情結
影片在大王調動盾牌槍刺如林輕鬆剷除政敵之後,又設計出一個令人拍案驚奇的儀式展現新高潮。緊接着出現的場景轉換既富有視覺衝擊力又具有讓觀眾震驚劇作效果。王子元傑發動兵變,大王早已準備雄師百萬,銀灰色盔甲大兵壓城,殺死黃金甲叛軍。在此之後,場景從屠城血海迅速轉換到鮮花盛典,這是一段變血腥場面為焰火裝點亮麗天空的雜耍蒙太奇。我們看到鮮血流淌的台階被覆蓋、石雕被快速沖洗乾淨,上千人手捧菊花魚貫來到宮廷中間的廣場,他們擺花鋪地毯,頃刻瞬間就鋪滿鮮花遍地。導演讓我們看到帝王的大手筆,他突然翻手,轉瞬之間就將那座屠城之後死神還在空中翱翔和歡笑的宮廷廣場變為鮮花盛開的村莊。在我看來,這才是本片在視覺上最讓人感到有衝擊力和敘事上的最有新意之處。這一筆讓我意外,但是稍加聯想後又覺得十分熟悉。這種從令人震驚的暴力突變到水洗清場、鮮花盛開之間的突然轉換太有力了,它是一個令人驚嘆的段落,它具有視覺奇觀,在這天才地營造出的強烈意象中,有着可以多重解讀的意思,它值得我們好好品味。
儘管我不認同影片設計的戲劇情境,徹底地不喜歡這種為權威設計奢華的趣味和俯首稱奴的價值觀,儘管對這類大片進行簡單的惡評可以顯示批評者的藝術高明和政治正確;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張藝謀今天拍的電影首先是中國的領導還有百姓喜聞樂見的。但是,導演為什麼要拍攝這些充滿了陰森之氣的故事?就中國的現實語境和政治環境而言還有一點奇怪的是,張藝謀為什麼要拍攝這些具備明顯的歷史場景聯想、可能導致作品被管理部門攔截的場景?本片是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文本。
在榮格心理學的認識中,人的陰影是他的心理的一個方面,可以不被自己所覺察,面臨自己的陰影是十分痛苦的,並且是無休止的。可以認為,本片的創作者是在表現自我,但他同時也是在以此揣摩觀眾、迎合觀眾。這裏,作品形象體系中的意念要大於導演的動機,藝術品的形象要遠遠比創作者承認或者意識到主題要豐富、複雜得多。本片的導演和編劇很可能並沒有製造影射或者象徵來完成自己的主題隱喻,他們的創作是一種無意識指引下的形式衝動。創作者的確在盡力讓自己天馬行空發揮想像,但是這類影片能夠反複製作贏得票房是由於他們自己趣味和潛意識的直覺流動投合了當今中國社會的上下諸多人等的心理需求。
可以認為,《滿城盡帶黃金甲》顯現了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某些內容。不管我們喜歡與否,這種華美儀式的鋪陳和隨後的從暴力場景到夜空中的焰火綻放和鮮花廣場的轉換肯定是觸摸到廣大觀眾心中的敏感之處的。這些意象中有張藝謀揮之不去的心中塊壘,這也就是頑固地縈繞我們所有中國人心中,使我們長久迷惑、希望躲避而又無法逃離的心底情結。直覺地把握直覺,直覺地呈現直覺是張藝謀的重要天才或者說作為電影作者的主要天才。這部電影又一次成功地觸摸到我們民族的心理感應點。這一段意象在視覺上是強烈的,在敘事上也是有些轉折突然的。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十幾年前北京六三那個血腥的夜晚帶給中國人的震撼、驚恐在藝術中的呈現,也是對中國人之後的臣服和帝王表現權威、再次宣示規矩的一種藝術化的變形顯現。這裏我們顯然看到一種原型觸發轉化為藝術形象的時機和引爆點。「原始意象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碰到的問題相對應的平衡和補償因素,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為這種意象是幾千年生存鬥爭和適應經驗的沉澱物,生活中每一巨大的經驗每種意義深遠的衝突都會重新喚起這種意象所積累的珍貴貯藏」 所以,我們才會在《滿城盡帶黃金甲》、《英雄》、《夜宴》等影片中看到這許多充滿陰暗和受虐意味的場景。它是中國社會的歷史記憶引發出來的強烈意象,這是中國人心中某種集體無意識的藝術顯現。這裏面顯然有對突然降臨的暴力事件的震驚,也表現了震驚遺留下來的精神創傷,這種創傷的心理症候是:把荒誕當作必須接受的現實,把邪惡的暴力掌控、「勝者為王」當作亘古以來從不改變的天道。它也許是我們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是我們兩千多年來的歷史記憶、心理痕跡在當代經驗觸發、引導和規定以後的形式張揚,它是我們心理情結經過處理和變形之後的一種形象呈現。如果僅僅從《英雄》、《夜宴》和《黃金甲》營造的景象和觀眾的熱烈追捧來診斷我們民族的脈象,我們這塊土地上那個所謂「大寫的人」已經被打斷了脊梁骨。這還不算,這個斷了腰的人又掙扎着翻身起來,匍匐爬到威嚴而又仁慈、心狠手辣卻又兼愛天下的帝王腳下長跪不起、常跪不起。
必須承認,直覺地把握民族心理是張藝謀的長項之一。這類影片是我們中國人集體無意識被擠壓、被訓練、被強力指引和導向之後的一種走向,它是十分具有現實性的走向。但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它並不是必然的走向,不是所有人的心底潮流和藝術呈現的共同走向,它只是一種走向。僅就藝術性想像和影像呈現而言,它也是目前諸多品味中的一種,我們還看到許多不同的現實感覺和影像創造,只不過不在這一類古裝主旋律大片中而已。
四、第五代演唱「古裝主旋律」
除了極強的形式創造能力,張藝謀作為導演的另一個天才是本能地了解本能,他總是對社會心理有一種直覺的把握。90年代古裝主旋律影視作品的內在主題完全符合了官方用形象語言和藝術外包裝去建造政治合法性的要求。具體而言是在這些方面:1、由民族自豪感導向國家主義。形象展現是中國歷史悠久、哲學博大精深,山河壯麗。2、好帝王能發展經濟讓百姓過上好日子,百姓在這時就會高興(《荊軻刺秦王》、《天下糧倉》、《雍正王朝》)。以參照閱讀的文本還有一些國家形象宣傳片。同一時期,張藝謀和許多主旋律導演在專題片、MTV中用唯漂亮主義營造繁榮、歡樂的美麗新世界。張藝謀申奧片的核心創意就是孩子的笑臉。3、君王建造長城、征討異族維護了國家統一。《荊軻刺秦王》、《英雄》《康熙帝國》)4、殺人成為影片敘事中的重要題材,通過殺人的敘事編排闡述統治的合法性來源於力量,生產權威崇拜心態,以此形象地倡導犬儒主義的服從心態。這可以從《英雄》、《雍正王朝》、《荊軻刺秦王》等明顯看出,《滿塵盡帶黃金甲》是又一個標本,它的意義和心理結果更為複雜。這裏有一個事實比較引起我注意:同一時期的大陸青年導演也在影片中大量涉及死亡這個題材,但是在他們作品中我看到的是對死亡的迷惘和心理震撼而不是像在第五代導演作品中看到的更多是權威崇拜。
張藝謀們90年代以來為何把古裝主旋律電影電視拍得這麼符合宣傳部門的要求?第一動機是製片資本的要求,因為必須要考慮被主管機關審查通過。通過這種有形的、具體的要求、指令;通過禁止(《活着》、《藍風箏》、《霸王別姬》)和命令修改影片(《有話好好說》等)的訓練和馴服後,創作者的創作被納入主導意識形態的再現系統。張藝謀們被納入這個系統後,不光要呈現(自覺、不自覺地)一些思想指導者所指定的歷史解釋和和現實意義,還通過美學趣味和其中英雄形象的營造來再生產這種認同機制。中國的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不再把建立明確的、自圓其說的主義和信仰作為宣傳任務,而是將另一些價值(富有、國家主義)作為合法性來源,使用另一種心理說服的路徑和運作模式。這時,我們也看到了第五代主將們的形象系統產生了很大變化。
到了《英雄》,張導演探索了將「唯漂亮主義」與權威崇拜進行完美結合的風格,拍出了古裝主旋律的傑作。「在主題意念和政治取向上,《英雄》完全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陳凱歌《荊軻刺秦王》的傳統。這就是被業內稱為古裝主旋律的傳統。從《荊軻刺秦王》到《雍正王朝》一路走到《英雄》我們看到第五代導演的一個重大轉向。三個同學都走了一條由先鋒探索性電影向主導文化跑步的道路。在我看來,我們的導演把政治上正確變成了政治上保險。把沒有阻力當進步,把大眾心中病態心理情結作為商業賣點,把道義、人道這些電影中必然關心、應該關心的內容放在了兩邊。」 這樣,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同學就在「古裝主旋律」這面大旗下集合了:張藝謀塑造了《英雄》、陳凱歌講述了《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胡玫拍出了《雍正王朝》,高歌「世間萬苦皇帝最苦」、 陳家林重新打造《康熙帝國》、吳子牛蓋起為清官歌與呼的《天下糧倉》。這類影片呼應的基本是當下政治話語的宣傳重點:以清朝繁榮盛世直接比喻當前的富強國力、國泰民安、以對康熙、秦始皇的頌揚來表現當前的統一必要性和決心。
但是,要當武俠片、商業大片看,《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卻是一些十分另類的作品。從敘事學角度來分析,《英雄》的幾個敘述者都是圍繞皇帝來講故事、講道理,而且那個最終的、明察秋毫的的判斷者非常英明,他能洞察一切,一兩句話就揭出真情。這種圍繞中心式的敘事還與影片的空間設計相關:主人公每替皇帝殺一個敵人,他就可以在大殿上跟皇帝接近一步。如果聯繫結尾處秦始皇隔着長階梯把劍扔給刺客那個鏡頭來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敘事與空間相聯繫的安排是有深意的,它表現了帝王的絕對自信和雍容大度。在《英雄》當中,一切故事的真假、對錯都由那個刺客跪着請皇帝來評判。最後,作者試圖把那個惡名垂青史的殺人皇帝呈現為一個愛天下、愛和平、懂得大仁義的英雄。我在香港、台灣的武打片和武俠小說中從沒見過這種敘事設計。 大陸許多觀眾和學者是從影片作者流露出的那種權威崇拜來分析這部影片。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在為統治者的暴力提供心理合法性。
五、政治式寫作與紅衛兵情結
《英雄》、《荊軻刺秦王》、《滿城盡帶黃金甲》等部影片顯露了那一代人心底的紅衛兵情結。這種藝術文本是一種潛意識的流露和有意識編排的混合雜交體。創作者也許沒認識到自己內心深處是那麼懼怕權威、那麼崇拜權威。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殫思竭慮以為是精巧設計的創意和藝術追求怎麼就匯入集體心理中那幾千年積澱下來的權威崇拜心態。
在敘事電影的創作中,我們可以認為張藝謀們創作的古裝主旋律電影回到了他們在從影初期竭力逃避的電影形態:羅蘭。巴特所總結的政治式寫作,更準確地說是其中的革命寫作。羅蘭。巴特總結的革命寫作的幾個特徵在他們95年以後的作品中都有明顯表現。1)髙揚的抒情性。聽聽《荊軻刺秦王》和《英雄》的台詞、音樂就能發現這一點。《荊軻刺秦王》讓小孩跳城牆那一場的交響樂隊演奏大調音樂也有強烈的抒情性。羅蘭。巴特借用波特萊爾的話引證革命式寫作是「對生命中重大場景帶有誇張性的真實表達。」 2)暴力崇拜,不同於港台電影的將暴力浪漫化、純形式化、非表意化,革命寫作中的暴力描寫是要引起仰視,而且緊密地對應一個政治宣佈。在主旋律影片《淮海大戰》的片頭,有一個長長的移動鏡頭拍攝煙火爆炸、屍體,落幅是一個受傷的戰士對着逆光中升起的太陽,這是為了追求一種十分明確的象徵:革命烈士用生命催生新中國。在羅蘭。巴特看來,這種革命式寫作中的字詞形式、內容表達的誇張姿態,事實上對讀者而言「它本身就足以延續日常生活中的絞架」。「革命寫作要表達的就是這場革命傳奇的隱德來希:它用恐懼直擊人們的心靈,並迫使他們明白,作為一個公民,他們就應該認識到流血的神聖意義。」 3)描繪革命英雄。這類影片中的英雄不是港台電影中的英雄,那是個人主義的英雄。這類影片中的英雄都是國家的英雄,他們關心的都是天下、江山。我們常聽到這樣的台詞:「王要愛天下的人」、「護國護民」、「為了天下的和平」(節選自《荊軻刺秦王》、《英雄》台詞和字幕)。
|
同樣是80年代以思想解放為標誌的「新時期」脫穎而出的大師級人物,電影導演跟學者、文學家比較起來有着巨大不同,張藝謀們是這樣地與社會上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自然保護主義等思潮和新的電影敘事方法隔絕而與犬儒主義的主流思潮完全合拍。這是有意為之的拒絕,還是因為孤陋寡聞導致的隔漠?在筆者看來:引起這些變化的原因在於幾個因素:書報檢查機構明確而有力的導向、媒體的話語力量、他們自身的深層意識。具體而言是:1)電影機構的制約。與同時期的美術、文學乃至思想界的同齡人相比,為什麼電影導演更快地成為80年代的活化石?甚至更快、更集體化地退化到六十年代。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這個行業對工業運行機制和電影審查等一整套意識形態機構依賴性更大,所以更容易被馴服。2)中國式的後殖民話語、文革話語的壓制。到了90年代中後期,後殖民話語幾乎成了闡釋張藝謀、陳凱歌那些走向國際的影片的主旋律解說和唯一的分析角度。3)童年記憶、青春記憶的重要性。他們是紅衛兵,他們的青春在欲望被極度壓制和對權威的恐懼和崇拜中扭曲地度過。他們那時就用對領袖的捍衛和服從來為自己的所有欲望實現進行包裝和命名。他們的一切反叛、一切個體欲望爆發都是建立在保衛最高權威這個名目下的,因此他們看似危險的叛逆實際只不過是完全具有合法性的「奉旨造反」。他們的行動比歷代的農民起義要安全、保險得多。因為這種強烈的少年記憶,他們與「領袖」、「王」、「天下的王」所構成的施虐/受虐關係成為縈繞他們心中的永久情結。20世紀80年代短短10年的思想解放運動逝去以後,在90年代的強力導向氛圍下,人到中年的他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們心底的紅衛兵意識復活了。他們那一代人的青春記憶決定了他們紅衛兵的職責,紅衛兵身份和行為那時是他們生活的意義來源。今天,歸順姿態和在新意識形態指揮下的舞蹈是他們藝術家許可證和經濟上的利益來源。所以,他們成為了可以教育好的一代。這個年齡和過去經驗的共性群體,再次有先有後地出現了創作作品的共同思想走向。當然,也有因人而異的情況和個體的變化。越到後來,主旋律話語和政府宣傳、主旋律要求對張藝謀影響越大。而到了他拍攝《英雄》的時候,陳凱歌也有過轉向普通化、人情化的《和你在一起》。同樣是張藝謀的同班同學,顧長衛在2004年拍攝的《孔雀》以有趣味的劇作和極具力度的真實感描繪了河南小城安陽文革後期貧民的那些沒有陽光的日子。 作者通訊處:北京海淀區 西土城路4號 郝建郵編:100088 E-MAIL:[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