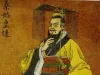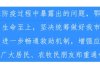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區分聚眾淫亂罪和性侵犯罪,經常容易引發爭論。
張三、李四、王五都是中學生,17歲;某天晚上,約着兩個學妹,趙一、錢二去看電影,兩個學妹都14歲。看完電影,五人決定再打把遊戲,快速提分。所以,五人一合計,就決定刷夜開房打遊戲,房費五人均攤,畢竟學生都沒有獨立收入,錢都是父母給的。白天還要認真上課,絕對不能打遊戲。令人震驚的是,五人在房間裏發生了性關係。過了幾天,女方家長得知此事後,非常生氣,帶着趙一、錢二去派出所報警,控訴三個男同學性侵。
司法機關在處理這種案件時,陷入了困境:三人確實承認發生了關係,但都主張學妹是同意的;而且聊天記錄確實也顯示,去賓館通宵打遊戲是由趙一提出來的,本來張三是準備回家寫作業的。但是,趙一和錢二卻主張,自己被三位男生誘騙到了賓館房間,最後被迫發生了性關係。總之,現有的證據有疑點,沒有足夠地證據證明男生在女生不同意的情況下強行與之發生關係。
是聚眾淫亂還是性侵犯罪?
面對此種情況,究竟該怎麼辦?
第一種觀點認為,雖然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三個男生強行與女方發生關係,但被告人和辯護人也沒有提供有利的證據足以否定三個男生沒有強行和女方發生關係。所以,從保護被害人的角度,還是主張構成犯罪,而且由於屬於輪姦,所以量刑幅度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但考慮到三人是不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所以可以從寬處理。
第二種觀點認為,既然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女方不同意,那麼有疑問時應該做有利於被告人的推定,所以應該做出無罪判決。
第三種觀點認為,把三個男的都放了,好像寬縱了但是,似乎對女方不公平,但如果把三個男的都當做輪姦來判,好像又太重了,可能冤枉他們。所以,還是折衷算了,構成較輕的聚眾淫亂犯罪,畢竟即便女的自願發生性關係,三個男的也系聚眾淫亂,屬於引誘未成年人聚眾淫亂罪。
《刑法》第301條規定了聚眾淫亂罪:聚眾進行淫亂活動的,對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參加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引誘未成年人參加聚眾淫亂活動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但這樣做,趙一、錢二似乎也會貼上犯罪分子的標籤,雖然他們沒有達到16歲,不負聚眾淫亂罪的刑事責任。
第一種觀點是所謂的「疑罪從有」,第二種觀點則是「疑罪從無」,第三種觀點則是折衷的「疑罪從輕」。對此,該如何選擇呢?很多同學認為我是「羅貫中」,所以肯定選折衷說。但這是否也是一種讓狐狸走向刺蝟的獨斷論呢?
客觀說來,三種立場都有合理之處,它反映的都是有限的人類如何儘可能地去追逐司法的正義。
刑事法治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在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中尋找平衡。如果只是強調懲罰犯罪,那其實無需成文法律,因為成文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國家打擊犯罪的手腳。因此,無論是《刑法》,還是《刑事訴訟法》,都必須對懲罰犯罪的國家權力(power)進行約束,防止打擊過度。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是每一個人中國人都應該知道的歷史教訓。
法治的一個重要作用,不是去追求最好的結果。因為人類的有限性無法在現世里做到最好,法治只是為了避免出現相對較壞的結果。
這就是為什麼在思考任何問題,都要降下「無知之幕」。想一想,如果你在投胎之前,不知道來到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你是希望出生在一個弱肉強食、強者通吃的世界,還是希望即便你再low再弱,作為人最基本的權利(right)也能得到保障的世界?
如果選擇「罪疑從有」,那麼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潛在的犯罪分子。李四看了王五一眼,王五說瞅啥瞅,李四說得罪不起我開溜,結果當天晚上王五被殺。警察懷疑是李四乾的,一旦進入懷疑的視線,那就怎麼看怎麼都像犯罪分子。李四手機上居然有王五的照片,李四居然對其他朋友說王五太壞了。雖然李四有不在場證據,但如何證明沒有僱人把王五殺了呢?
人類的有限性,在於我們對真相無法獲得百分之分的認識。如果只要有疑點你就有罪,那麼結果就是,說你有罪你就有罪,說你「刑」你就「刑」,不「刑」也「刑」。
那是不是就選折衷說?畢竟如果「疑罪從無」,可能就放縱了罪犯,對被害人不公平。如果降下「無知之幕」:你不幸成為了被害人,是不是也不願放縱罪犯?
《尚書》就曾主張「疑罪從輕」,所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意思就是:對於犯罪事實存在不清楚的,處斷一定要從輕;對有功於國的人,雖事實有可疑處,也應該從優賞賜。與其錯殺無辜的人,寧可犯執法失誤的過失。蘇東坡獲得榜眼的策論文《刑賞忠厚之至論》,就引用了《尚書》這句話。
「疑罪從輕」為何容易產生冤假錯案?
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有大量的冤案都來自於「疑罪從輕」的觀點,最典型的就是趙作海案。
1998年2月15日,村民趙作亮到公安局報案,聲稱叔父趙振裳失蹤四月有餘,至今沒有下落。接到報案後,警方對失蹤案進行了調查,確定了犯罪嫌疑人趙作海。趙作海跟趙振裳屬於同村的叔侄關係,但兩人關係不好。辦案機關懷疑,趙作海和村里一位杜姓女性有曖昧關係,兩人因為杜某爭風吃醋。趙振裳曾帶着菜刀沖入杜家,在趙作海頭上砍了一下。事發之後,趙振裳就失蹤了。警方調查三個月之後,在井中發現了一具高度腐爛的無頭男屍。當時法醫鑑定技術相對比較落後,加上屍體腐爛程度過高,根本無法辨認,死者究竟是誰。
公安機關遂把趙作海作為重大嫌疑人,於5月9日刑拘。1999年5月10日至6月18日,趙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一審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趙作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省高級法院核准一審上述判決。
在死緩的判決書上,對事件是如此敘述:杜女與趙作海、趙振裳均保持不正當的男女關係;1997年10月30日的晚上,趙作海與杜女在杜家發生不正當兩性關係後,被趙振裳撞見,從而引來趙振裳的追砍,趙作海奪刀將追在身後的趙振裳殺害。隨後,趙作海對趙振裳屍體的分解以及拋屍。
趙作海在服刑11年後,2010年4月30日,「亡」者歸來,被「殺害」10多年趙振裳突然回家。此事後被新聞媒體報道。2010年5月9日,趙作海被宣告無罪釋放。
事後,6名當年的辦案人員被認定為刑訊逼供罪,其中兩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兩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一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還有一人被免予刑事處罰。
之所以會產生趙作海案,也許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疑罪從輕」的思想。司法人員在辦理案件過程中意識到了疑點,但覺得「不能放過一個壞人」,「又不能冤枉一個好人」,那麼兩者之間的平衡就是判個輕罪算了,槍下留人,畢竟保了他一條命,也算對得起良心,心理也平衡了。從趙作海的角度,在死刑立即執行和死緩中選擇,死緩也不算最壞的選擇,被逼無奈也只有認命。所以趙作海放棄了上訴權,在服刑過程中也沒有努力申訴。
如果當時「亡者」沒有歸來呢?趙作海是不是就要一生背負殺人犯的惡名?降下「無知之幕」,有沒有可能你也會成為趙作海呢?降下「無知之幕」,即便你是被害人,會希望有着重重疑點的所謂「犯罪人」接受有罪判決,從而讓真兇逍遙法外嗎?
司法實踐中,有着大量的冤假錯案,其實都是「疑罪從輕」的產物。尤其當被告人在道德上有虧欠,司法人員在判他有罪的情況下,也會得到心理上的平衡—-反正不是好人,受點苦是應該的。
問題是,如果用嚴格的道德標準審視,我們誰是好人呢?誰沒有做過壞事呢?難道做過壞事就應該被當做罪犯嗎?我個人對法治的理解是,入罪必須講法律,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如果入罪講道德,只要道德有虧就有罪,那麼有誰是無罪的呢?但是,出罪可以講道德,因為法律只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種行為在道德是鼓勵點讚的,那麼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是犯罪。
然而,個別司法人員完全顛倒了這個邏輯:在入罪問題,你和講法律,他和你講道德;在出罪問題上,你和他講道德,他和你講法律。這種片面強調打擊的重刑主義思維,是法治的大敵。
這就是為什麼《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原則是「疑罪從無」: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作出證據不足、指控之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據說蘇軾當年在考場寫《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時,《尚書》的話其實引用錯了,他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誤記為「賞疑從與,罰疑從去」。這個誤引,也許更符合現代法治的精神。
回到文章開頭講述的案件來說,大家覺得選哪個選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