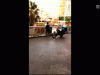張招弟的電動車不大,能擺得下外賣箱的位置只有座位下的踏板。外出跑單時,她必須用雙腳小心護住外賣箱,確保它不會掉下車,也不能劇烈晃動。否則,可能會面臨餐品灑漏、顧客投訴等諸多後果。對張招弟來說,這不是一份輕鬆的工作,但她需要這份工作。
張招弟跑外賣四五年了。上一段婚姻中,丈夫在工地幹活,早出晚歸,日常只有她和婆婆在家。但凡她待在家中,耳邊就儘是婆婆的嘮叨、挑剔和控制:「洗衣服要用手洗」「不要躺在床上」「什麼時候去上班」……每到此時,張招弟恨不得立刻「飛出去」。
成為騎手後,打開院門、跨上電動車的那一刻,她意識到,自己終於可以自由呼吸了。
穿梭於大街小巷的騎手中,鮮有女性。根據餓了麼的調研:九成以上外賣騎手為男性,八成來自農村。也因此,人們習慣性稱騎手為「外賣小哥」。
而就在諸多「外賣小哥」中,我們發現了一些名為「招弟」的女性騎手——她們大多成長於農村,大多有姐姐,大多也還有一個弟弟。
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被命名,映射的其實是他父母與周遭社會的價值觀。有人希望孩子聰慧美好,有人希望孩子飛黃騰達,有人希望孩子平安長大……而「招弟」的名字,從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未出世的另一人。
在外賣騎手這樣一個男性主導的行業里,「招弟」經歷了怎樣的人生?她們如何尋找生活的出口?帶着這些問題,我們找到了兩位「招弟」,聽她們講述起自己的故事。
弟弟招來了,我被遺棄了
張招弟34歲,出生在浙江最南端的農村。她有兩對父母,結過兩次婚,生了兩個女兒。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誰取的——原生家庭里,她是第三胎,有兩個姐姐。在她之後,父母如願生下了男孩。至於這個名為「招弟」的女兒,則在幾個月時被棄到橋下,一對殘疾人父母把她抱了回去。而這對殘疾人夫婦,在幾年後也生了兒子。總之,在這裏,生男孩似乎是每個家庭的任務,是每個女人與生俱來的「使命」。
「女孩讀書也沒什麼用,還不如早點兒嫁人」,當年在老家,誰不這樣想呢?慢慢地,張招弟也不喜歡上學了,「一心想着玩」。初中沒畢業,她就「出了社會」,打工掙錢。她做過各種工作——保潔、服務員,也開過三輪車載客,一個月掙兩千來塊,勉強能養活自己。
第一任丈夫是她在網上認識的。對方比她大10歲,做搬運工,張招弟不顧身邊所有人的反對,跟這個自己覺得「成熟」的男人走在了一起,生養了兩個孩子。
婚姻中,矛盾始終不斷。張招弟和公婆住在一起,想抱孫子的公公對生了兩胎女兒的兒媳很是不滿;婆婆控制欲極強,想要干涉她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於那個大她10歲的「成熟」男人,對母親言聽計從,矛盾升級時,會掐着她的脖子不放。每到這時,張招弟就想要逃走,「飛出去」。
張招弟離了婚。她先是回了親生父母家,父母很客氣,「這裏不是你的家,以後不要再來了」——彼時,她剛和他們相認幾年。於是張招弟又回到養父母家,從此和親生父母再無聯繫。
小縣城裏,縱使婚姻再不幸福,那也比離了婚強。當初反對她嫁給前夫的那些親戚朋友,都勸她去復婚。張招弟不聽勸,「明知道他家是個陷阱,我怎麼可能再跳進去」。為了躲避那些複雜的目光,每到過年,她都獨自躲在娘家的房間裏。時間久了,她逐漸封閉自己,不大出門,也不和人打交道。
「招弟」們人生最初的版本都有些類似。作為家裏的老二,羅招弟打小就知道自己名字的含義——連着生了兩個女兒,家裏想要個兒子。這在農村並不少見,羅招弟記得,同村還有一個女孩叫「引弟」。這些西北山村裏的女孩,大多讀到中學便外出打工,接着結婚生子,羅招弟也循着同樣的路,從村子走到縣城,接着一頭扎進婚姻和育兒中,只剩眼前的瑣碎,再也不見遠方。
做騎手前,羅招弟當了十來年家庭主婦。她初中畢業後開始打工,20歲結婚。丈夫在工地勞作,她就留在家裏帶娃,雖然也想出去賺錢,但「實在走不開」。大兒子長到8歲時,小兒子又出生了,羅招弟也便重複着餵奶、帶娃、接送、做飯、打掃等傳統認為女性該承擔的家庭事務。
羅招弟所在的寧夏縣城,沒什麼工業產業,男人們多在本地打工或外出務工,而對羅招弟這樣已婚已育的女性來說,工作機會寥寥無幾。即便是她早年打過工的那家超市,工作時長也無法兼顧幼兒或接送學齡兒童上學。
2022年,羅招弟家出現了財務危機。大兒子沒考上高中,最終決定去外地上職校,每年3萬多學費成了壓在夫妻心口的一座山。丈夫日常在工地打工,穩定的時候一個月也只能掙到五六千。
羅招弟愁得睡不着,尋思着自己怎麼也得出去工作。
也是有工作的人了
一次點外賣的工夫,40歲的羅招弟找到了工作——騎手來送餐,滿腦子都是找工作的羅招弟攔着對方問招不招騎手,接着她找到最近的餓了麼站點的站長,問了下需求和要求,直接上崗了。
做騎手是羅招弟幾乎唯一的選擇,這份工作門檻不高,時間自由,「干別的耽誤照顧孩子嘛,小的還在上學,要做飯、接送孩子。」
她的跑單時間完全配合小兒子的時間表。早上7點多送孩子上學後,開始跑單;中午是外賣點單高峰期,通常羅招弟做好飯後,11點多先把孩子接回家,自己出門跑單,下午一點多送孩子上學,再把熱在鍋里的飯拿出來吃幾口。晚上,她通常會跑單到8點多,如果孩子作業太多,就索性不出門。
在羅招弟站點裏,還有一位像她一樣的寶媽騎手。考慮到女騎手的家庭情況,站長沒有給女騎手排班。她們無需像男騎手一樣有出勤時段要求,而是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安排上線和下線時間。
在成為外賣騎手之前,張招弟在一家飯店做服務員,老闆嫌她手慢,把她開了。對張招弟來說,跑外賣自在得多——沒有老闆,也沒有婆婆在旁盯着,只要勤快點兒,她一個月能掙上還算可以的收入。
對羅招弟來說,送外賣最難的是找路。縣城不大,平房很多,騎手們不分區,都是一個人跑整個縣城。有時地圖上無法顯示具體地址,就意味着無法導航,只能給顧客打電話問路。
剛開始不熟路的時候,她一天只能送出十幾單。逐漸摸清縣城道路後,羅招弟送餐速度快了起來,兼顧孩子上下學吃飯的同時,她一天能送三十多單,這筆收入她很滿足。
對比現在每天出門工作,過去做家庭主婦的日子在羅招弟看來「無聊極了」。那些年,她每天做完家務,就自己在家繡鞋墊。十多年裏,除了陪親戚去北京看病和到隔壁省探親,她幾乎沒出過遠門。
跑外賣可不一樣,見的人多,心也漸漸開闊了。在站點休息的時候,羅招弟認識了不少朋友。一個下雨天,羅招弟敲開顧客的門,對方看到門外是濕漉漉的女騎手,硬是把她請進屋,請她喝了杯熱水。羅招弟不擅表達,她只說「遇到過好人」,這件事讓她記了很久。
找前夫打官司,我不怕了
我們的身邊,究竟有多少「招弟」?
在公安部「互聯網+政務服務」網站上,我們以人數前五的姓氏王、李、張、劉、陳進行檢索,發現這幾個姓氏中共有超過2.2萬女性叫招娣或招弟。據此前澎湃新聞報道,國內某省叫「招弟」之類名字的女性超過1萬人,其中,60歲以上叫「招弟」「迎弟」的人數最多,20歲以下的偏少。
招弟,她們的命運緊緊和家庭綁定在一起。
羅招弟說,沒怎麼想過自己的期望或需求,因為「條件不允許」。更何況,在這個小縣城裏,原本沒那麼多為已婚已育的婦女提供的工作機會。
成年人的世界沒有詩和遠方,她只是想着,找一份工作,能讓家裏日子稍微寬鬆些。跑外賣的第一個月,拿到工資後,她特地接上孩子,去外面飯館吃了頓飯。
今年張招弟再婚了。現任丈夫比她大四歲,認識沒多久,父母就催着趕緊領證。張招弟覺得這樣也好,畢竟「一個人也挺苦」,「條件好的,沒找到合適的或者不願意,可以不結婚。像我們條件不好的,哪有人會這麼想啊?都是為了生存。」
外賣還是要繼續跑下去的,這是她早就有的「覺悟」。剛開始打工時,張招弟的工資都上交給父親,她沒錢吃飯,再餓都得回家吃。她說這給了自己一個教訓:不能沒有收入,要掌握經濟權。
丈夫對她不錯,雖然家裏會催着她趕緊生孩子,但丈夫覺得如果張招弟身體不允許,就不生了。婚後,她又回到了和婆家一大家子生活的日子。兩代人生活理念上難免有衝突,新婆婆也依然免不了嘮叨,但張招弟不怕了,那輛馱着外賣箱的電動車是她逃離煩悶生活的出口。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孫萍教授的調查,近年來,女性騎手的數量一直在持續增加。通過訪談孫萍發現,這些女騎手多為已婚狀態,並育有至少1個小孩。撫育子女、分擔家庭負擔成為她們進入外賣行業的重要原因。
在適應了外賣工作後,部分女性甚至開始「翻盤」,將性別優勢轉換為勞動優勢,在這個男性主導的行業中展示出了更強的競爭力。去年的全國網約配送員職業競賽中,來自杭州的二胎媽媽黃曉琴奪得冠軍;查閱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各地勞模騎手信息中不難發現,如廖澤萌、田丹等女騎手的身影。
這不單是一份餬口的工作、一份生活的底氣,更是一個可以實現個人價值的出口。對於「招弟」們來說,一輛電瓶車和一個外賣箱,在她們人生的系統里,提供了有限度的自由。
當「招弟」們走出家門,面對更大的世界,有了一些選項和期待。
羅招弟眼下最大的期盼,就是大兒子職校畢業後順利找到工作。日子更寬裕一點兒,甚至還可以計劃一次全家旅行。
張招弟則說,她想找前夫打官司,要回小女兒的撫養權。女兒是她親手帶大的,她捨不得。她想着,自己再婚了,也掙錢了,經濟獨立,至少有了打撫養權官司的底氣。
「早點要回女兒的撫養權」,最近,她把這句話寫在了自己的微信簽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