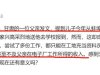本文作者白先生是一位從小縣城考進北京名牌大學的80後。在外追尋多年的他,回想起自己與父親的30年,想起當年面對父親的陰鬱,打算闖蕩世界,不魚死網破不足以明志,想起自己曾不顧一切地想要掙脫家庭束縛,進入一片廣闊的天地。然而大城市帶來的,卻是另一種撕扯。不僅如此,過去數十年代際變遷的結果,並不完全是進步話語中的解放與幸福,也不是一路奔跑無礙的狂歡,而是無形中帶有一絲俄狄浦斯式的命運感和悲劇感。
轉眼間,作者自己也已身為人父,也會想,該不該像父親當年要求自己一樣,要求自己的孩子如何克服命運的局限,為了一個縹緲的人生理想,忍受掙扎的少年時光?80後這代人一起見證了父輩肩扛重擔、解放自己的孩子,也一起見證了父輩的衰落,這是時代的宿命。那麼,面向未來的人們,又如何挑過這「因襲的重擔」、打開新的寬闊和光明?
01
「火車上小心,到了給我電話。」
父親站在春運的綠皮車廂外,車門像一個巨大的鼻孔,把黏稠的人群吸進去。
衰敗的縣城火車站有如一道佈景,映襯出父親起於青萍之末的衰老。
他從肩上把沉重的行李從窗口遞給我,「響兩聲就行了,我給你打過去。」
我大學畢業之後的半年,工作和讀書都沒有着落。在河南老家過了一個愁雲慘澹的過年之後,我給一位平素待我不薄的大學老師打電話,問問有沒有可能在他的研究所謀一個秘書之類的職位,他答應試試看。帶着決絕的信念,我收拾好行裝,打算從此闖蕩世界,把這個令我糾結的家庭拋在腦後。
現在回想起那段曾經令我壓抑、憤怒的青澀時光,竟有一絲無關痛癢的恍惚。想要再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居然如此艱難。而當時父母的陰鬱和親戚的奚落,讓一個二十出頭、滿腦子被形而上的問題填滿的小青年覺得有如世界末日,不魚死網破不足以明志。所有問題的核心,現在看來,無非是一個80後青年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不被父母承認而已。
我到武漢上大學的1998年,一些人文書店還能看到1980年代「文化熱」之後的出版遺骸,比如李澤厚的《中國思想史論》,《美學四講》,王小波的小說,海德格爾等等。對於一個從小就對「政治思想教育」滿腹狐疑的文科生來說,這些東西遠比大學課堂里的「九五規劃教材」有意思得多,而當時流行的哈耶克,簡直讓我陡然覺得多了一雙看世界的眼睛。帶着青春期的叛逆,我像上足了發條一樣和這個世界較勁。經常像個哲人一樣,抽着一塊錢三根買來的「白雲」,皺着眉頭在宿舍樓頂平台俯瞰着腳下芸芸眾生。我由衷地鄙夷那些中規中矩,英語和法學理論都能考98分的同學,以談論科斯、布迪厄等生僻的學術大師為能事,以「三農問題」、「左右之爭」為掛懷。1999年之後,大學擴招,學費陡漲,身邊那些「98分同學」也漸成異類,很多人謀劃着做點生意,或者準備出國,我這樣不務正業的學生就更加邊緣。
每個學年的寒暑假,是我和以父親為代表的家庭關係最緊張的時候,只有這段時間我和父親朝夕相處,彼此口誅筆伐。我們在很多問題上水火不容,一言不合我就摔門而去。我像個愣頭青一樣衝決家庭的羅網,認為個體意識的成長一定伴隨着精神上的「弒父」,而父親完全是專制主義的金牌代言人。我捧着《拯救與逍遙》之類的書,幻想着自己像舍斯托夫一樣去撞那道無形的牆。
在我眼裏,父親無法容忍任何異端,連我的髮型、服飾都要無端指責,更不要說我那夜讀晝伏的作息時間以及各種奇談怪論。而大學畢業之後的考研失利、工作無着,更被他看作是我多年來「懶惰、不務正業」種下的惡果。至於我那段時間灰色的心情和鬱結,父親好像根本就未加留意,我被這種十分功利的「唯目的論」傷透了心。我像個激進的左翼文人一樣,認為「家」是一切專制和不平等的淵藪,家庭成員的關係也充滿了叢林法則,一天都呆不下去了。
我在潮水般南下打工的兄弟姐妹們的縫隙中擠上火車,數九寒天出了一身大汗。身邊染黃頭髮的小妹正連拖帶拽把沒擠上車的同伴從窗口拉進來,交錯中看到父親閃爍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嘴唇,我低下頭不去看他。
火車開動了,黃髮小妹和同伴大聲和窗外親友揮手告別,站台漸行漸遠。父親不知從哪兒掏出一條毛巾,抽打混亂中蹭在衣服上的灰塵,接着是鞋子。我看着那個越來越小的身影,眼圈有點脹。
02
我家祖上是地主,其實也僅比貧窮人家多了幾畝薄田,並無僱工,但也算是耕讀傳家。祖父兄弟幾個都上過私塾,祖父寫一手好毛筆字,多年後我在老家的後牆上看到他幾十年前寫的村名,頗有顏氏風骨;五爺善國畫,幼時見過他的虎嘯山林圖,呼之欲出,令我驚駭。
父親出生於1950年代,兄妹五個。父親年幼時,祖父作為地主已經被打倒,整日批鬥,加上祖母去世早,無人看管,常年在驚恐不安中度日,很早就開始了少年樵夫生涯,撿柴到集市賣,編草帽、藤筐換點鹽,據伯父講,還常遭村中惡童追打。父親很少向我提及這段歷史,我只在他後來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讀到一節,說有天晚上賣柴回家,祖父剛結束一天的批鬥,耳根處不知被誰刺了一刀,鮮血淋淋,兄弟姊妹不敢多言,低頭默默吃飯。我懂事後,似乎聽母親提起過當年毆打祖父的兇手,父親回報的還是默默。
小學畢業後,村革委會主任拒絕讓父親升初中,挨了一年還復如此。大姑帶着靦腆的父親到主任那裏求情,當時的忍辱負重、低聲下氣已無法追述,可以想見一個狂亂的年代和乖戾的人性,給生性懦弱的父親造成怎樣的烙印。
費盡周折讀完中學後,父親當然沒有上大學的權利,在一所鄉中學當語文老師,暮鼓晨鐘,如履薄冰。我認識幾個父親當年的學生,他們無一例外地向我描述當年的父親是如何勤勉,如何五更即起夤夜不眠,一心撲在教學第一線。我猜想,父親應該是懷着一顆「黑五類」報恩的心,竭力贖掉出身帶給他的原罪。
進入1980年代,隨着我的降生和生活的漸趨平穩,父親開始寫作,給一些報刊當通訊員。大約1984年前後,父親的一篇通訊作品獲得了當年全國好新聞一等獎——我上小學三四年級時,還在思想道德教材中學到這篇作品。這次獲獎改變了父親的人生軌跡,當年30歲左右的他被拔擢為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從此步入仕途。
我上初中時,父親到鄉鎮當黨委書記鍛煉。我老家在黃河故道,有治水的傳統。那年春天,黃土地剛剛解凍,父親帶領全鄉的青壯年勞動力疏浚河道,身先士卒,不舍晝夜地趕工,落下了腰疼的毛病。1990年代,鄉村亂象已呈,追繳超生罰款,動輒扒房掀屋;各種攤派,「層巒疊嶂」。箇中情景,李昌平後來都報告總理了。父親天性善良,我曾跟他下鄉,田間地頭,隨處和老農攀談,絕無一點「幹部」的架子,但各種攤派收不上來,鄉財政自然吃緊,下屬多有怨言。於上級,他也不予打點,像一個農民,寧願把餘糧給兒女吃了,也不願進行一種投入產出式的官場博弈。對他而言,最大的成就,就是看着他的產品——我,能好學上進,出人頭地,突破他因為出身帶來的局限。而當時的我,說來慚愧,正在各種港片的刺激下,過着一種牯嶺街少年般的生活,和一幫不良少年嘯聚街頭,在校園內橫衝直撞。
好幾年前,我在一篇寫父親的文章里說,父親以一種清教徒式的禁慾苦行,和近乎自虐的奮鬥理念,走過他幾十年的人生歷程。現在看來,似乎還不僅是這樣。
人是時代的兒子。
他由衷地認同現在的時代,卻從未想過記恨過往。一些時代的弊病,他當然看在眼裏,卻以清者自清的姿態置身事外。也就是說,他自動過濾掉了三十年來的另一種無序,而把艱苦奮鬥當作最高的人生準則。
太多的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他以沒有上大學為憾(1980年代上了一個大專),便在四十多歲時自修了一個成人自考本科。考試前的數月,他每天5點多起床溫習功課。我告訴他自考監考很鬆,他不以為然,非要親力親為考出將近滿分的成績。他半生清廉自守,卻也無緣青雲直上,最後在1990年代末一次全省公開招聘中,考到異地為官,並以此證明「這個時代還是相信真才實學的」。
我們舉家遷到數百公里之外的另一個城市,父親像頭老牛一樣躬耕在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報答這個時代給他的另一份恩情。我第一次踏進那個舉目無親的城市和父母佈置簡陋的居所時,酸楚無端。他們和千百萬被時代挾裹着涌往各地的打工者一樣,自食其力、樸實勤勞,卻又無法改變冥冥之中的宿命。
03
幾年前我得了一場大病,父母把人事不省的我拖回家中治療。轉了幾次院後,我的肚子像個吹足了氣的氣球,一戳就爆,身上插了三根輸液管。主治醫生說再觀察一會兒,不行就開刀。我聽他在門外和父親耳語,好像是說你這孩子要是熬不過今晚的話,說不準就完蛋了。說完又跑過來握着我的手說小伙子你要堅強一點,以後還有大好的前途云云,讓我感覺像在安慰一個要槍決的犯人。父親愁眉苦臉地蹲在病房門口抽煙,我虛弱地央求他別抽了,嗆得慌。他像扔掉一團火一樣把煙甩了,狠狠踩熄,我從未見他動作如此利索過。他雙手撐在床邊眼巴巴地看着我,眼睛由於幾天不睡而充斥着血絲,胡茬像冬天的殘草般佈滿又黃又黑的臉。在那個無邊的黑夜,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家族血脈的綿延,自己身上承載着父親畢生的重託。
命運兜兜轉轉。大學畢業的第二年,我考進北京一所名牌大學讀研究生,之後到「體制內」就業、成家,一切顯得順風順水。少年時的種種乖張也似乎漸漸消退,我和父親之間的隔膜好像變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類似客套的東西。父親已經習慣抽煙時給我一根,我也習慣了父親打電話問完我的近況後,貌似不經意地提起某個親戚朋友遇到的麻煩,問我「能不能儘可能幫助解決一下」。
我曾經不顧一切地想要掙脫家庭的束縛,進入到一片廣闊的天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然而大城市帶給我的,卻是另一種撕扯。
在這個急速現代化的時代,每個人的心靈都是一塊化石,層層疊疊,積澱了太多變遷。想想父母的背井離鄉,和自己十多年來的漂泊,常常讓我不知身在何處,又去往何方。社會學家說,這是一個無根的現代性,我卻感受到了作為個體的無根感。弗洛伊德教會了我們「弒父情結」,時代也不斷地「弒父」,問題是,「弒父」之後怎麼辦?
所以,我常想起魯迅所說的「因襲的重擔」。我們如何背負這因襲的重擔,又如何肩住黑暗的閘門?我又回想起當年,說起文革時毆打我祖父的兇手時,父親的默默。和家族史一樣,時代如何讓仇恨及身而止,讓一切痛楚、怨毒,停留在自己的肩頭?
想起當年姜文導演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上映時,我讀到一個朋友的影評,「爸爸的爸爸死了,兒子的兒子生了。一輩子接着一輩子,總有槍聲響起,也總會有安息。家族的理想,和族群的理想一樣,都經過死亡,也經過新生」。
轉眼間,我也身為人父。深夜不寐時,我也會想,我會不會因襲父親「嚴於律己,亦嚴於律人」的苛刻?會不會像父親要求自己一樣,要求自己的孩子如何克服我命運的局限,為了一個縹緲的人生理想,忍受掙扎的少年時光?我和這代人一起見證了父權的衰落,父親的背影從高大走向衰老,這是家族史的宿命,也是時代的宿命。而我要做的,只是肩住自己的閘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