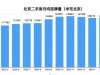網上看到一篇有關北京知青下鄉插隊部署工作的文章,勾起了我與北京知青一起生活的一段回憶。
1966年文革開始,大學停止招生,工廠停止招工,城市的中學畢業生,除了留在學校繼續鬧革命,別無出路。據北京市勞動局統計,到了1968年7月份,北京市三年累計畢業生已達25.8萬人,形成了巨大的社會壓力。
於是中央出台了「上山下鄉」的戰略部署,在半年時間內,北京市開展了三次上山下鄉大動員,目的地分別是東北、內蒙古和山西。這三批都是通過辦學習班,憶苦思甜、鬥私批修教育,由領導動員、學生自願報名組織的,但只完成了五萬多人,是全部畢業生的一個零頭。
可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於當年的12月21日發表了著名的重要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就是命令,自願不自願都得服從,從此掀起了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插隊落戶運動。
1968年12月初,我們村迎來了北京來的十多名中學生,他們應屬於那批自願報名來山西的三萬兩千人之列。那年我十一歲,正在本村上五年級。
知青們是被公社那台唯一的機動車,蘇制「小嘎斯」送來的。小卡車就停在我家的打麥場上,大隊組織了群眾敲鑼打鼓來歡迎。知青們除了自己的行裝之外,還帶來一大捆《毛澤東選集》,是北京市政府送給我們村的革命禮物,每戶都分得一套「紅寶書」。
我們這個小山村一共只有二十幾戶人家,家家都住土窯洞,生產隊並沒有可用的住宿地方,只能把他們安排到社員家裏。實際選擇的是我家和我堂伯、堂叔三家,每家各分了四五個。說來有意思,知青是來和貧下中農相結合的,可我們家是中農成分,堂伯和堂叔兩家還都是富農,屬於「階級敵人」呢,也不知道這幹部是怎麼想的。
我家分來四個女生,穿着打扮整齊劃一,都是那個年代北京女孩的標準形象:頭上梳兩條齊肩短辮,一身灰布衣服。上衣是北京特有的那種半長棉大衣,那種大衣在改革開放初期曾風靡半個中國,我在北京上大學時,老家不少人都托我給代買過。知青的衣服並不是新的,有些褪色,但很乾淨得體。
我家向陽的小北窯被騰出來給知青做了宿舍。這窯本來是我與哥哥住的,我們不得不搬回到大東窯,與父母和妹妹共享那兩個前後相連的大土炕。北窯里原有一個炕,可睡兩人,爸爸又在地面上用木板和條凳搭起一個簡易大床,供另外兩位用。
知青們自己開伙做飯,剛開始糧菜供應是由上面負責的,標準遠遠高於村民。普通社員家裏的主食都吃粗面饃和鹹菜,但知青吃的是白面饃和炒菜,只是村里人發現他們蒸的饅頭硬得能打死狗。我的一位大學同學是「老三屆」的北京知青,剛巧當年也在晉南插隊,他證實了我的說法,認為他們當時吃飯上真沒受苦。
當地人稱知青為「洋學生」,這個稱呼沒有貶義,只是很形象。因為他們是大城市來的學生而已,我們本地也有中學生,從沒人管他們叫「知識青年」。
「洋學生」雖然每天與社員一起下地,但生產隊並沒拿他們當作重要的勞動力。看待他們就像那些上面派來的「蹲點幹部」一樣,知道他們過段時間就會走的,不會長久。再說了,隊裏畢竟就是那麼多地,那麼多活,在那個生產條件下,多幾個知青不會使地里多打糧食。因此對他們的勞動沒有嚴格的要求,像挑擔、駕馭牲口等重活、難活也不會安排他們干。所以知青小團體和村民始終是兩張皮,並不能像領袖期望的那樣,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打成一片;或者說像一坨黃泥與一坨紅泥揉在一起那麼簡單。
上級也注意到生產隊並不能有效地對知青「再教育」,後來就把他們歸屬到了大隊林場,吃住條件不變,只是幹活在林場。大隊林場管理着一百多畝蘋果園,那時候果樹不施肥也不澆水,一年裏就是剪枝、噴農藥、摘果子這三件事,活路簡單而不重,員工不多便於管理。蘋果快成熟時,有村民路過看到有「洋學生」在吃蘋果,還用小刀削了皮,很是憤憤不平。認為他們能天天隨便吃蘋果就是莫大的福利了,還要削了皮吃,太嬌性了。
我家的四個知青姐姐,性情各異,特點分明。最成熟穩重的是王志賢同學,一看就是班幹部的模樣。她平時表情矜持,言語不多,沒見過她高聲說笑。但在開大會時,她總是代表知青發言,慷慨激昂,立場鮮明,能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很快就入了黨,第一個抽調回城走了。
另外兩位徐淑英、張連弟,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形體反差很大,但卻又形影不離。倆人屬於那種老實本分、默默無聞的類型。她們在村里呆的時間最長,好幾年都沒有撈到回城的機會,好像真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孩子。最終當地政府安排她們進了縣裏的機械廠,當了工人。我去縣城時看過她們,一身藍色工作服,帶着些許油跡,在那個時代也是讓人羨慕的工人階級形象。再後來她們年齡也大了,就在當地結婚生子,一直干到退休。據說孩子享受了政策照顧,去了北京。
四個女知青中,個性最鮮明的是盧平姑娘,身材嬌小,圓臉大眼。她性格活潑直率,能說愛笑,每天的話要比其他三位加起來還多。可能是性格上的差異,她與其他三位的關係不怎麼融洽,出出進進總是一個人耍單幫。晚上收工在家很無聊,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連電燈也沒有,我們村不通電力。盧平總會跑到我們家住的窯洞來,和我們一起聊天。我爸爸提醒她要和同學們處好關係,她振振有詞地說,她們三個人不可能長期好,只有兩個人才可以長久保持好關係。
我也最喜歡找盧平玩,她給我看她的壓箱底的寶貝:一張大大的手帕,上面別滿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毛主席像章,讓我大開眼界,她也送了一枚給我。最神奇的是那個夜光像章,用手電筒照一會兒,就會在黑夜裏發出燦爛的光芒。
春天來了,我用紙盒養了幾隻蠶當寵物,她就天天和我一起伺弄:餵桑葉,清理糞便,直到蠶寶寶成熟結繭。蠶繭都是銀白色的,但盧平說,北京的蠶結繭是彩色的,有紅的、綠的和黃的等等,我將信將疑。後來我確實也養過彩色的蠶種,但只有紅色和黃色,並沒有綠的,看來她說話有一定的水分。
盧平也跟我爸爸媽媽聊村裏的人和事,常常會用階級鬥爭的觀點給人定性,爸爸不同意,她就說:「大叔眼大無神,不分敵友。」
到第二年秋天時,盧平的妹妹也中學畢業了,從北京跑來看姐姐。盧平很高興,特地領妹妹「二平」見我。二平比姐姐小一歲,長得比姐姐秀氣文靜,沒那麼多話。再後來盧平也走了,不是抽調回城,而是隨妹妹一起去安徽農村了,據說那兒是她爸爸的老家。
轉眼間,半個世紀就過去了,我與四位知青姐姐走過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只是在那個特定的時間、地點軌跡重合到了一起。回想我們共渡的一段短暫的歷史時光,真實體會到了那句名言:在歷史長河中,個人只是一粒隨波逐流的沙子,大浪把你帶到哪裏,就在哪裏上岸。如今我都成退休老人了,她們也已年過七十了。我真心希望她們身體健康,生活幸福。
2022年2月21日於三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