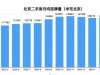西方不能沒有耶路撒冷,正如中國互聯網的歷史不能沒有華清嘉園。
華清嘉園是一個位於北京海淀的居民小區,佔地190畝,擁有23棟居民樓、97個單元、1776個停車位、2475套房子——既有37平的開間,也有177平的四房,周邊更是配套有19家髮廊、8家咖啡館、5家按摩和3家保定驢肉火燒。
這塊地最早的主人是京圈房企的老大哥——首創集團的劉曉光。首創於1994年拿地,但到了96年因為經營困難轉手給了另一家京圈樓企,樓面價4000元一平,在當時可謂獅子開口級的天價,圈內人都嘲諷:接盤者是傻子嗎?
新東家接手後馬上動工,項目前兩期叫「東升公寓」,第三期改叫洋氣的「華清嘉園」,跟斜對面的清華隔街呼應。小區2000年開盤,首批售價5000元/平,群眾直罵太貴,不過後來表明:有的事兒你以為是巔峰,其實只是開始。
開盤第二年,華清嘉園單價突破7000元/平方米,2005年破萬,2006年破2萬,2010年破4萬,2012年破6萬,2013年小戶型單價一度逼近10萬,震驚了整個樓市。14年短暫回調到了7萬左右,之後又是一路飆漲,2020單價已有報價突破16萬。
華清嘉園之所以兇猛,離不開其「上風上水」的位置:西臨中關村、東靠五道口、南連知春路、北接清華園,撒泡尿能濺到三個博士,扔塊磚能砸中五個碼農,更有宇宙名校中關村二小等作為學區配套,其20年漲30倍便不算離大譜。
但全國漲幾十倍的樓盤千千萬,憑什麼華清嘉園能在歷史上擁有姓名?
原因自然是那些從這裏走出去的互聯網新貴們:王興的校內網曾租在13號樓805,吳世春的酷訊曾經租在11號樓1706,宿華和程一笑曾經租在7號樓305……穿過小區的格子衫海洋,你還能找到張一鳴、徐易容、陳安妮等人的影子。
靠着「大佬們曾經戰鬥過的地方」這個標籤,華清嘉園成了互聯網人的「革命老區」。而沿着小區東門的13號線往北,穿過清華園便是上地、後廠村和西二旗,這些曾經是一片農田和墓地的地方,現在則擠滿了互聯網公司,鱗次櫛比,密集如麻。
在華清嘉園房價飆漲的日子裏,學生們背熟《程式設計師面試寶典》湧進大廠,美元基金拿着一疊疊TS撒胡椒面式投資,西二旗地鐵站人潮洶湧,沙丁魚罐頭車廂里總有人一邊着吃韭菜盒子,一邊焦慮地思考未來上市主體到底是放開曼還是放維爾京。
那可是黃金時代啊,敲鐘此起彼伏,融資蜂擁而至,美元滾滾而來,未來的《互聯網詞典》上一定有一句:張華在後廠村當程式設計師,期權量足;李萍在vc投互聯網,carry豐厚;我在五道口鏈家賣學區房,月傭十萬: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莎士比亞說:這些殘暴的歡愉,終將以殘暴結局。

在中國房地產及互聯網發展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海淀「華清嘉園」居民小區(網絡圖片)
2019年短視頻大戰的時候,北京互聯網圈流傳着這樣一個段子:微博的一個初級算法工程師,先是被內推到了抖音,薪酬漲了一倍;3個月後從抖音被挖到了百度,package漲了50%;半年後從百度跳到快手,又漲了30%,還給了不少期權。等於一年裏繞後廠村兜了一圈,什麼也沒幹,但薪酬是之前的3倍。
這種荒誕情節,是發生在中國過去二十年裏諸多「互聯網大戰」的一個不常見的註腳,但毫無疑問,互聯網已經成為中國寒門子弟階層躍遷的黃金通道——改革開放後,高考、下海、炒房等都短暫地引領過這個通道。顯然,現在輪到互聯網了。
中國高校最早開設計算機專業的年份是1956年,學生們需要學習枯燥的程序語言,跟塞滿電路板的冰冷主機打交道。90年代互聯網和帶圖形界面的PC機逐漸普及,計算機專業熱度開始提升,而2000年後國內web1.0公司崛起,待遇開始明顯拉開跟其他專業間的距離。
2010年移動互聯網爆發,大廠薪資更是芝麻開花節節高,北大青鳥的Java培訓超越了藍翔的挖掘機和新東方的湘菜專修,清華姚班和交大ACM則在知乎和微博封神,甚至連幾歲的小孩子,都在各種少兒編程班裏寫下人生的第一行「hello world」。
程式設計師成了少數幾個能入丈母娘法眼的職業。在深圳,相親市場上的姑娘們優選鵝廠男(鵝廠:指的是騰訊,這種稱呼不含有任何感情色彩,只是一種代稱),次選華為男;在杭州,小康家庭的美女要托人才能在阿里內網上發徵婚帖;而在江西上饒,有家長打出「恭喜xxx月薪18000入職京東」的紅色橫幅,場面堪比喜提高考狀元。
一首民謠這樣傳唱: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貧農,70年代嫁軍營,80年代嫁文憑,90年代嫁富翁,2000年代嫁碼農。
互聯網大廠的HR顯然比媒婆和紅娘們更焦慮,2015年雅虎北京全球研發中心關閉,其辦公地點清華同方大廈門口便上演了搶人的「名場面」:上百名HR和獵頭聚在一起,試圖拉攏那350名剛拿到N+4的雅虎員工,不少美女高舉着廣告牌,有的寫着「入職就送iPhone」,有的寫着「B輪獨角獸急尋CTO」,有的則寫着「雅虎的哥哥,我們幫你繼續牛」……
各行各業的人都湧向互聯網,搞地產的,開會所的,賣情趣用品的,甚至有山西煤老闆也在華清嘉園租個房子做起了App。他們躊躇滿志,擁有張一鳴的野心和100遍《社交網絡》觀影經驗,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則是:萬事俱備,就TM差一個程式設計師了。
熱潮似乎也映射進了國產影視劇中:早年IT技術男是《蝸居》裏的小貝——一個女朋友因為房子而跟領導偷情的苦主。而現在,國產劇中的程式設計師形象雖然還沒能像《黑客帝國》裏的那樣酷,但起碼能在《我的經濟適用男》裏跟佟麗亞搭CP了(CP:即Couple的意思,特指存在戀愛關係的情侶)。
高管們則更是財源滾滾。2005年百度上市造就了8位億萬富翁,9年後阿里上市把這個數字幾乎加了兩個零,甚至連千萬富翁都有1000多名,而京東、拼多多、美團、小米、映客、虎牙、貝殼、快手等公司的上市都讓一大批人獲得了財務自由。
當然,這些滾燙的錢,最終還是會像洄游的大馬哈魚一樣精準找到它們的故鄉:房子。
一個精通時事的海淀房產中介這樣回憶:字節、快手和騰訊的人偏愛200平米左右的大戶型,年終獎前出手比較多;百度和網易的員工買兩房三房佔多數,不過動不動就全款;小戶型主要是新浪和小米的人在買;似乎沒怎麼見過搜狐的人。
海淀學區房只是內卷打工人門的選項,互聯網資本家顯然有更高追求。在上海,套現成功的創始人們喜歡收藏一套翠湖天地;在深圳,毗鄰口岸的深圳灣一號成為南山新貴們的標配;在北京,華清嘉園只是剛需入門款,new money們扎堆的順義別墅區,才是納斯達克敲完鍾後的下一站。
互聯網富豪們的畫風或許跟煤老闆們完全不同:他們通常穿着樸素,帶蘋果手錶而非百達翡麗,坐商業航班而非私人飛機,加班熬夜996,不會搞36輛悍馬的娶親車隊,也不會在晚飯前去望京買下兩個單元,但他們的財富積累速度和在輿論場中的號召力,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
因此,當順義媽媽們聚在一起討論自家老公的跟投項目時,當烏鎮的飯局觥籌交錯暢談下一個萬億風口時,當杭州的保時捷銷售在朋友圈預祝螞蟻順利上市、開曼和新加坡的新註冊Family Office如雨後春筍湧現時,氣氛一下子就變得蓋茨比起來了。
多少年後,人們會怎樣回憶這些浮華和躁動?
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納斯達克寒風呼嘯,國內互聯網公司也一片蕭索。在當年的12月12日,一場名為「資本市場發育十周年」的會議在上海舉行,國家信息中心一名姓劉的副主任,發表了題為「新經濟與資本市場和風險投資」的演講。
在演講中,他明確指出儘管近期納斯達克市場出現了一些波動,但「以互聯網為依託的新經濟仍然不斷地滲透,不斷地擴張,成為影響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國際分工和國家競爭力核心的因素。」他分析了美國、日本、英國等國家的數字經濟政策,然後又總結了中國政府「十五」信息化規劃的框架,最後旗幟鮮明的給出了結論:「大的趨勢十分明確,我不認為周期性的因素會干擾結構性的變化,因此對大的方向不應該產生困惑。」
20年後重讀這篇演講稿,依然覺得內中觀點極具前瞻性,令人醍醐灌頂。
互聯網經濟引領了本世紀頭20年,在創造了無數財富神話的同時,給中國帶來了切切實實的效率提升——超過1000萬的直接從業、幾千萬的間接從業、全球靠前排的數碼化能力……在疫情的每時每刻里,誰又能否認互聯網對社會巨大的正面作用?
但狂飆了20年,這個行業也越來越步履沉重,證據之一便是接近見頂的互聯網滲透率。截止到2021年6月,中國已有71.6%的互聯網普及率和10.11億網民,五環內外的用戶們都實現了「抖音自由」,該下沉的地方幾乎都已經下沉了。
證據之二,是創新模式正在枯竭。過去20年大多數的互聯網創新本質是下游模式創新,但如今,包括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在內的幾乎所有領域,巨頭們都用劍和犁翻了無數次,在上游技術創新停滯的當下,留給大廠想像力的僅剩下個別戰場。
一個時代到了告別的時候,它不會簡單地跟你說一句再見,而是會充滿儀式感地跟你傾訴100句蜜語甜言,拼命地暗示「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而那些仍然執着於舊範式的人們,只有在經歷過無數次受傷後,才會最終迎來自己的夢醒時分。
接棒華清嘉園的,會是浦東張江的中芯花園小區嗎?這個問題正如「硬科技會接棒互聯網嗎」一樣,誰也猜不准。但用一個樓盤來表徵一個行業,其實暗含了一層隱喻:互聯網和房地產是過去20年經濟的兩大範式,它們幾乎同時遇到了落幕時刻。
過去四十年裏,我們目睹和親身經歷了無數黃金時代的結束:鄉鎮企業黃金時代的結束,「三來一補」黃金時代的結束,煤老闆們黃金時代的結束,基建工程黃金時代的結束,房地產黃金時代的結束……很多時候,體面的告別,就是最好的告別。
時代一路走來,時代一路遠去。沉浸在舊時光影的人們,到了需要翻到下一頁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