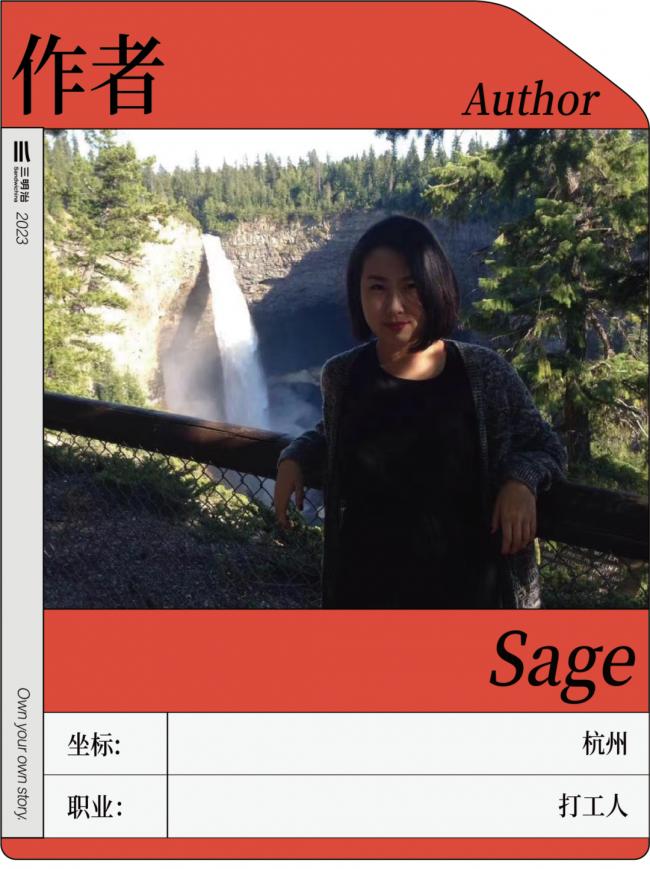邵逸夫醫院急診中心的門口有幾排木頭長椅,供家屬抽煙休息。現在想來這個設定倒是非常的合理和人性化,畢竟誰不需要從渾濁的搶救大廳掀開重重的塑料門帘出來透口氣呢。
春天的杭州就算是在深夜氣溫也不能算太涼,我盤腿坐在椅子上吃已經涼掉的漢堡和冰已經化掉的可樂。不斷有人從陪護區走出來抽煙。杭州這個季節的雨下個不停,毫無規律可言。急診部巨大的,從幾公里之外都能看到的燈牌倒映在潮濕路面的積水裏。
推着爸爸的急診輪床做完所有的急診檢查,等來報告已經過了零點。當天晚上住院部已經沒有床位,只能先在留觀室過夜。我送走了一起跟着救護車來的我媽和親戚們。點了那份漢堡外賣,從我被從加班會議中叫回家,整整六個小時過去了。
黑暗中,在只有監控儀上的曲線和數字在跳動。我不斷調整坐姿,一會兒把腿架在他的床尾,一會兒趴在床邊的小桌板上,企圖坐在椅子上眯哪怕連續15分鐘,卻一直被隔壁床位不停咯痰的大爺吵醒。帘子掀開的時候,我看到了他從被單里露出來的雙腳,像枯枝般安靜而毫無血色的垂在雪白的床單上。
六小時前,我趕回家的時候,爸爸已經側躺在書房地板上無法動彈。我跑下樓去小區門口接救護車,開始下小雨了,一點點打濕擔架上的一次性床單。
醫院的急診SOP讓人眼花繚亂,醫護人員給的指令簡短又模糊。為了節省時間,保證我不在跟急診醫生溝通的過程里被打斷,我把所有想要問的問題寫在備忘錄里,不斷增加,不斷修改。把手機屏幕按滅又刷開。我在並不大的急診大廳來回快速穿梭,排隊檢查拿藥繳費,在20幾度的天氣里竟然也走出一身的汗。
檢查結果出來,初步判斷不是血栓問題,而是耳蝸神經失調導致的嚴重眩暈,這讓我多少鬆了口氣。
他酗酒30年,我經常開玩笑說他一定最後會喪命於此。
「你小心嘴歪眼斜護工打你哦。」我說。
「臭丫頭,「他一邊喝酒一邊說,」你嘴真是不饒人。」
好了,我咬下一大口已經冷掉的漢堡心想,至少這次我們還算是走運。
去年年底的時候,有個朋友在群里發了個星座專家分析的2023年星座運勢。我打開滑到了雙子座那一塊,專家說,我上半年的日子沒可能沒那麼好過。但是也沒說,這麼不好過。
距離春節還有兩天,媽媽說她偏頭痛。痛得厲害,口服了所有我為新冠準備的止痛藥還不見效。我當她是操心操的。姥姥姥爺開始行動不便,他們兄弟姐妹直至那天,還沒決定誰去陪伴。這是幾乎每年她都會煩心的事情。好像去年,前年,大前年也是這樣。只是今年更嚴重一點。
我僥倖地希望可以全家過個順利的春節,讓我在經歷了近一年996的日子能睡個懶覺。結果在除夕那天,我被從床上叫起來,她頭痛到在床上打滾尖叫。
在所有三甲醫院馬上放假之前,我在互聯網醫院掛上了專家號。「考慮帶狀線皰疹」,多虧了這位遠在外地過年的醫生說的這六個字,我抓起鑰匙下樓,跑遍了附近所有藥店,拿着這張處方湊齊了藥品。
我眼睜睜看着她對身體失控的焦慮和情緒的崩潰。我自責,明明不久前剛看過關於帶狀線皰疹的科普,甚至樓下快遞柜上有一整面牆的宣傳廣告。但又深感失控,我的能力太有限了。我怎麼也跑不贏時間。我躺在她臥室外面的沙發上陪護,每一個小時起來餵藥,倒水,切水果,熱那一鍋一次只能喝一點的粥。講講我最擅長的笑話。
每一種藥都不一樣,有白色的黃色的粉色的,一天一次的,一天三次的,有隻能吃7天的,有需要遞增服用,到峰值的最大藥效之後再依次遞減的。我提前分好這些藥片,再在固定的時間遞到她手裏,看她吞下去。在這個場景里,好像我是那個媽媽了。
我跟朋友開玩笑說我真的挺幸運的,陪床的日子從除夕到初七。從放春節假期到直接無縫上班,至少沒讓我過上更加讓人頭疼的,一邊上班一邊陪床的日子。只是這份幸運沒延續太久,我媽給我發來了速回二字的微信,這次爸爸緊急住院了。
有些事情我有點搞不清楚。
我16歲離開家,19歲出國上大學,再過了整整8年後才回國與父母同住。過了這些年,我們都不知道對方的角色是什麼,因為看上去,好像這八年間我們並不彼此緊密需要。他們把我當高中生,我把他們當作,尚未開始衰老的中年人。
在這熬人的求醫時間裏。在邵逸夫門口的長椅上,在住院部等漫長的電梯時,在睡在沙發上陪護的時間裏。我感受到身體裏的變化。我聽到自己在不受控地蹭蹭長大。這不是青春期的那種不顧一切橫衝直撞的成長,而是另一種,伴隨着擊打聲和鐘聲的變化。
經過這次項目管理,我好像升職了,從家庭基層升職成為了擁有一些決策權的管理人員,擁有了我從再次和父母同居開始就想要的一些話語權。只是我當時絕對沒想到,這伴隨着父母永不回頭衰老的開始。
他們開始聽我的意見,去哪個醫院,掛什麼號,什麼時間複查。醫院複雜的操作流程和下不完的app小程序給與了我某種特殊的權力。
「能不能麻煩你,給我或爸爸掛個號。」媽媽說。她的眼神變得溫和。她從前不是這樣的。從前我希望她溫和,現在卻又不想要了。
十年前我在上新聞學院的時候好像的確學過什麼「媒介即信息」,「掌握了媒介的人就有了統治權」這類的概念。只是沒想到現在才徹底理解了,更沒想到的是在這個場景下理解的。
五月底我過生日,melody和cello,我從高一就認識的好友,特地從外地趕來為我慶生。
「把蠟燭吹了,慶祝我們又長了一歲。」
「雖然坎坷,但是長大總是值得紀念的嘛。」melody說。
半個小時之前,她倆偷偷計劃着給我買了個蛋糕,我有點不好意思。我們都是16歲離開家,早已習慣獨自一人面對生活。誰還沒過過幾次無人記得的生日。
我們拎着蛋糕從商場走出來。melody去接她媽媽打來的電話,她爸爸的心臟搭橋手術定在了下周。
「好好,你放心,我知道。」她說。
「沒事的」cello說,她爸爸剛在去年做了類似的手術。「你信我。」
「我信你我信你。」她拍拍cello。
我坐在旁邊看着她們,我的好朋友們,兩隻手無處擺放,覺得安心又酸楚。安心的是我們早已是父母的依靠。酸楚的是,我們也都不得不成為父母的依靠。
16歲我們壯志未酬,想着大學,想着未來成為大人的生活。現在沒想到談的最多的,卻是這個話題。高中畢業後我去了加西,花了8年時間在太平洋邊上的城市裏,最終回杭州定居。cello本科去了加東,又輾轉香港讀了研究生最後入職北京的銀行總行。Melody則在美國讀完本科後去了澳洲讀研,在回國和移民之間搖擺不定,現在暫居上海。
沒人開口說,但是我們都清楚的知道,這種陪床的日子對我們來說顯然只是個開始,必定之後還要面對越來越多類似的日子。
「我現在最擅長的我跟你說。「cello吸了一口飲料。
」都不是我那銀行的工作。」
「反正協和和積水潭的號我是很會搶的。」
「嗯,」我看着盤子裏的蛋糕說,「顯然以後這技能,肯定還要不少用上呢。」
這面前的蛋糕,與其說是慶祝我們出生長大,還不如說慶祝我們一步步成為了專業陪診項目經理人。不但會在凌晨時分醫院刷新系統的時候快速搶號,還會在小紅書看各類疾病案例分析,把自己的工作迅速調整為陪診狀態(我們戲稱這是work from bedside),甚至知道,病房的那張摺疊床,穿什麼樣的衣服躺下最舒服。
「的確好像也沒人告訴我們這些奧。」我撥弄着紙盤子裏的蛋糕說。
「那還能都告訴你?那可怎麼活啊。」melody說。
「是哦。」這話說的對,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回復。
今年我給自己的生日禮物是一個紋身,紋身的針在我皮膚上碰撞發生滋滋的聲音,聽得人可怕。文完了,發現竟然也是我媽媽的名字中的兩個字。
從紋身店出來,五月末的上海已經是夏天了,我因為忍着疼痛低血糖的厲害,跑到一家奶茶店點了杯飲料。剛坐下,收到家族群里的微信,媽媽再次住院。她四個月前長了皰疹的那一側大腦,有了血栓。
我打開手機開始看改簽的高鐵票,melody對我說沒事,我說嗯沒事。
她拍拍我。「真的沒事。」
我去她的衣櫃照她列的單子收拾住院所需的東西,她的衣帽間裏環繞着她的味道。是就算過了20年,我依舊記得的,我小時候她陪我睡覺時頭髮上散發的味道。我緩緩坐在那間小屋子的地板上,把頭伸進她的外套里,企圖獲得一點兒時的安全感。
關於陪護的體驗,與嘆息生命脆弱和衰敗並列的,是對時間本身的全新感受。這裏有無盡的等待,等待是最磨人的事情。床位要等,電梯要等,查房要等,檢查要等,化驗結果要等。為了等待查房時跟負責醫生聊上兩句,我從8點開始等待,直到12點。
眼看我寶貴的上午就要在等待中度過,我又憤怒又焦慮的在走廊里踱步了整整四個小時。我向同病房的其他病人抱怨,他們點點頭,卻好像並理解。是啊,時間哪裏比得上身體的病痛更讓人焦慮敏感。
可是我卻在這折磨的四個小時裏暗下決心。既然時間寶貴,必定更加珍惜。珍惜每一次可以出去玩的時光。珍惜每一次可以出國,可以走遠,可以體驗更不一樣的事情的機會。
從邵逸夫到我家不用出地上出口。一條地鐵線允許我可以直接從醫院門診大樓直通小區車庫。聽說這幾天外面下暴雨。我卻什麼都聽不到。回家倒在床上聽不到任何電話。也不做夢,也無夢可做。
我不是個稱職的女兒,我抱怨,我焦慮,我變得非常有控制欲,我和還在病中的他們吵架。我無法考慮周全,我既幼稚又極端。我的能力太有限了。我根本搞不定這一切。
挺好的,我自嘲。
「現在你知道當家長多麻煩了。」
很難說是誰真的需要誰,我們作為一個家庭,我們彼此互相需要,但是又沒必要扛着「這裏沒有我不行」的擔子。我們彼此承擔,難道不就是為了讓對方輕鬆一點嗎?覺得自己最重要其實是一種不自量力,何嘗對其他成員的一種輕微的否定和不了解。
我去拿藥,每個取藥窗口上掛着一大塊無邊際的屏幕,我在一排大屏幕上找到她的名字。站在對應的窗口排隊。藥劑師跟我核對姓名,然後把所有的藥放在台子上。我打開帆布包把一盒盒的藥往包里放。足足五分鐘,她還沒放完,我的包要塞滿了。那是足足接近一個床頭櫃那麼多的藥盒子。她一邊往外拿我越來越緊張。在那漫長的一分鐘裏,媽媽在旁邊看着我,看着那小山一樣的藥盒。
這次之後,我媽媽需要終身服藥了。這句話從醫生嘴裏說出來,極其平靜普通。
道謝之後,她挽着我的手臂等電梯。
她說,「我沒想到這一天這麼快」。
我說「只是慢性病,控制好就沒有問題。」
她說,「那我就不自由了」。
我說「是啊,我知道,可是沒有關係」。
在那一瞬間我突然覺得好像被是什麼東西抓住了。卻又覺得感受到了一種像徒步很久之後終於脫下兩隻厚靴子那樣的輕鬆。
我爸爸從小叫我「獨根草」。我崇拜凱魯亞克和麥田裏的守望者,最好是可以隨時隨地拔腿就走。我是宇宙的女兒,世界的公民,我沒有身份,我不允許自己有標籤。
回國的這幾年,我常常覺得被困住,被時間,被工作,被這個女兒的身份。但奇怪的是,這種感受卻在漸漸消散。
我不得不被迫面對我一直不想面對的問題。反覆思索,究竟我是害怕被困住,還是更期待能力更大,可以保護家人的自由?
我像一隻氣球,緩緩地落在我家的院子裏。和南瓜,爬藤上的豆角,番茄,大蔥,茄子。還有剛剛降落的我。那隻一直懸空的腳,在某一天早上突然踩在了地上。我面對門口轉過身,發現其實身後並非束縛,而是新的曠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