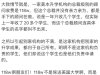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上海虹橋國際機場,我與王蓓送別獨生子翔鷹赴美留學。那是一個晴朗的早晨,我例外得到允許,越過海關,把兒子送進檢票口。在即將分別的一瞬間,我擁抱住他,他的眼圈紅了。
「爸爸,我真不想走……」
我沒有說什麼,也說不出什麼。鬆開手,把他推向候機室,推向陌生的大洋彼岸。他背着非常沉重的行囊和憂傷轉過身去,消失在台階上那扇玻璃門內。門內有許多人的身影,我分不清哪一個身影是我的兒子。送走兒子以後好幾天,我都沉浸在紛亂的思緒之中。我和妻從來都不想把兒子送走。早在八年前,海外的親友就建議我們讓他出國留學,我妻和兒子都不能接受。我們完全不能想像,這個最小的家庭會少了一個,而其中的任何一個都是必不可少的三分之一。
兒子在一九七八年考人上海交通大學,就讀於船舶動力專業。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在安徽黃山的山路上碰見他的一位同學,才得知我的兒子是交通大學小有名氣的校園詩人,着實使我吃了一驚。回到家讓他把詩稿拿給我看,才發現他已經默默寫了厚厚一沓了。後來他在《上海文學》雜誌上發表過兩篇小說。又在其他雜誌和報紙上發表過中篇小說、詩歌,從此,他反而對寫詩,寫小說更有興趣。交大畢業之後,在一個船舶研究所工作。白天忙科研,夜間卻總在寫小說。不知為什麼,他很像三十年代的讀書人,喜聽音樂,很少交際,不善言談,安於淡泊寧靜,在少女面前不知所措。我很不贊成他也以文學為業,理由倒不是因為我這輛前車經常傾覆,而是覺得他更應務實,身有一技之長,文學只能作為業餘愛好。為此,他可能會永遠耿耿於懷又從未形之於色。他在研究所工作了五年,在經濟浪潮的衝擊下,他和他的同仁們更多的時間是到工廠去搞點賺小錢的諮詢工作,學而不能盡用的苦悶使他重又萌生出國深造的念頭。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我在改編白先勇小說《謫仙記》為電影劇本期間,由於過度疲勞,暈倒在地休克過幾分鐘之後,兒子又動搖了出國的念頭。他非常傷感地提出,放棄出國機會,留下來與進入遲暮之年的父母相依為命。但辦完一切必要的出國手續,買好機票,全家已經筋疲力盡了。這個時候再打退堂鼓,顯然為時已晚。他只好忍痛離家去國。
一九五九年歲末,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在上海郊區一家軍工廠勞動改造。我的鉗工組長——一個抗戰時期八路軍的老修械工張師傅通知我:「你家裏(指我妻子)生了,是個兒子,來了電話。准你一天假,回去吧!」於是我騎上自行車,飛似的從二十餘公里以外的北郊趕回市區。不是探視時間,只能站在婦嬰保健院的樓下,7和樓上的妻子交談了幾句簡短的對話:
「兒子……在哪兒……?」
「在嬰兒室,現在看不到……」
「你還好啊?……」
她苦笑笑點點頭。
一個星期之後,我去接他們母子回來的時候才看到兒子。我抱着他不知所措,總怕傷了他過於柔軟的小身體。妻因病缺奶,我去買了一個奶瓶開始餵兒子牛奶,用針在奶嘴上扎了幾個孔便放進兒子的小嘴裏。他吸了很久,一面吸一面哭,哭得滿臉滿身發紅,我和妻急得團團轉,心疼得眼圈都濕了。問過鄰居才知道,扎奶嘴要用燒紅的針才行,只有烙過的孔才能吸得出奶水。於是趕緊如法烙孔,直到深夜,兒子才吮吸到奶水,止住哭聲。晚上,我把他摟在懷裏,很怕壓了他,徹夜不敢熟睡。
兒子在歡快地成長着,他哪裏知道我們這個家庭和別人的家庭並不一樣呢?三歲時他就迷戀古典音樂,那麼一丁點小,就能靜靜地坐在我懷裏一次聽完一部至兩部交響音樂。六歲時就經常要我帶他去外灘,拿着鉛筆和速寫本在眾人圍觀下速寫各種船舶,還根據汽笛的不同聲音,分別把每一艘船稱為:小鴨、小狗、老虎等等。
他媽媽經常忙於拍片而不在家,他的童年時代大部分時間和我相處。他非常喜歡郊野草地,一看見綠茵茵的草地就大叫着在草地上翻滾。跟我上街從不索要吃食,卻總要買玩具。有一次,因為沒給他買一支連擊衝鋒鎗,他突然在我臉上打了一巴掌,氣得我把他扔在沙發上,不再理他,三分鐘以後他就省悟到自己的錯誤,哭叫着撲到我的懷裏,很久都不放開我。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對我使過性子。在他四歲時的一個傍晚,我去幼兒園接他,把他放在自行車的大樑上帶着他騎行,被警察發現,要我到派出所去受「教育」,兒子難過地問我:
「怎麼辦呢?爸爸……」
回答他的卻不是我,而是警察。這位警察也承受不了一個孩子的恐懼目光和顫抖的聲音。
「算了,回去吧!下次可不許這樣!」
突然被獲釋的感覺使得他緊緊摟着我的脖子……
兒子小時候最害怕的聲音是那個穿街過巷的箍桶匠的呼喊,他總是在走到你身邊的時候突然大喊:「箍桶啊!」兒子不明白他喊的是什麼,出人不意而具有神秘的威脅,每當他不願午睡時,我總是抱着他說:「睡吧!箍桶的來了!」他只好緊緊地抱住我,閉上眼睛漸漸睡去。
他曾經是一個口齒伶俐能說會道的孩子。一九六三年春節,我帶他去廣州看他正在廣州拍電影的媽媽。在火車上,當我從洗手間回到座位時,全車廂的旅客都朝我鬨笑起來,他們告訴我:
「你兒子泄露了你們的家庭秘密。」
他卻得意地對我說:
「爸爸,我只不過告訴他們,電影裏,走鋼絲的金姑娘就是我的媽媽。」他說的金姑娘就是當時正在放映的電影《飛刀華》裏的女主角。
一九六三年,雖然早已摘掉右派帽子,但我在上海的處境仍很艱難。當時的上海市委主要領導人柯慶施、張春橋等把我當做政治賤民,不許我寫作,只許我下鄉勞動,我被下放到浙江紹興一個公社裏去種水稻。一九六四年夏天,途經杭州遇到當時的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他答應讓我重返軍隊。我雖然不忍離別妻兒,但穿上軍裝可以減輕社會歧視的現實,使得我不得不離家遠行了。終於在那年冬天去了武漢,再次入伍。我在十六鋪碼頭登上江輪,兒子在岸邊他媽媽懷抱里,出神地欣賞着大輪船航行前的壯觀場景。汽笛鳴響了,即將起錨……船上岸邊的人揮手道別,突然,我聽到兒子大聲哭喊起來,他在送行者的人叢中十分引人注目,因為他頭上戴着一頂小紅帽。他的哭聲非常傷心,使得船員們把即將抽去的跳板又搭了上去,搬運工們用手把兒子接過來傳到我手上,我抱住他,他緊緊抱住我,不再哭了。汽笛在鳴響,我噙着淚水對他說:
「你跟我走了,媽媽一個人在家不是更傷心嗎?」
他立即把臉轉向岸上眼含淚水的媽媽,又撲向傳他上船的搬運工人,要他們把他傳回媽媽的懷抱里……
當輪船轉身駛去的時候,兒子又大聲號哭起來……那頂小紅帽很快就模糊了,而他的哭聲卻在我的耳邊縈繞了許多時日……
之後,每當我回家探親的日子,他就高興地喊起來:「爸爸回來嘍,好開心啊!」我問他為什麼開心?他想了想,說:「爸爸回來,有好小菜吃!」——這當然是事實的一部分。但他想要說卻說不清的,是他對我的依戀。有一次他跟媽媽在一起看法國影片《白鬃野馬》,他看到許多人都降服不了那匹雪白的野馬時,突然大聲說:「要是我爸爸在這兒就好了!」他心目中的我,是一個無所不能的大智大勇者。而那時,我的實際社會地位,又是多麼卑微,多麼的無能、無奈。一個天真爛漫的幼童萬難理解。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我這個雖已摘帽多年的右派分子,理所當然地在武漢又被囚禁。秋天住院動手術,我才有機會偷偷地在夜晚溜出病房,給上海家中打了一個電話。接電話的是兒子(他媽媽也已失去了自由),兒子尚未意識到已經來臨的災難有多麼深重,一聽到我的聲音,就高興地向我講述了上海的各種情況。我問他上學了沒有,他告訴我:「老師都在鬧革命,我們不上學了!」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他如此流利、如此喜悅的聲音了。
離別了七年之後,一九七二年他隨媽媽到武漢來探望我的時候,人長高了,語言卻很短,像是已經枯竭了的溪水。
這段歲月,隔着一座黑沉沉的大山,我的兒子在山那邊難道誤飲了啞泉的水?妻告訴我一些有關兒子的事情之後,我才找到答案。
文革第一年的歲末,造反派就抄了我們的家,抄走了我們的全部藏書、藏畫和兒子的童話書,砸爛了他心愛的玩具,坦克、衝鋒鎗等……同時,還押走了他的媽媽。在被破壞得凌亂不堪的屋子裏,兒子坐在地板上蹬着小腿大聲哭喊着:「還我的玩具,還我的媽媽!還我的書……還我的媽媽……」直到哭啞了嗓子……
文革的第二年,他在學校要求參加紅小兵。使他難以理解的是,一再不被批准。老師回答說:「你沒有資格!」那時小朋友們也學會了歧視「異類」。在家是父母唯一的寶貝兒子,怎麼能承受得住冷酷的歧視和敵視呢?回到家中,坐在小院的台階上掩面嚎哭起來。他痛苦地問媽媽:「我樣樣都不比別人差,為什麼不讓我參加紅小兵?!為什麼?媽媽,你告訴我!為什麼呀!……」
妻沒法回答這樣的問題,即使能回答,天真幼小的兒子也聽不懂。他們只有相向哭泣。
從此,兒子漸漸失去了語言和歡樂。媽媽被送到郊區幹校去勞動改造,爸爸被關在外省的「牛棚」里,他只能和年邁的、愁腸百結的外婆在一起艱難度日。需要說的話只是:「婆,我餓!」「我冷,婆!」厄運對於幼小的身心來說,太沉重,太突然了!後來的日子就是盼,盼回了媽媽,再盼爸爸。每天中午和傍晚都要跑到弄堂口等郵遞員,或許有一天會有爸爸寫來的、經過檢查以後寄回家的短訊,內容千篇一律,都是:「我還活着,你們要保重!」但這也是天大的喜訊啊!
夜裏,兒子和婆婆、媽媽都患了失眠症。婆婆在黑暗中說:「鷹兒,報個時辰。」兒子早就熟悉了所有的時辰,隨口報了一個。婆婆捏指一算,念念有詞地說:「速喜、速喜,就在門裏!你爸爸的信就快到了,睡吧!啊!」兒子這才翻身睡去,接着做一個會見爸爸的夢。第二天一早就悄悄告訴婆婆和媽媽:「我夢見爸爸了,他還摸摸我的頭……」
這種日子過了整整六個年頭。六年,有多少個日日夜夜呢?
每個學期終了,妻都要被兒子的班主任叫到學校接受訓斥:「你兒子成天不說話,思想很陰暗,心懷階級仇恨!這難道不是你們家長的影響嗎?!」妻最忍受不了對她善良忠厚兒子的曲解,但她只能把由於憤懣而湧上的淚水強忍下去,無言以對。
一九七二年,妻和兒子才被准許第一次到武漢來探望我。那時我正在東湖邊的一個農場裏勞動改造。我被允許去碼頭上接他們。當我看見妻帶着一個瘦高個兒的少年向我走來時,我完全認不出他就是那個經常騎在我的脖子上,抱住我的頭喋喋不休,不知怎麼表達他的愛才好的兒子。沉重的行李壓歪了他的肩膀,他苦澀地笑笑,啞聲叫了一聲:「爸爸!」
第一個夜晚,一家三口團聚在我那間狗窩似的小屋裏,兒子興奮得不能人睡,快活得情不自禁地用雙腳蹬着被子叫着:「開心死了!開心死了!」白天他經常到豬舍里來,默默地看着我清理豬圈,煮飼料,分飼料,給病豬打針,為母豬接生。我怕直視他的目光,他的目光里充滿疑問、同情和憂傷,卻沒有一絲抱怨。那時候,這樣的家庭,這樣的負「罪」的父親太多了!
「四人幫」垮台的頭兩年,我忙於創作和爭取話劇《曙光》的上演,奔走於京、瀘、漢三地,從來沒有問過兒子的學業,他居然默默地在一九七八年考取了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學,按照他童年的夢想,進入船舶動力系。他第一次看榜回來我都不敢相信,又讓他再去看了一次,我才確信他是考取了。同時我感到非常內疚,哪有這樣的父親?對於生長於亂世的兒子的學業不聞不問,兒子竟不讓父母操心,順利升入大學!當然,功夫不負有心人。妻告訴我:兒子從來不要別人督促,為了學業,寒冬暑熱,沒有一夜不是在深夜才熄燈人睡的。大學畢業之後,走上了工作崗位,依然如此。
數十年來,我們的家庭由於我的緣故屢遭不幸,兒子的心中餘悸很深。一九八四年他曾在一封信里勸我說:「爸爸!您不能改變一個方式生活嗎?為什麼那樣重視文學的使命呢?從您的少年時代起,您為這塊土地已經付出了您應該付出的一切。」我覆信給他:「兒子,我不能,因為文學是我的生命。我越來越理解古人說的『文章千古事』那句話。一個有生命的人怎麼能不重視自己生命的意義呢!兒子,雖然從你出生那時起就因我而受累,就飽嘗孤獨無依和驚恐的滋味,我很抱歉!兒子,我在參加了戰爭,經歷了長期坎坷之後,仍然選擇了這條時斷時續的艱難道路,選擇了這個伴隨着我的也是你的辛酸、快慰和幸福的事業。如果為了安度晚年,我當然可以放棄這項工作和從事這項神聖工作的嚴肅態度,我們也許會有一個像別人一樣安寧和舒適的家。但我不能,原諒我;兒子!你曾經多次原諒過爸爸,因為我的選擇似乎和頑固不化、執迷不悟沒有關係,而是對生活執著的愛。看得出,你對爸爸還是理解的,但你的理解不可能很深,因為你沒有經歷過我所經歷的時間和空間。兒子,我不能用生命的意義這樣昂貴的代價,去換取寧靜和舒適的生活……原諒我,兒子!……」他無法和我完全共識,因為他沒有看到他的爸爸看到過的一切:他的祖父被日本憲兵活埋;他的父親兒時為了求生而失學;中原大地屍橫遍野;飢餓的人們骨瘦如柴,野狗卻個個肥壯。中國人世世代代為渴望光明在瀕死之際都睜着天真、輕信的眼睛……兒子遠在美國,每逢國內有了任何一點風吹草動,就要打電話回來,一定要聽到我的聲音,聽到了,他才安心……
為了他去美國留學,我們一家三口都痛苦地踟躕了很久。每當我看見美國駐滬領事館門前等待簽證的長龍,就有一種說不清的惆悵。在中國的唐代,前來中國求學求知的人數是當時的世界第一。今天,卻恰恰相反,中國人出國如潮。歷史和現在都是嚴峻生活的真實。四十年代中葉,他的父親就曾在出國留學和為一個新中國而在自己的土地上犧牲奮鬥之間進行過選擇,我選擇了後者。
一九八八年夏,我應邀去美國參加「艾奧瓦國際寫作計劃」的活動,兒子從明尼亞波利斯來看我。那時,他已經在美國度過了最艱苦的一年。明尼亞波利斯是個讀書的好地方,但找工作卻很困難。兒子去美國的頭兩個月,四處碰壁,找不到打工的地方。有一個時期,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正在這時,一家華人餐館的老闆通知他去試工。同時去餐館的還有一位中國內地留學生,他比兒子早去美國一年,是由另一城市轉到明城來讀書的。異國逢夥伴,相依相隨求生存。一周後,老闆才宣佈,他只能在兩人中留用一人。出人意料的是,他沒有選中在美打工已有一年經驗的另一位,卻留用了不善於勞動,只會埋頭苦幹的兒子。找到工作應是一件大喜事,而兒子卻陷入深深的苦惱和不安之中。他在家信中寫道:「雖然找到了工作,卻一點也不高興。我和他走出餐館,心裏很難過,不知說什麼才能寬慰他。我想,要是我不到美國來,這份工作肯定是他的。可明天,他到什麼地方才能找到工作呢?……」看完信,妻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在競爭、搏鬥中才能生存的異國,兒子的善良,兒子內心深處具有的愛心,使她感到驕傲和欣慰。
兒子有了工作,生活更艱苦。不停地勞作,什麼苦活都得干。明城寒冷的氣候要佔半年的時間,冬季的深夜打工歸去,在大雪冰封的路上,踏着深深的積雪,一步一個坑,步行一小時才能走回住處。打工、學習,學習、打工,對於一個父母寶貝的獨生子來說,太不容易了!他以一種甘於寂寞和頑強的韌性,闖過了種種難關。學會了語言和許多勞動技能,得以自食其力。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明尼蘇達大學邀請我去演講,他的同學們這時不知道他就是我的兒子。他並不是羞於讓別人知道他有一個這樣的父親,而是因為他從來都只願意做一個不引人注目的人。一位教授直率地對我說:「你兒子的性格和美國很不協調。在美國,人們不可能慢慢地去認識你,就像中國諺語說的那樣: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而是要你自己去爭取讓別人賞識你。」後來的發展卻是中國式的,兩年之後,兒子以他勤奮的學習和優異的成績,終於被他的導師賞識,並給予最大的信賴。
但他年年、月月、時時都想回國,我太了解他了!他的心靈仍然和兒時一樣,眷戀着他那個只放得下一張小桌和一張小床的房間;夜裏,他可以在燈下伴着交響音樂寫詩,寫小說,不時走到父母的房門外,聽聽爸爸媽媽均勻的呼吸。雖然我和他從未正式地討論過什麼,甚至很少交談,但我們之間的愛和理解是不言而喻的。他還眷戀上海的大街小巷,中國的大地、河流、海洋,中國式的擁擠,中國式的喧譁,上海的方言……連那些不禮貌的粗野的吵鬧和謾罵也都是親切的。因為,一切都在他遙遠的回憶之中,蒙着一層霧似的、溫馨的鄉愁……
我的兒子!我親愛的兒子和我是多麼的不相同,又是多麼的相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