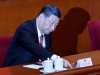前面已說過,新亞推薦我來哈佛,是為了參加哈佛燕京社訪問學人的計劃,為期不超過兩年,所以我最初根本不曾有過攻讀學位的念頭。然而一年之後,即從一九五六年秋季起,我竟從訪問計劃轉為正式研究生,攻讀中國古代史博士學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讓我對此先作一交代。
大約在一九五〇年,美國成立了一個半官方半民間的組織,名之曰"中國流亡知識人援助會",其功能在通過種種方式幫助從大陸逃出的知識界人士重獲安定的生活,包括移民至其他國家在內。我父親很早便向援助會登記,申請移居美國,但因久無回應,已將這件事淡忘了。然而事有湊巧,我到美國不久,父親竟收到援助會通知,申請已獲通過;唯一的條件是必須得到在美親友或機構的書面保證,在生活困難時願意提供經濟支持。由於這一非常意外的變化,父親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要在一、兩年之內回香港,剛好和全家來美錯開了,因為他很需要我的助力。所以他寫快信給我,讓我向哈佛探詢,是否可以轉入博士研究計劃,以延長留美期限,他並且告訴我:他已取得賓四師的首肯。當時我一方面為父親高興,另一方面卻又感到難以向哈佛燕京學社啟齒。一載考慮之後,我決定先向楊聯陞教授請示,看看他對這件事的態度。出乎意料之外,楊先生對我讀博士學位相當熱心。他告訴我:最初在訪問學人的審查會上,大家對我唯一遲疑的地方是年齡太輕——訪問學人一般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間,我當時才二十五歲。因此他鼓勵我向哈燕社社長葉理綏直接提出轉換研究計劃的請求。不但如此,他還教我怎樣陳辭,以獲得葉氏的同情。我依照他的指示,果然很快便得了哈燕社的同意。事實上,主要關鍵是楊先生有意收我為他的博士生,否則絕不可能如此順利。不過我當時對於哈佛大學研究院的運作程序茫無所知,直到多年後我在哈佛任教才理解到這一點。
從訪問學人一變而成博士研究生,這是我個人生命史上一個最大的轉折點。很顯然地,如果我訪問兩年後即回新亞,則此下教學和研究必將走上另一條道路。當時錢先生由於尊重我全家重聚的情感,慨然允許我改修學位,但是他內心則仍然盼望我先返新亞。他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給我的信上說得非常坦率:弟儻能早返,得失之間,亦殊難計量。國內治文史者,日乏其人,必俟有後起英秀,任此重負。學位僅屬虛名,弟若早歸,幸穆尚未衰頹,相與講究切磋,積數年之講貫,甚望弟能建樹宏模,不負平昔之所期。在美固可益研新知,然舊籍邃深,亦甚須潛心,時過而學,則事倍功半。至於他年重出國,機緣決不乏,故弟之繼續在國外深造,或先歸益治舊籍,再過數年,重再遠遊,此事得失,各居其半。盡可安心乘運,不必多所計慮也。(《素書樓余瀋》,全集本,頁四〇三~四〇四)錢先生在這封信中明白表示:他願意在精力未衰之前,將畢生治學心得傳授給我。這是他以前從未說過的話,當時讀後我內心甚為激動。親承錢先生的衣缽可以說是人生最難得的際遇,豈能和在美讀學位相提並論?必須指出:這不僅關繋繫着治學途徑的抉擇,而且更涉及我們師生之間的感情。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錢先生給我父親的一封信上,特別對這一點作了十分動人的描述。他說:只望明年遠遊歸來,學校事能乘此擺開,多得清閒,有英時等數人時時過從,談論學術,放情山水,弟當自買一車由內人駕駛,家中時時備一兩味家常菜,邀英時等三數人聚餐會游,弟之理想專在此處。……若使英時能在弟身旁親眼看其一日千里之脫轡絕馳,弟之心情蓋無愉快過於此者。(同上,頁二〇六~二〇七)這是錢先生一九六〇年一月到耶魯大學訪問前所寫的信,所以有"明年遠遊"的話。三年前他要我"早歸","相與講究切磋",這一想法此時竟以純感性的語言表達了出來。可惜由於全家來美的關係,我終於不得不改讀學位,並且畢業後也不得不先在美國執教,直到一九七三年我才告假回到新亞,履行了當年承諾的義務,但那時錢先生卻已定居在台北了。無論如何,失去向晚年的錢先生從事系統問學的機緣,這是我生平最大一憾事。
現在讓我對讀學位的曲折過程作一簡要追憶。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正式成為哈佛曆史學系的博士研究生。根據那時系中規定,博士生必須選修四門專科:一門主修科和三門副修科。我的主科是追隨楊先生研究中國古史(集中在漢、唐之間),這是早已決定了的。副科三門之屮,我首先選了中國近代史,由費正清和史華慈兩人合授。就我當時聞見所及,西方學者研究這一領域大體以西方檔案和記載為主要史料,如費正清的名著《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這一取徑恰好可以糾正中國學者的研究偏向。我覺得不應放過這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大好機會。另外兩門副科我在原則上已決定選取歐洲史方面。這不僅是我的興趣所在,而且也考慮到將來回到新亞的教學要求,不過當時心中除了"文藝復興"一科之外,另一科則在猶豫之中。好在選科的確定為時尚早,我仍可從容思考。
我第一學年選修的課程充分反映了我當時的心態。賽門的"羅馬史"
首先我選修了一門羅馬史。這是因為基爾莫本年休假,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這一段歷史沒有任何課程可選。哈佛本來也沒有羅馬史的專任教授,恰巧英國牛津大學的賽門(Ronald Syme)來哈佛任訪問教授一年,開了這門課。我當時對西方史學界所知有限,根本未聞其名,但在歷史系的選課聚會上,費正清教授特別向我推薦,說他是當代羅馬史大家,機會難得。我考慮到羅馬適可與漢代中國互相對照,以凸顯東兩大統一帝國之異同所在,當下便接受了費正清的提議。後來我讀他的名著《羅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1939)及其他論文再加上聽了一學期的講授,對他的淵博和深思都有了比較親切的認識,不愧為一代史學大師。三十多年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布朗(Peter Brown)教授偶有交流的機會。我有一次問他在牛津時曾否從學於賽門?他很興奮地說:他聽過賽氏講課,得到了很大的啟發,雖然他的專業導師另有其人。(按:其人即Arnaldo Momigliano)也是同領域的大師。布朗是當今最受尊重的羅馬史家,開闢了所謂"古代晚期"的研究園地。他獲得的學術榮譽無數,包括二〇〇八年的"克魯格獎"。後來我寫《漢代貿易與擴張》,涉及中國與羅馬的交通,頗得力於賽氏此課,但這是意外的幸運,非始料所及。懷特的"歷史哲學"
其次,我選了哲學繫懷特教授的歷史哲學,前面已提到,在上一年十月哈佛燕京學社的宴會上,我已開始對他的歷史哲學感到極大的興趣,現在既取得研究生的身份,便決定正式選修此課"史學的性質與功能"。
事實上,這是懷特經過多年醞釀而開出的新課,選課的學生(包括高年級大學生和研究生)多來自歷史系,哲學系學生反而是少數。從上世紀五十年初開始,懷特和英國哲學家(俄裔)艾薩克·柏林(Isaiah Berlin)志同道合,一直在計劃合寫一部關於歷史哲學的書;這一點在兩人通信中表現得十分清楚。我們必須記住,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英、美分析哲學(包括語言哲學)的壯盛時代,從分析與語言角度討論史學的性質問題也乘勢興起,柏林和懷特都是這一新潮的先驅者。一九五三年柏林關於"歷史必然性"的著名演講(後來以專書問世),即曾轟傳一時。懷特在這一領域的觀點與伯林大體相近,他也受到後者的啟發,所以合作寫書的動機很強。懷特在哈佛開這門新課便是為了完成這一願望。但稍後他發現:和柏林之間還存着一些基本分歧,不易調和,終於獨立出版了《歷史知識的基礎》(Foundations if Historical Knowledge,1965)那本富有原創性的專著。讀者欲知其詳,可以參看懷特的自傳《一個哲學家的故事》(A Philosopher's Story,1999)。
由於懷特自覺是在開闢一個新的人文園地,他在講堂上時時流露出一種推動新潮流的激情。這激情對不少聽講者發生了感染的力量,好像也在參預其事,我便是其中之一人。這大概相當於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所謂的"預流"。其影響所及,使我感到有必要對中西史學之間的異同作較深入的考察,以彰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特色所在。因此在懷特課上,我提出以章學誠與柯靈烏(R. G. Collingwood)史學思想的比較,作為期中論文的題旨。恰一九五三年倪德衛(David S. Nivison)完成了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章學誠的文史思想》(The Literary and Histrorical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eng)。懷特知有此英文論文可資參考,所以接受了我的提議。我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寫《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便是由這篇期中論文擴大與修訂而成。
懷特此課對我此後的學術取向影響相當大;七〇年代初我以章學誠與戴震為中心而展開的清代學術史研究,便是從這裏開端的。不僅此也,即以個人關係而言,我和懷特教授也頗為有緣。我一九八七年移講普林斯頓大學,發現他已在一九七〇年從哈佛轉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因此我有機會多次和他聚餐和談論。我們聚談常有普大漢學友人如裴德生、艾爾曼等參加,甚為歡暢。記得懷特有一次笑着對我們說:他完全不懂中文,卻想不到由於我聽過他的課,竟結交了許多漢學家朋友,而且對於中國文化和思想也越來越感興趣了。懷特先生生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卒於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以中國算法,他足足活了一百年。在現代美國哲學史上,他的成就無論就哲學的分析或實驗主義的推陳出新而言,都具有高度的突破性。他之所以實過於名,如羅特所感慨的,是由於受到哲學界的忽視。這是有欠公平的。
佛烈德里治的"古代政治思想史"
我選的第三門課是西方古代政治思想史,由政治學系名家佛烈德里治(Carl J. Friedrich)講授。佛氏原籍德國,對政治哲學和制度各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著作多不勝舉。當時他對極權體制和民主憲政之間的差異,分辨得最為到家,影響極大。我之所以選此課,主要是因為我在香港時期已開始探討民主與極權的分野,並寫了一些相關的文字。但那時我深感對西方政治思想史缺乏系統性的認識,因為沒有受過嚴格訓練,而新亞書院也未設政治學系。當時我遇到困難時,除了請先父指點之外,別無可以請教的人,現在竟有佛氏這樣的大名家,可以供我選擇,自然不肯放過天賜良機。佛氏此課包括講授、討論班、讀原始經典、寫期中論文等等,正合乎我培養基本功的需要。佛氏在每周一次的討論班中不但要求學生將他的講詞和經典文本結合起來討論,而且鼓勵外國學生將西方的政治觀念和他們自己本土的思想試作比較。(班上有印度、日本、中國、中東等地的留學生。)我便曾被他指定對中國儒家、道家略作介紹。此課對我當然是一種很有益的訓練,但我也同時感到自己的背景知識遠遠不足。我既不通希臘文和拉丁文,又在西方古史和經典常識等方面和美國研究生相差很多。所以從頭到尾,我都處於巨大壓力之下。不過我在此課中也得到一個有趣的經驗,至今不忘。佛氏要求學生寫一篇期中論文,以代替期中考試,但說明這只是擇一題旨陳述己見的報告,並非研究性論文,因此不必詳引經典文本並加腳註。我當時正在讀柏拉圖的《共和國》(Republic),發生了一個疑問:這一關於政治社會秩序的理想究竟是柏拉圖獨自創造出來的呢?還是前有所承,早已潛存在希臘傳統之中呢?我查了幾種有關《共和國》的流行論著,但都找不到清楚的解答。在思考過程中,我忽生一念,何不用中國考證學中探源溯流的方法在希臘相關經典文本中試加追尋一番呢?因此在《共和國》以外,我又遍檢了柏拉圖的《政治家》和《法律》以及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和《倫理學》;並且參考了修昔底德的史著《伯羅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戰爭》。最後我寫成了一篇五、六頁的短文,報告探索所得,發現《共和國》的構想確有源頭可尋。由於佛氏交代學生不必注釋,我在文中僅引述經典文本,未詳列篇章與頁數。想不到一星期之後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親筆短訊,要我將論文中所引經典文本註明篇章,供他參考。這實在出我意外,但我也很高興他居然肯定我的考證有可取之處,對於他這樣的專家尚不無參考價值。事隔六十年,我的記憶仍大致清楚,可見當時感受之深,可惜他的手書和我的原稿已在一再搬遷中遺失無蹤了。
費正清的"專題研究課"
上述三門課和我的學位計劃完全不相干。我的選擇大致基於兩重考慮:第一是當時決定讀完學位便回新亞任教,因此覺得應該把握住現有的機會,對西方歷史與文化的背景取得直接的認識,多多益善;第二是所選課程和我在香港幾年來研讀與寫作的領域比較接近,因此興趣相當濃厚。但是這三門課都是我在一九五六年秋季同時攻讀的。上面已提及,我的原有根基甚為薄弱,其中任何一門都讓我感到吃力,何況同時修二門?同時我又拘泥於歷史系所頒發的修課指南,說博士生每學期可選二門演講課,另加一門"專題研究課",寫出一篇具有原創性的論文。研討課我當然不敢涉及西方文史的領域,所以選了費正清教授有關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此課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生(約六至七人)共同研讀《籌辦夷務始末》屮若干特選的篇章,並儘量參考相關的西方文獻。但這一部分僅限於最初三至四星期,作為全課的預備階段;研究生則在此期間選定論文題目,開始進行個別的研究。第二部分接着第一階段而來,由研究生每周輪流報告研究所得,然後再經教授和其他同班者提出質詢和討論。這是我第一次進入西方的"中國研究"的行列,因此特別在此記下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