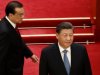命運是一個多麼悲涼的詞,在這個命運面前,我連一句大話也不敢說,都怕侮辱命運這個詞。
這個新聞不熱,即便熱了也會很快冷下去。
最近幾年,從呼格案到現在,在見慣了太多冤案錯案的我們面前,我們顯得對他人的命運有幾分麻木,並且這個案件該去吐槽誰呢?這個案件始終沒有槽點,他只是具體的幾個人的命運,與你我而言,它似乎始終都沒有任何關聯,冷下去肯定又會是必然了。
我想我對這個案件本身的感觸是會多於很多人的。因為這始終都涉及一個普通人被修改了的命運。
當一個離家26年的人,第一次回到家鄉。他看到的是他的兩個兒子,兩個兒子如此陌生,他完全不認識他們,兒子見他也很陌生。小兒子情緒突然很激動,衝着他撕心裂肺地喊:「這些年,你去哪了?」大兒子性格內斂一點,一個人坐在老屋的地上,撕心裂肺地哭。
作為一個被修改了命運的父親,他又該做什麼呢?也只能哭,哭得連一句對不起都說不出來。
對不起,他對不起誰呢?
誰又對不起他呢?
他的母親,80多歲了,身體像一枚彎曲的豆芽。早幾天,老母親就去買了大米,正值夏季多雨,米全生蟲了。母親把大米擺在水泥地面上曬,漆黑的蟲子四下散去,別人問他老母親:「你買這麼多大米幹什麼?」
她回答:「我等我兒子回來吃!」

張玉環兒子和張玉環母親
他的妻子,噢,不對,他的前妻。在他入獄幾年後,走投無路的她帶着兩個兒子嫁人了。他的妻子,噢,不對,他的前妻。在迎接他時,把辮子拆了又扎,扎了又拆,總覺得不好看。在即將見到他的那一刻,因為激動,卻暈倒了,兒子在旁邊扶着她,有人掐她人中,掐得很痛。她醒過來,說:
「張玉環,他還欠我一個抱,這個抱,我想了很多很多年,我非要他抱着我轉。」
她眼神里,全是「幸福」,是幸福嗎?我不知道,大概只有失去了的人才懂得幸福。
說完她笑着,看着天空,很害羞,有點不好意思,很難用美來形容她的眼神,那是語言難以言說的悲歡之後呈現出來的眼睛。沒有經歷時間折磨的人,沒有這樣的眼睛。
在張玉環被偷走的9778天裏,折合一共27年的時間裏。一切都是物是人非,當他回到家鄉,屋子已經徹底崩塌,荒廢了,無人住了,房頂漏了,只剩下牆,紅色的,地面全是雜草和青苔。
大哥老了,滿頭白髮,母親老了,老到只剩下等着兒子出獄這一個願望了。當年走的時候,大兒子4歲,小兒子3歲。他們關於父親的記憶是定格的,完全定格在父親被帶走的那一天。等他再回來的時候,孫子已經12歲了,而他對這一切完全是陌生的。
兒子說:「父親是一個陌生的詞,從小我學寫作文,只能按照奶奶的樣子來寫《我和父親》。」
前妻說:「孩子讀書,老被欺負,經常在學校被人說是殺人犯的孩子,孩子上了小學就不上了。」
如今他回來了,整個周圍的環境全籠罩着哭泣的味道。母親哭了,兩個兒子哭了,前妻哭了。
你很難講清楚這裏哭聲里,到底哭的是什麼?是哭訴多年的等待,還是哭訴被修改的命運?
只是兒子說:「父親還是父親,只是媽媽不再是父親的妻子。」
他的兒子命運被修改了,過早地就輟學了,跟隨着船隻在海上打漁。妻子的命運也被修改了,不得已在丈夫入獄6年後,為了撫養兩個年幼的孩子嫁了人。
妻子在腹中長瘤的時候問過他:「我可能快死了,你說你到底做沒做?」他說:「小女,我沒做,我真的沒做。」
然後是9778天的折磨,當年的「認罪」是行刑逼供,「他們打我,用棒子打我,放狼狗咬我」。
然後是1000多封寄出而石沉大海的申訴信。每一封都是一次等待,每一封都是一次次絕望的過程。然後是前妻多年的奔走,每一次奔走都是一次次在絕望的邊緣徘徊。
她說:「永遠不要嘲笑一個喝醉酒哭的人,你永遠不知道他經歷了什麼。」
這是一連串被修改了的命運,這是一個很悲慘境遇的家庭。但我依然從這個家庭里看到了善良,兩個孩子並沒有因為父親的誤判,走向人生的反面,妻子也沒有因為丈夫的誤判走向人生背面,他們依然堅信善良。
我毫不費力地也在這個女人身上看到了很多浪漫,忠貞、堅強、長情、有情有義、識體、顧全、孝順等等,這些很好的詞全部都可以用在她身上。
而如今那個被修改命運的男人回來了,他說:「我接受他們的道歉」,他們是指當年誤判的江西省高院。
不知道為什麼,自始至終,他身上背着的那塊紅花,我總覺得如此刺眼,不知道是誰給他戴上的,那紅花太大了,大的像領取國務院頒發全國勞模時的獎章。
這便是建國以來,關押最長的錯判案件,一共9778天,27年。每一天都是我們難以想像的黑夜無邊,白晝苦長。但很顯然,因為無法感同身受,也不可能感同身受,所以,我們並未太關注這件事。
有時候,我不知道日復一日,我為什麼還要寫下這些文字。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就像我一直也不知道樹葉為何會從樹枝上長出來,然後又似乎無緣無故地落下去。
每一個樹葉難道不應該有本屬於自己的命運嗎?它們的命運難道不是應該屬於每一個自己本該屬於的季節嗎?但多數時候,樹葉的命運,總是被風吹着、裹着、推搡着、欺辱着,也許你會讚美樹葉在風中無常的命運,總會呈現出某一刻生命的美妙。
但顯然人不是樹葉,這風的力,來自政府、來自他人、來自一個個錯誤。這風的每一個微小的錯誤,均可改變一個人,甚至幾個人的人生。
命運是一個多麼悲涼的詞,在這個命運面前,我連一句大話也不敢說,都怕侮辱命運這個詞。
所謂道歉,不過是一場錯誤之後的彌補。我打了你一巴掌,對不起,打錯了!我踢了你一腳,對不起,我踢錯了!我誤判了你,對不起,我誤判錯了!道歉是一個多麼輕佻的詞呀,歉道完了,可那些錯誤呢,那些打在他人命運里的疼痛感還在,並未消失,會跟着一個人一生的。
我從來都是對這個「道歉」都是表示懷疑的,我不懷疑道歉這種方式的可取性,因為除了道歉,賠錢,認錯,重新調查,施害者還能做什麼呢?但是我始終懷疑這道歉的淺薄,即便是一個鄭重的道歉,也完全不可能撫慰一個人一生的疼痛。不信,你去看看那些被刀子劃上的樹幹吧,即便你給這樹幹怎麼樣的心理修復,但那個傷口一直都在。
我甚至懷疑道歉變成了一個成熟的工業流程,尤其在現在的中國,你只要登錄微博,每一天都有各式各樣的道歉,但這道歉從未改變這個國家和民族的誠實。
「對不起,我們錯了。」像一個靚麗的風景線,像一個性感嘴唇說出的輕佻詞彙。意思是「哥哥,對不起了噢,我錯了,好不好啦!」
我也越來越厭倦一些詞,比如「沉冤昭雪」。
如果這個詞只是出現一次,它帶給人們的振奮或許是真實的,但當這個詞,屢次出現時,你總覺得這個詞很可惡,甚至消解了這個詞的原有意義。這個詞,本來應該在埋藏在字典的縫隙里,或者應該出現在文學作品裏。結果這個詞,常常出現在公眾視野里,你卻感到這個詞,有幾分甜膩。像書籍上討厭的腰封,像國民女王,像帶貨女王,平台一哥等等詞彙一樣,意義完全都被統統消解掉了。
沉冤昭雪,這本來應該是一個沉重的詞彙,應該每一個字都有上千斤的重量,很可惜,這些年,這個詞,輕佻地我不敢正視了。
不好意思啊,我越來越不認識這個詞了,就像夏天很少認識雪。
也許,你還看到了,這個故事裏沒有一個壞人,張玉環不是壞人,他選擇了包容那些修改自己命運的人。宋小女不是壞人,她長情、識體、顧全、堅毅,兩個兒子,也不是壞人,他們努力生活,接受並愛着父親,也愛着為自己付出的另一個父親,他們都是長情的人。
這個故事裏,沒有壞人,也沒有一個偉人,這個故事裏,只有一個個普通的人,默默承受命運,並反抗命運的人。
在這個故事裏,我還看到了一個女人,宋小女。我看所有關注這個案件的人都在讚美她。是讚美她什麼呢?讚美她絕望,讚美她申訴無門,讚美她勇敢善良,讚美她不拋棄、不放棄?
在她身上,我發現讚美也是一個可恥的詞,她應該本不需要讚美的,她要的只是生活。張玉環也是,他要的不是活着,只是生活。更可恥的是,我們還假裝感同身受,試圖在這個故事裏,找到都市青年男女,婚姻破碎男男女女的愛情啟示,說什麼「我又相信愛情了,人間還是很值得。」
去你的吧!我早已厭倦你們了。
悲劇的本身只是悲劇,你們輕易就把別人的命運看成了一部冗長,文筆極差的言情小說了。那些試圖在別人命運找到安慰自我的人們,你們常常都在不該感動的地方感動,也常在不該感動的時刻感動。
說實話,我挺厭惡你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