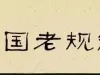恐懼是自由的昏厥。從心理學上講,陷入罪孽始終發生在昏厥狀態中……恐懼是控制個人的外部異力。人不能擺脫它的控制,因為害怕……
——(丹麥)克爾凱郭爾(S. Kierkegaard)
在我因1989年「六四大屠殺」被關押過的「劣跡」、而被中共當局用國家強權生硬地烙上永久的「危險分子」標籤30年後的今天,坐在柏林的家中第一次用作家的名分來強制回顧這段難耐的過往,其內心的掙扎與糾結,確乎有種恍如隔世之感。
在這裏我之所以強調「作家」的身份,並不單純是因為這次機會是對我的身心在監獄的那兩年零八個月的非人生活中失去了原本堅固正常的六顆牙齒、雙手關節也因長期戴手銬而落下腱鞘炎直到現在若犯病痛的連筆都拿不住的現狀的安慰和補償,而是由於從那個時刻開始,我的個體生命就被定義為人見人怕的「恐懼的帶菌體」!儘管我自己在1980年代初、年齡還不到20歲時寫的文章就獲過獎、同時在那個出本書極不容易的時期,還因為出版過書而被當時權威的《中國青年報》專題稱道。就是在出獄後,一直也沒有停止過寫作且作品也曾入圍國際上重要文學獎的提名。
但從出獄後我自己的名字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不能在中國大陸的媒體上出現,第一次出現還是把我名字中的「勍」字拆開為「京力」兩字方在媒體上面世的。而據我所知,1980年代中國著名的女作家戴晴在出版一部她自己翻譯的相關「二戰」的書時,不得不用了一個叫「尚蔚」的假名字。但中國的傳統士大夫們一直奉行的則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而就是在現在的中國,更為嚴重的則是:為數不少的中國作家至今名字還被當局像防瘟疫一樣完全屏閉着,而更要命的是一些因發表不同意見的獨立筆會的作家還被判重刑關在監獄裏。身為一位作家,是通過其作品和讀者的交流才換得身份認證和名分確定的,讀者的反響又是其繼續創作的動力和被認可的享受。一旦你在出版物上突然消失,從此和讀者再也毫無應對的可能,這種屈辱和絕望不能不說是一種殘酷的精神蹂躪和懲罰。
在意識形態壟斷的專制國家裏,作為一個作家,你只要對這個腐爛透頂的制度表示哪怕是應付式的順從,這個有着「養貓養狗養作家」傳統的腐敗機制,就會給你一個常人難以想見的物質享樂和精神饕餮——在前蘇聯時期,那些御用作家既有超過100萬盧布(那時盧布非常堅挺)的身價,又有花園別墅,時不時還有美貌演員相伴的豪華宴會;就是在全民奔小康的現在中國,據我所知一個黨所承認可的黨員女作家、中國作家協會現任主席鐵凝,她的一篇幾萬字的小說,生硬的把字排大,出成一本所謂的書,其稿費就是六萬多人民幣,然後再賣電視版權多少萬,而且平時什麼事也不干,還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專業作家工資、勞保和一套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分配一套大房子,有專職司機、秘書,享受部長級別的所有有無待遇。那麼他們這些所謂的作家對這個制度,除了感恩戴德還能說什麼?!
更何況中國大陸的中宣部、文化部對這些「自己人」的作品,也是局一國之力大力向國外推薦也是不遺餘力的——中共公開登報承認僅運作兒童作家曹文軒獲得國際著名的安徒生獎就花了400.2萬人民幣(見2016年04月07日《北京日報的題為「曹文軒,不是一個人在戰鬥」),無怪乎像余華、莫言等名流們一邊在大陸寫着小罵大幫忙的所謂「反腐」之類頌歌式的文章或電視劇本,一邊被提名去競逐諾貝爾文學獎,而其頭銜前面的一個重要的前綴詞「黨員」或「委員」什麼的往往都被西方社會忽視了,使得他們把大陸政協或人大什麼的官宴和西方的各種文化西式大餐都能通吃;更可氣的是那個余華,在意大利麵對媒體還奢談:中國的出版很自由,我的作品出版時就沒受到什麼審查(大意)!這就是西方主流社會追捧的名流,這也太令啼人笑皆非了。
我在寫這篇稿子的時候,對自己這次能否正常回國仍心存忐忑——因為眾所周知,像我一樣的獨立作家同仁,當局不但不許可他們出國參與文學活動,就是正常的出國旅遊也不被許可。而我個人在1999年底從俄羅斯回國時,在新疆海關也被扣押了10多天,其原由只有一個——就是奉勸我不要再回中國。
恐懼和謊言是一切極權專制國家維持其統治的合法性和連續性的最重要的手段,那些獨裁者們,利用手中掌控的幾乎是整個社會的資源優勢,不計成本地強行侵佔、蹂躪並威脅幾乎整個社會和公民的私人空間。而那些掌權者們,恰好就是利用公眾的普遍恐懼心理保障着他們既得的腐敗利益和維護着其源源不斷的腐敗利益源頭。而謊言則是其不斷篡改歷史和現實的最佳工具。也正是這種瀰漫在中國上空的恐怖和謊言,嚴重地污染和毒化着整個中國社會與各個不同的階層。故而,我將這種形態定義為「國家恐怖」。
也正是因為在「六四大屠殺」後的整整30年中,這種「國家恐怖」愈演愈烈,使得中國人的整體墮落達到了顛峰,而這種國家恐怖就像一個帶菌者一樣,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會無限蔓延,吞噬人們的生活細節、吞噬言論自由、吞噬人們的未來和精神成長、最終吞噬一切!
而這決非危言聳聽,下面請允許我用自己在獄內獄外30年感同身受且無孔不入的恐懼騷擾的個案,來作為一個解析現實中國政治生態的鮮活標本。儘管此前我一直不願公開承認這種國家恐怖不斷肢解着我的正常生活:夢魘般持續不斷的威脅、毫無私隱可言的個人私密生活、靈魂和肉體同時被恐怖追逐的棲無定所的狼狽與焦慮……
在中國宣判一個罪犯時,第一句往往是「捕前系……
而我被捕以前則是一個充滿無望之欲、卻在一所大學的作家班裏混着日子。胡耀邦去世引起風潮,平庸而慵懶的日子驟然間變得激越而飽滿了:站在不被官方承認的「民主論壇」上演講並在掌聲中飄飄然,當中共當局「4.26」在其《人民日報》上發佈充滿暴力恐嚇的社論後,我當時所在的大學保衛幹部的便衣人員們,晝伏夜出地撕毀校園裏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時,我公開貼出了自己寫的一張頗具黑色幽默的打狗隊告示。而也正是這段文字,成了當局的那些打手們最恨我、且在後來狠狠地整我的禍根。當然「西安4.22事件赴京請願團」的幕後黑手、指使做了個真棺材抬上大街遊行、書寫並廣泛散發一份」惡毒「的《告工人同胞書》和起草空校宣言煽動西安讓十多萬大學生提前離校」等,都是我「罪行」的分類,而我的刑事判決書的第一條則是「在動亂中出版非法刊物《民主與自由》並任主編,油印1000份,起草多份」告同學書「煽動學生罷課到底,反動氣焰囂張。」,這都是因言獲罪的標本。
在此期間最讓我感動則是,在「六四大屠殺」開槍後我決定逃亡時,發現自己已是身無分文,一位外語系的學生對我說:「周老師,這些錢是我募捐時偷偷藏下來的,我錯了,你帶着趕快逃吧」。
而能讓我一直對這個國家滿懷信心的則是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季節里。在我的逃亡路上,偶遇的一對幾乎一字不識的農民夫婦的一句令我終生不忘的「看你就像學生,先躲在我家,若公安來了,我就從前門放狗咬,你從後門往山上跑!」。在漫無目的逃亡路上,我怎麼也放心不下西安交通大學那個心愛的女孩兒,最後決定:回去看上她一眼,哪怕天塌地陷。
但我還是在她所在的大學門口被一群蹲守了快三個月的便衣警察們亂拳打倒了,當我再次抬頭看到的卻是滿眼不同制式、黑洞洞的槍口時,我才知道這不是在拍電影。
「狗日的這點倒像甫志高(中共紅色宣傳小說《紅岩》中的反面人物,未回家看妻子而被抓)多情的不得了,竟敢動手打警察,「六四」這伙反革命中還沒有過!把拇指拷給這小子砸上。」人與人渣僅一字之差。看見被打得滿臉是血的我,我當時的女友無助地高喊:「抓學生了,打學生了」,警察們的拇指銬銬的我大熱天冷汗如注,這些幾乎都是同齡的警察都是無動於衷。
「又沒犯啥罪,給!把這瓶啤酒喝了」,一個在旁邊開商店的個體戶倒是一點不怕,一邊將已啟開瓶蓋的啤酒瓶遞到我的嘴上,一邊冷冷的盯着二十多個凶神般的警察。
我所關押的「西安市公安局五處看守所」是中國所有監獄中都有名的「監獄博士後流動站」:我剛一進號子,就看見一排光禿禿的頭頂,全都帶着手銬和腳鐐的犯人,事後我才知道他們全都是等待處決的殺人犯,在此我陪伴過的死刑犯就有近30人之多而。這其中一個外號「鴿子」的嫌疑犯則是個「異性癖」的假女人,他因首次犯案後被放進了女監舍而在西安的黑道中聲名大振。也就是在這裏,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同性混亂雜處的醜陋。
「聽說寫稿子發表後能減刑,你教我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我讓你『撬豆包(同性肛交)』,受活得很」,晚上熄燈後「鴿子」直往我的被窩裏鑽。
「我要讓你們變成三改對象——老婆改嫁,兒子改姓,你狗日的改造」,綽號「王老虎」的看守所所長經常在監舍的廣播上如此吼着。
西安一所軍事大學因「六四大屠殺」被關押的男大學生,在放風時抓起一把自己剛拉下來的糞便就往自己嘴裏塞。因為他想通過裝瘋來見一面同被關在這所監獄裏的「同案」女友。自己的大便白白吃了,還要挨上一頓電警棒,女友自然不會讓他一見。最後倒是他不斷寫在「鬼票」(監獄裏特製的飯票,因用的人大都是死刑犯而得名)上的情書,奇蹟般地起到了與女友聯絡的作用。
「趙毅,等不到三個月後槍斃你了,現在咱倆就來個了斷,今天我打死你,再槍斃我;你要先打死我,就得提前槍斃你」。言罷,我手中的木板讓他頭上血花飛濺,這個總用他即將被槍斃來欺負被關押大學生的惡棍,被我打得頭破血流。我因此被戴上了「背銬」:把兩個手背在身後,再把兩個手腕死死的疊在一起,然後用生鐵鑄造的土銬子銬死。從此,我的吃喝拉撒,都得靠同號子關押的學生幫忙,晚上只能趴着睡覺。等到六天之後,卸下銬子我的雙手都從背後收不回來,老犯人幫我活血用偷偷藏下的縫衣針刺我的雙臂,我的雙臂毫無知覺,他幫我用滾燙的毛巾反覆敷了三天才漸漸的恢復了知覺。事後他幽幽地告訴我:生鐵鑄的土銬子吸血哩,再多銬一天,你的雙臂就廢了。
下面是一些持續一年裏和我在一個鍋里攪勺把的「活死人」們:
張啟祥:省軍區司令員家裏就是我搶的,在他家裏我一槍要了兩條命,他兒媳婦的命真硬,我捅了二十多刀還沒死,你們知道不知道?活人心肝炒着吃嫩得很。
蘆西言:我在公安局已當上副處長了,都是讓大煙害的,竟用配槍換大煙「冒了泡」(黑話:吸毒),誰知那支槍竟到了魏振海那個殺人魔王的手裏,一下子就染上了五條人命。
韓新建:打不了我的頭(槍斃),輪姦時我不是第一個和最後一個,聽說在輪姦案中的這兩個人都要槍斃,至於其他……
吳西貴:我這個死刑判得冤,偷了二十多輛摩托車,可自己長這麼大連幾塊錢一碗的羊肉泡饃都沒吃過,誰讓我媽我爸生下一窩窩的弟妹,他們自己又沒本事養活呢。
下面則是一個在常態社會裏生活的人們怎麼也想像不到一些監獄內的「私刑」——
「種牛豆」:夏天將號子裏的「砍頭子」(較老實的犯人)身上或胳膊刺破,再將跳蚤、臭蟲和虱子放進去,幾天後,「砍頭子」胳膊上就真正變成「艷若桃梨」了:一個西紅柿般大的透明的包,裏面成十上百的小生物在蠕動,其滋味真的是刮骨鑽髓。
大毬比賽:不足18平米的監舍,塞着40多名人犯,除「頭塊板」(牢頭獄霸)外全部犯人都脫得一絲不掛,然後每人都開始自己手淫,將生殖器弄大,「頭塊板」手拿毛筆,給生殖器最大的犯人肚子上打個勾,生殖器小的則劃上叉。
皮管王:用抽水的硬塑料管打人犯屁股,此刑據說是由收審所王管教「發明」。我就親眼目睹了同監舍的一個人犯因偷偷抽煙被發現後,王管掄圓皮管打了三十多管子,犯人的屁股腫得像兩枚透明的柿子。事後在他們號子裏不小心撞破了,血水四散,獄醫用了兩大磁缸子衛生棉球全都放進屁股後的血洞裏仍填不滿,後來此人因感染死亡。家屬到監獄看屍體前,收審所所長在監舍的廣播裏公然講道:某某是病死的,待會兒家屬來了,該怎麼看到的就怎麼說,誰要是不老實睜眼說瞎話,他就是娃樣子。
就是在這樣的一種環境裏,我在一百多個因「六四」事件關押的教師和學生中第一個當上了「頭塊板」,在我「掌權」期間,曾經歷了「失敗的獄中民主與物極必反的獄中暴政」——其實我也有令人吃驚惡的一面:打,往殘里打,鬥,往死里鬥,剋扣,讓你們餓得學虱子叫……
至此,我才明白——野獸關的時間長了,獸性就少了,變得溫順了。而人若關的久了,人性就少了,獸性就反而變多了。
1990年9月26日,作為陝西省因「六四」事件關押的所有人犯中最後一位,我被押送到陝西西部以盛產西鳳酒而聞名的鳳翔縣棗子河陝西省勞教所投入勞動教養。此前,該勞教所專門成立的「六四」事件勞教中隊已關押了一百多人。其中有教師、工程師、大學生、個體戶、工人、無業的所謂打砸搶分子、「六四」期間以學生名義非法募捐的青年農民,甚至於真正意義上的乞丐。
1990年11月初,我偶爾在監獄裏看「新聞聯播」上講要放方勵之先生去美國。接着連續幾天裏,從獄中僅能見到的一份官方報紙上,我看到的幾乎全都是中共當局為爭取延長美國的「最惠國待遇」而喋喋不休地重複着:「我們中國的監獄中已經沒有因『六四』事件關押的大學生了」云云。其不知,僅在我們這個監獄裏,當時還關押着幾十個學生和教師!
由於信息隔絕,我當時判斷國際社會似乎也相信了中共的謊言,因而就有了一種強烈地被愚弄感。加之在完全封閉的環境中產生了一種非理性的極端心理反彈:中國的知識分子太軟弱了,歷次政治運動中逆來順受,我要開一個先例——越獄成功後再偷越國境,做出個樣子來給他們看看。
人一旦陷入某種情緒之中,特別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之下,往往會在偏激的同時更加固執。於是我便開始尋找想越獄的同案犯。很快深得勞教所副所長劉某喜愛、幷且擔任中隊小組長的賀國安向我透露了他要越獄的理由:他自己是單位開車的工人,找了個女大學生做女朋友,雖然對方常來看他,但也怕天長日久女友變卦,想找人一塊越獄,然後帶着女朋友一起逃往國外。開始我並不置可否,後來見其言辭懇切,加之他擔任小組長,有利於同外役號接觸上,能方便搞來越獄用的鋼鋸條等,故答應與他合夥越獄。此間,艾東也同我接觸上了,他的越獄理由簡單易信:1990年他才被公安局從海南抓回來,一下子判了三年,往後的刑期太長,將來所有政治犯都刑滿釋放了,留下他自己一個人太難熬了。
在一次破綻百出的越獄計劃失敗後,我們立即又實施下一次越獄計劃:用賀安國通過外役號藏在香腸里的半截鋼鋸條,我趁人不注意的時候將監獄庫房的鋼窗上的鋼棍鋸斷兩根,然後又用稀泥在斷處糊上遮人耳目,接着我又把自己的被罩和床單拿到庫房,趁晚上和艾東一起悄悄撕成碎片,共同擰成一條8米多長的粗繩藏好,準備過幾天等到風高月黑之夜三人從鋸開的窗戶溜出,再搭人梯翻越監獄大牆,然後由先上牆的人放下事先準備好的繩子,其它兩人再順着繩子爬上牆越獄。當時定好某天晚上12點整越獄。
可不到當晚8點,我們監舍里衝進一大群氣勢洶洶的獄警,不用費勁就從庫房裏搜出了那條繩子,搬開了窗上鋸斷了的鋼棍,我立即被押到嚴管隊禁閉室關押。中隊裏一片混亂,由其「六四」相關人犯在監獄裏秘密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西北分部」的核心成員臨時應急開會作出兩條決定:一是馬上銷毀所有相關文字性的證據,二是若出事都往周勍頭上推。原因是我先關禁閉可能是我告的密,另外是保存組織,犧牲局外人士!
前一條尚系果斷(哪怕原因荒誕),而後一條既愚蠢,(因他們所有活動都背着我,有何密可告?)又缺乏人性與道德!繼我被關禁閉之後,劉從書(六四西安工人自治聯合會主席)、艾東等相關的20人被分別隔離在一棟空樓里,一時風聲鶴唳,那位「文革」中「三種人」出身的劉副所長更是得意洋洋,急不可耐地向陝西省以及中央有關當局報功;據說司法部非常重視,從北京派來辦案的項目大員曾說,此乃建國以來首次政治犯獄中組黨,是一條大魚。
當我單獨被關進禁閉室後,方有機會冷靜地從頭至尾細想整個過程,一旦冷靜下來立即明白這是一個圈套,是劉副所長為立功在發現劉從書他們經常偷偷聚會時為放長線釣大魚而佈下的一個陷阱。而我們三人的越獄行動,只不過是在他們認為必要逼從劉從書認罪時,給其造成心理落差的一個誘餌!等想明白這個道理後,在初冬陰冷的禁閉室里,我仍是冷汗淋漓!
平素我們忙碌、豪情萬丈,也常常野心勃勃。可又有幾個人能在忙碌中抽出些許時間想一想:今晩臨上床時脫下的鞋子,明天一早能否還穿得上雙腳?這裏就用我在這次監獄裏不足三平方米的禁閉室里的個例來左證:那是一個對「與世隔絶」一詞有着切膚痛感的「超現實」的空間——沒有聲音,沒有時間,甚至沒有光亮,自然也就沒了白天和黑夜。若不大聲對着逼仄的牆壁胡亂地說話,人就會失語、甚或發瘋,至今我獨自一人走在路上,常常還會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語,往往引得路人側目。
在禁閉室的無望和孤寂之中,偶爾透過狹窄的門縫擠進來的些許亮光,照射着濡濕的地面上一群螞蟻在聲勢喧天地搬動幾粒我無意間散落的大米的熱鬧場面,便成了我自娛自樂的大戲,這些過往在我眼裏可能微不足道的小生靈,卻在帶給我片刻消解的同時帶來了另一種視角和感嘅:這一件在我們人類看來微不足道的事兒,但在螞蟻們的眼中,其浩大、宏偉與我們人類已完成或正在進行的任何重大工程的浩大與艱辛都是一般無二的,而更要命的是我們人只要不經意間撒的一泡尿就能令其災難滅頂;再深想想若是一群螞蟻在籃球上爬行,其自豪感和難易程度與我們的登天工程也應該無異,可人只要輕輕地用腳一踢,螞蟻們頓時便會有「坐地日行八萬里」的感覺。人只要換一個視角就會明白自己的境遇,同時敬畏、謙卑和感恩之情便能生根。近而就會明了人是需要相互依偎與溫暖並去珍視這諸多情愫!
此處只能引用我在監獄裏的加刑材料第五條:「周在禁閉室里態度十分頑劣,拒不交待罪錯,在禁閉室里放聲高唱,大喊大叫,干擾審查(當時我若不這樣做的話,在這個與世隔絕的鬼地方非發瘋不可!只有在這個特殊的時段,我才真正理解了茨威格在其著名的《象棋的故事》中那些經典的描述。)更為惡毒的是,周在禁閉室唆使同案劉從書等建立攻守同盟,讓這三人一口咬定是勞教所領導為了立功教唆慫恿他們犯罪,其用心極為險惡」。
而給我加刑5個月的另一個「罪證」則是:周入獄後從不認罪伏法,經常利用作家的身份在不同場合散佈為「六四」辯解的觀點,更重要的是他還偷偷收集了一份本監獄在押的「兩亂」人員名單,讓提前釋放的學生佟某私下帶出監獄轉交海外的報紙,妄圖借反華勢力給中國政府施壓。
結局與後果:中隊其它沒有參加組黨而知識層次較低的「六四」同案人員大罵「什麼知識分子,乾脆改為吃屎分子,啥還沒有干呢就為了個破總書記爭得頭破血流。可剛一關起來,一個個比誰都推得乾淨,簡直跟賊一樣,偷的時候只嫌偷得少,判刑時只怕判得多!」。
「總書記」劉從書加刑六個月,副總書記付喻加刑2個月,同時參與越獄和組黨的艾東加刑3個月,而我這個「黨外人士」,關禁閉室的時間最長且禁閉期間只提審過一次的人卻被加了5個月刑!賀國安在此後被艾東等人用凳子砸得保外就醫了。事後,我心境極糟,在監獄裏就用刀片將自己的頭髮和眉毛全部刮光,使自己變成了一個光禿禿的怪物。
真可謂監獄小社會,社會大監獄。
我出了監獄後,經常會聽到:你這幾天不能出家門一步,因為克林頓來了。忍無可忍,我一時性起,也就以硬碰硬了:「既然克林頓影響了我的正常生活,我將以命相搏,你們再要跟蹤我,我就要用汽油燒克林頓或者當着他的面自焚」。正當我自以為挾制住對方時,一位因經濟問題被公安局開除公職的鄰居道破「天機」:其實你真傻,這幾天咱們大院門口停的車、無端多出來的那些修鞋的、賣菜的,和那些穿便衣晃來晃去的全是公安局政治保衛處的便衣。
而每每到了所謂的敏感時期,由多名警察「保鏢」着離家出遊則是家常便飯,期間的焦慮和憂憤常人難以想見。而面對「只要你今晚和我們在一起,你就是想嫖,我們都給你守着門」這些公安局專職監視我的人的此番話,你是恐懼還是無所謂?
最讓我驚訝的是在湖南張家界市的那一次:為了安靜,我出行前沒告訴過任何人,可就在我到了當地的第三天早上,就在大街上我「巧遇」了西安市一直管着我的兩個警察!須知這是一個加上旅遊的人口超過300多萬人的城市。他們告訴我:其實很簡單,讓一批批的當地公安拿上你的照片開車上街轉游,只要你一露面就會碰上。我們有的是人和車!
當1990年代中期,我把一份《歷史故事報》辦的發行量大增的時候,公安局專職監視我的那個人又講:「你辦的報紙,就是整版上都印上共產黨萬歲,我們頭也覺得你是在諷刺黨呢,要麼你自動退出,要麼我們就把這份報關閉了,你自己看着辦吧。」。
中國的成語講:窺一斑見全豹。那就讓我來做供大家了解中國的那頭「豹子」吧:2008年北京奧運會剛開的頭一天,英國BBC駐北京的記者給我家裏打電話約訪問,我放下電話還不到一分鐘,警察「朋友」就到了我的樓下,登門就說:我們是順道來看你的!
我隨機問道:我們這一片像我這樣的人就一個,你們不會太忙吧?
答曰:不是就管你一個人,西邊小區還有兩個精神病,他倆是「武瘋子」,也歸我們管。
我自己心裏明白這些不期而至的「朋友」,既能笑臉搪塞,也能隨時掏出手銬把我拷走,他們只是個工具,要命的是他們背後的那隻看不見的手,這正可怕的就是這種不確定性!
而在整個奧運和殘奧舉辦的快兩個月期間,我家門口三、四個胳膊上套着紅袖標的老頭、老太太每天都是十幾個小時的守候。儘管我每次出門買菜或着干其他事他們都用異樣的目光盯着我,可我仍從心理憐憫他們——那麼大的年紀,不管天熱或者下雨就守在哪裏,真不知道他們的上級是如何給他們編排我才是他們有了如此高的積極性。而幾年前我租住在北京另外一個小區時,警察為了讓小區的保安更認真的監視我,竟然哄騙那些小保安說我家裏藏有槍支,會威脅國家安全!過去三年裏在此等環境下我一年內竟搬了五、六次家。
所以當奧運期間,有一位瑞典記者問我奧運與中國人權現狀時,我就問他:你看看北京滿街道上胳膊上帶着沒有任何法律效應的紅袖標的青年或老年「自願者」們,隨意搜查行人包裹的現狀和文革的紅衛兵有什麼區別?可這種公然踐踏現行法律的行為,卻就是發生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北京街頭,發生在所有奧運參與者的面前!
或許當局會辯解:這是從保障奧運安全的良好願望出發,但我們必須要切記——把人類帶到地獄的原因永遠是對人間天堂的許諾和憧憬!這種全 警察察國家的現狀,只能說明中國法治的脆弱和可悲。
難怪奧運期間北京的手機短訊上流行這樣一則笑話:奧委會主席羅格對胡錦濤說,鑑於中國的熱情與周到,下屆奧運會仍在北京舉辦。消息傳出,全國官員昏厥,北京警察狂呼:老羅,我操你大爺,你還讓不讓人活?!
本應是一個常態的生活,而我自己卻總處在沒有明天的恐懼和動盪之中。這無處不在的顫慄和不安,更重要的是使我在漫長的30年中,給自己的親人、朋友都堆積起來了由於自己無法掌控而帶來的情感債務——使得他們因為與我的接觸、甚或認識而受到盤問、傳訊、甚或威脅。而這些罪孽從何而來?與罪孽相關聯的恐懼生活又是從何處來的?我們將如何面對?
我之所以寫出這些經歷,並非其他,只是偶然發現了一個駭人的規律:我這麼多年所經歷的磨難,幾乎每次都與「文字」相關聯!至此,我方明白——一個國家只要把文字和從事文字工作的人當成恐怖對象,其國家基礎必定是國家恐怖主義的胚胎。此點從希特拉的德國到斯大林的蘇聯,從毛澤東的紅色恐怖再到薩達姆,乃至今日的古巴、北韓和我的專制的祖國,都概莫能外。
我以為,在一個由國家機器控制着幾乎是整個社會生活全部的極權國家裏,軟化其僵硬的社會組織細胞、恢復並修復被恐懼與謊言這兩具專制的磨盤碾壓蹂躪的人的基本屬性,遠比以暴抗暴重要的多——還是以「六四大屠殺」為例,我多年來在不同場合一直有一個觀點就是:對在「六四事件」中共產黨的悍然開槍,我事先和事後都有一種預料、甚至這並不是我在這一過程中最仇恨的。因為稍稍有點歷史常識的人就會明白:開槍和噬血才是其常態——戰爭時期為一個山頭不惜多死幾千人,為了所謂的「衛星上天」,不怕餓死幾千萬人,那麼與「六四事件」的開槍相比,只是其血腥史中的小巫而已。
最讓我不能原諒的則是,通過這一過程,讓我如此清晰透徹的明白了共產黨幾十年的統治,把人只所以是人的基本屬性破壞殆盡!使人喪失了最起碼的組織能力和交流能力——試回想一下,在1989年4月15日到6月底的那「驚心動魄」的兩個多月中,中國人表現出的那種高度地道德自覺——在沒有警察維護社會秩序、社會的公共部門有意「癱瘓」的情況下,在一個人口如此龐大的國度里,竟然沒有發生一起人為的惡性治安案件!我自己就親眼看到了一張當時貼在西安市中心的鐘樓上的一張「小偷罷偷,聲援學生運動」的「罷偷宣言」。這足以看出中國民眾為了自由民主的實現不惜一切的付出與決絕。因為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民主基礎幾百年的美國落杉機,僅1980年代的一次球迷騷亂,就死了上百人。
而中國的悲哀恰恰在「六四事件」之後,那麼一場高度道德自律、幾乎是全民爭取民主的運動,在開槍後的一瞬間,立即演化為一場人人過關的審查運動!這種結果正是共產黨一直想要把人馴服成為「工具和螺絲釘」的成功所在!所以說:極權制度是文明社會的毒瘤和天敵,其對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和國際社會的正常秩序都有着及其大的威脅和影響。而改變這種現狀的方法,就是儘可能的建立公民自治組織與行業協會,使得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能有參與公共事務的可能與能力,進而和國際社會形成良性互動,這就是一場理性與恐懼的賽跑,只有前者在這一過程中佔了上風,我們就不會再恐懼了!
我深信: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所謂的公共空間,就是大家人人都有份的時空,而在這一空間中,良性與惡性的力量對比只能是此消彼長的竟爭態勢。而對一個作家而言,我堅信一切自由都源自表達自由。而真誠且自由的寫作是對極權專制下浮媚禁錮生存境遇的解構與重構,為了自由寫作與自由表達我們都應該屢敗屢戰!
而關於「六四事件」,我認為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寬恕必須是建立在自覺的懺悔和罪責明晰的前提之下,在這點上德國統一後處理柏林圍牆慘案的成熟經驗可資汲取。我們絕不能再用結束「文革」時那種粗暴的一勺燴式的「粉碎幾人幫」來了結「六四事件」,因為當年的當事者們若認真負責地清算了「文革」,「六四」慘案就不會發生,而其後的種種惡行也就不會肆虐!我們必須給我們的後代創造一個像二戰結束後的歐洲國家一樣的環境,讓他們也能心直氣坦地發出相同的質詢:爸爸當時你在哪裏?你又在幹什麼?!這方是我們這個民族避免再陷罪惡之淵的前提,同時也是「六四事件」所有死難者和參與者為我們這個種族未來的良性發展所提供的歷史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