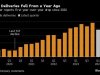《歐洲漫錄》的見識
在當時的中國,國民黨已經接受蘇俄的資助,因而開始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致力於完成蘇共領導人多年之前就為中國規定的革命任務——"反帝反封建"。與知識分子的個人言說相比,政黨的力量是巨大的,短短几年中,五四新文化就似乎已經過時,成為"落後的"或"反動的",一些學者與一代年輪人一樣,不知不覺中就學會了把政府稱為"北洋軍閥政府",學會了高喊"打倒封建勢力"、"打倒帝國主義"等新口號。與此同時,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也發生了新變:由向西方學習轉向蘇俄學習;由"西化"轉向"蘇化"。在這個背景上,蘇俄成了一些人想像中的聖地,紛紛前去學習取經。
蘇俄是如此誘人,徐志摩也決定前去看看。所以,他的歐洲之旅就有了游蘇的日程。《歐遊漫錄》記載的就是他對蘇俄的觀感。
走出國門,一路西行,穿越西伯利亞,徐志摩終於目睹了蘇俄。俄羅斯的風光真美!徐志摩一再從心底讚嘆,筆下也做了精彩的描寫。但俄羅斯人的生活真苦!革命之後的所謂新社會,讓徐志摩無法獻上他的讚美。他早已讀過許多關於蘇俄的描寫,但他一直懷疑,那也許正像蘇俄所說的,是帝國主義對蘇俄的惡意醜化,然而,眼前的事實,卻出乎他的意料:
"入境愈深,當地人民的苦況益發明顯。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襤褸的小孩子,從三四歲到五六歲,在站上問客人討錢,並且也不是客氣地討法,似乎他們的手伸了出來,決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連站上的飯館裏都有,無數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麼來的,全靠着我們吃飯處有木欄,斜着他們呆頓的不移動的眼注視着你蒸汽的熱湯或是你肘子邊長條的麵包。他們的樣子並不惡,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陰沉,看見他們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問這裏的人民知不知道什麼是自然的喜悅的笑容。"
在一個車站下車,天已經黑了,車站上照明的卻是幾隻貼在壁上的油燈。昏暗的候車室里是滿屋子黑黝黝的人群,"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氣味!悲憫心禁止我盡情的描寫;丹德假如到此地來過,他的地獄裏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終於到了莫斯科,這是徐志摩初到科里姆林宮時的感受:
這裏沒有光榮的古蹟,有的是血污的近跡;這裏沒有繁華的幻景,有的是斑駁的寺院;這裏沒有和暖的陽光,有的是泥濘的市街;這裏沒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怖和黑暗,慘酷,虛無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凍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世紀的漫遊中,莫斯科,是領路的南針,在未來文明變化的經程中,莫斯科是時代的象徵。古羅馬的牌坊是在殘闕的簡頁中,是在破碎的亂石間;未來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間,是在人類鮮艷的血肉間。莫斯科,集中你那偉大的破壞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種,一手拿着殺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後奴性的人類的子孫,多多的來,不斷的來,像他們現在去羅馬一樣,到這暗森森的雀山的邊沿,朝拜你的牌坊,紀念你的勞工,謳歌你的不朽!
俄羅斯悠久的文化已被摧毀,但徐志摩知道,自己到莫斯科"當然不是看舊文化來的"。那麼,莫斯科的新景觀如何呢?徐志摩首先看到的仍然是貧窮和蕭條:大街兩旁古老的店鋪大都倒閉,漂亮的店鋪是見不到的,最多也最熱鬧的是食品店,是政府開的,物資卻奇缺而且昂貴。俄羅斯人曾有的貴族氣徹底不見了,街上走過一群群男人,卻見不到一件白色的襯衣,更不用說禮服和鮮艷的領結。徐志摩寫道:"我碰着一位大學教授,他的襯衣大概就是他的寢衣,他的外套,像是一個癩毛黑狗皮統,大概就是他的被窩,頭髮是一團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經爬梳過的痕跡……"徐志摩還拜訪了另一位教授:"我打門進去的時候他躲在他的類似'行軍床'上看書或編講義,他見有客人連忙跳了起來,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絨衫,肘子胸部都快爛了,滿頭的亂發,一臉斑駁的鬍鬚。他的房間像一條絲瓜,長方的,家具有一張小木桌,一張椅子,牆壁上幾個掛衣服的鈎子,他自己的床是頂着窗的,斜對面另一張床,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牆角里有一隻酒精爐,在那裏出氣,大約是他的飯菜……"
在這樣的人群中,徐志摩覺得很窘。他說,有一次他與陳博生去英國,也曾經感到很窘,因為與周圍的人相比,他們這兩個中國人簡直是叫化子。這次到莫斯科來,他又覺得很窘,卻不是因為自己寒酸,而是因為自己的穿着太闊氣。因為在莫斯科,"晦氣是本色,襤褸是應分",而且人們的臉上只有憂鬱,沒有笑容,一個個都好像心頭沉重。

徐志摩
面對革命之後的俄羅斯,面對蘇俄的所謂社會改造,徐志摩感慨萬端,寫下了這樣的俏皮話:
什麼習慣都打得破,什麼標準都可以翻身,什麼思想都可以顛倒,什麼束縛都可以擺脫,什麼衣服都可以反穿……將來我們這兩腳行動厭倦了時競不妨翻新樣叫兩隻手幫着來走,誰要再站起來就是笑話……
《歐洲漫錄》記下了一些很有意義的事,有的涉及文化政策,有的透露了新制度的特色。徐志摩說:"我在京的時候,記得有一天,為《東方雜誌》上一條新聞,和朋友們起勁的談了半天,那新聞是列寧死後,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訴,被告是骨頭早腐了的托爾斯泰,說他的書,是代表波淇窪的人生觀,與蘇維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寧臨死的時候,叮囑他太太一定要取締他,否則蘇維埃有危險。法庭的判決是列寧太太的勝訴,宣告托爾斯泰的書一起毀版,現在的書全化成灰,從這灰再造紙,改印列寧的書,我們那時大家說這消息太離奇了,或許又是美國存心污毀蘇俄的一種宣傳……"參加那次談話的,還有陳西瀅、郁達夫等人。因為他們都是作家,所以很關心托爾斯泰著作被禁毀的事。帶着這份關心,徐志摩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問及那則新聞,托爾斯泰小姐卻沒有正面回答,而只是說:現在托爾斯泰的書買不到了,不但托爾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書也都快滅跡了。徐志摩問:莫斯科還有哪些重要的文學家?得到的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是禮拜六到達莫斯科的,本想利用周六、周日好好看莫斯科,沒有想到的是,碰巧一位大人物死了,"因為他出殯,整個莫斯科就得關門當孝子,滿街上迎喪,家家掛半旗,跳舞場不跳舞,戲館不演戲,什麼都沒有了"。喪事辦過之後,劇院可以演戲了。徐志摩等人去看戲,卻又遇到了這樣的事:劇院有戲,但售票處沒人,找人詢問,才知道"今晚不售門票",原因是所有的座位都讓黨的俱樂部包了,一般人不能進。徐志摩等人特別幸運,因為找到一個朋友,他們就被請進了劇院,而且不用買票。
由此,徐志摩見識了新社會的新秩序,也見識了黨在蘇俄的權威。
然後是參觀列寧遺體。正是這次參觀,讓徐志摩對對羅素產生了深深的歉意:"早幾年我膽子大得多,羅素批評了蘇維埃,我批評了羅素……我只記得羅素說,'我到俄國去的時候是一個共產黨,但……'意思是說他一到俄國,就取消了他紅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這回我自己也到了那空氣里去呼吸了幾天,我沒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從不曾有過信仰,共產或不共產。但我的確比先前明白了些,為什麼羅素不能向後轉……我覺得這世界的罪孽實在太深了,枝葉的改變,是要不到的,人們不根本悔悟的時候,不免遭大劫,但執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兒,也不是魔鬼,還是人類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負有那樣的使命。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天堂的中間卻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有了這樣的感受,徐志摩對於國內的蘇化浪潮產生了深深的憂慮。他深知中國的現實所孕育的不滿,也深知中國歷史形成的文化土壤,知道國人的反抗激情是多麼容易被調動。他開始對國內的青年說話:
"怨毒"已經瀰漫在空中,進了血管,長出來時是小疽是大癰說不定,開刀總躲不了,淤着的一大包膿,總得有個出路。別國我不敢說,我最親愛的祖國,其實是墮落得太不成話了;血液里有毒,細胞里有菌,性靈里有最不堪的污穢,皮膚上有麻風。血污池裏洗澡或許是一個對症的治法……但同時我要對你們說一句話,你們不要生氣:你們口裏說的話大部分是借來的,你們不一定明白,你們說話背後,真正的意思是什麼,還有,照你們的理想,我們應得準備的代價,你們也不一定計算過或是認清楚;血海的滋味,換一句話說,我們終久還不曾大規模的嘗過。……照你現在的做法做下去時,你們不久就會覺得你們不知怎的叫人家放在虎背上去,那時候下來的好,還是不下來的好?我們現在理論時代,下筆做文章的時代,事情究竟好辦,話不圓也得說他圓的來,方的就把四個角剪了去就就圓了,回頭你自己也忘了角是你剪的,只以為原來就圓的,那我懂得。比如說到了那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種一把快刀交在你的手裏,叫你到你自己的村莊你的家族裏去見房子放火,見人動刀——你干不干?……
莫斯科是似乎做定了運命的代理人了,只要世界上,不論哪一處,多翻一陣血浪,他們便自以為離他們的理想近一步,你站在他們的地位看,這並不背謬,十分的合理。
……為什麼我們就這樣的貧,理想是得向人家借的,方法又得向人家借的?不錯,他們不說莫斯科,他們口口聲聲說國際,因此他們的就是我們的。那是騙人,我說:講和平,講人道主義,許可以加上國際的字樣,那也待考,至於殺人流血有什麼國際?你們要是躲懶,不去自己發明流自己血的方法,卻只貪圖現成,聽人家的話,我說你們就不配,你們辜負你們骨里的髓,辜負你們管里的血!
我不是主張國家主義的人,但講到革命,便不得不講國家主義。為什麼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軍師,還得運外國主意來籌劃流血?那也是一種可恥的墮落。
革英國命的是克郎威爾;革法國命的是盧騷、丹當、羅佩士披亞、羅蘭夫人;革意大利命的是馬志尼、加利包爾提;革俄國命的是列寧——你們要記着,假如革中國命的是孫中山,你們要小心了,不要讓外國來的野鬼鑽進了中山先生的棺材裏去!
幾代人的苦難過去之後,我們知道,當時的人們沒有聽從徐志摩的勸告。但是,歷史不應忘記,在那個路口上,有人這樣提醒過。它至少證明,當時的知識界並非全都犯糊塗。
接下來的問題是:在那樣一個知識界大面積狂熱的背景上,徐志摩何以能夠獨醒而不迷?眾所周知,像魯迅那樣目光銳利的人,幾年之後都沒有看透那層偽裝,自己被欺騙,卻寫了《我們再也不受騙了》那樣的文章;像胡適那樣頭腦冷靜的知識界領袖,也讚美過那"偉大的試驗",而沒有意識到它將給人類文明帶來的後果;徐志摩平時對政治並不怎麼關心,憑什麼有這樣的目光?
是依靠思想,依靠知識,還是依靠詩人那顆純潔透明而未被污染的赤子之心?與胡適相比,徐志摩讀書未必多;與魯迅相比,徐志摩對社會的了解未必深入。徐志摩所擁有的知識和理論資源,胡適等人都該有。那麼,徐志摩的優勢來自哪裏?也許真的首先來自純潔而健康的人性,來自未被污染的靈魂。理論家、學者常常會變成沒有溫度的機器;而葆有赤子之心的詩人,或許可以憑本能而做出選擇。徐志摩參觀列寧遺體展覽館,沒有像一些人那樣產生對列寧的崇拜,因為他一進門就看到了一個紅色的地球模型,由此產生了震驚與恐懼:"從北極到南極,從東極到西極(姑且這麼說),一體是血色,旁邊一把血染的鐮刀,一個血染的錘子。那樣大膽的空前的預言,摩西見了都許會失色,何況我們不禁嚇的凡胎俗骨。"看到血紅的地球模型和鐮刀錘子而產生恐怖感,大概不是知識和理論決定的。
不過,徐志摩對蘇俄的認識,也與知識有關。這得益於他的兩個老師:一個是羅素,一個是韋爾斯。
徐志摩崇拜羅素,1920年,他放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不讀,橫渡大西洋,到英國去追隨羅素。羅素的社會主義傾向眾所周知,但他也是較早認識蘇俄真相的人。早在1920年,他就隨同英國工黨代表團去蘇聯考察。蘇俄的那一套,沒有逃過羅素的眼睛,所以寫出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對於羅素的著作,徐志摩每見必讀,這次不但做了筆記,而且寫了評論。他雖然並不完全認同羅素的看法,卻也不能不受其影響。徐志摩在他的書評中說,羅素之所以拒絕蘇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布爾什維克的方法實現共產主義,人類要付出的代價過於巨大;二是即使付出如此代價,它所要達到的結果是否能夠實現,也無法讓人相信。就前者而言,它太殘酷;就後者言,它太虛幻。為了實現那個虛幻的烏托邦,採用慘烈的暴力手段,讓人類付出慘重的代價,這是羅素害怕的。羅素不滿於人類生存現狀,但他拒絕流血。他也致力於救渡人類,但救渡的辦法,只能是漸進的、和平的。這些思想,都對徐志摩產生了影響。
1920年,韋爾斯也去了蘇俄,並且見到了列寧。歸來之後,他把游俄見聞寫成遊記,刊登在倫敦的《星期日快報》上。徐志摩讀過之後,也為他寫了評論,並且寄回國內發表在《改造》上。通過徐志摩的文章,我們可以看到韋爾斯蘇俄親身經歷的事:參觀一所小學校,韋爾斯問學生平時學不學英文,學生一齊回答:學。韋爾斯又問:你們最喜歡的英國文學家是誰?學生一齊回答:韋爾斯。韋爾斯進而問道:你們喜歡他的什麼書?學生立即說出了他的十多種著作。韋爾斯不相信自己能夠如此為俄羅斯孩子所熟知,覺得這這些學生是被訓練出來的。於是,他獨自悄悄來到一所更好的學校,把那些問題重新問了一遍,得到的回答卻完全不同——孩子們對韋爾斯一無所知。韋爾斯又來到該校藏書室,書架上沒有他的任何著作。韋爾斯明白了:原來一切都是演戲。徐志摩熟知這個故事,自然也知道蘇俄是多麼會演戲,知道那種制度是如何教會孩子們說謊,並建成一個依靠謊言支撐的社會。在寫於1921年的那篇文章中,徐志摩就做出了這樣的總結:"蘇俄之招待外國名人,往往事前預備,暴長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