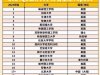看過林建華校長的道歉信,我同很多網友一樣,認可其文風質樸和態度坦白。但是也正是從其坦言中,我發現了一個遠比白字更大的問題。
先說白字。念白字是中國文化中司空見慣的事情。有幾個人敢說一個白字沒念過。我上大課點名時常常見到不認識的字,索性直接問該同學:你名字中的那個字念什麼。而林校長的問題有二。其一,如網友說,鴻鵠不是生僻的詞彙。其二,為重大儀式的致辭,事先要精心準備的。戴高樂和丘吉爾的即席演講能力舉世聞名。戴高樂的兒子對記者透露底細:「我爸爸一輩子都在準備演講稿,他和丘吉爾的差別是他承認,丘吉爾不承認。」為準備陳子明悼詞,我之前最少念過五遍,而且在稿子上標出了重音。我的不幸是,偌大的靈堂中居然不給麥克。讓一個在發聲上精心準備過輕重抑揚的人,措手不及。文化水平既定,苛求何益。我的譴責是,這是有備而來的發言,不是對即席突發的應對,閣下是怎麼準備的。有不夠敬業之嫌啊。
但與道歉信中所暴露的另一個問題相比,念白字就是小事情了。道歉信中他說:「真正讓我感到失望和內疚的,是我的這個錯誤所引起的關注,使人們忽視了我希望通過致詞讓大家理解的思想:『焦慮與質疑並不能創造價值,反而會阻礙我們邁向未來的腳步。能夠讓我們走向未來的,是堅定的信心、直面現實的勇氣和直面未來的行動。』」如果不是他在這裏提出,即使我讀過他的慶典致辭,也很可能「忽視他希望通過致詞讓大家理解的思想」。而我以為「焦慮與質疑並不能創造價值,反而會阻礙我們邁向未來的腳步」,是比念一個白字重要百倍的事情。
我們先從「質疑」說起。質疑是懷疑精神的體現。馬克思在對他女兒的自白中說他的座右銘是:懷疑一切。愛因斯坦說:提出一個問題,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沒有懷疑,何來問題;沒有問題,談何解決。密爾說:即使是一個千真萬確地道理,經懷疑後接受,和當作教條來接受,是大不一樣的。我們不談懷疑精神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性,畢竟社會是有分工的。但至少,對一所大學而言,懷疑精神是至關重要,它當然會「創造價值」。而恰恰是在面對懷疑精神上,北大的多數教師們與管理者在認識上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差異。九十年代初葉,我到北戴河講課,與時任北大副書記的林炎志住在一個房間。或許因彼此都有了解,雖初次見面,努力以朋友相待,相互刻意尋找公約數:我們都愛游泳,中學時代都是跑800公尺的好手。因此相談愉快。返京時又是兩人一同乘坐火車。車上他翻閱一本老教授回憶北大的圖書,翻到張中行的那篇,指着其中強調懷疑精神是北大最重要的精神資源一處,問我:怎麼能這麼說呢,這太不對頭了吧。我已經忘了我怎麼應對的了。只是記得,我聽後首先是震驚,震驚在看待大學精神上,教授與管理者的深刻差異。應該說,林建華校長的坦率,讓我們領受到更大的震驚。因為林炎志先生是私下與一個朋友切磋此事,而林建華校長是面對全校師生、乃至全社會,堂而皇之地宣講「質疑無價值」的人生觀、世界觀。在一個錯別字上,林校長可以立即道歉。我卻很難相信,在價值觀上我能說服他。但是這番道理我必須講,因為這關乎北大精神之核心。
關於「焦慮」也說幾句。家兄是建設部前負責人之一。一次他問我北大畢業生們的精神面貌如何。我說:我的研究生們多數是農村子弟,眼下幾乎都是房奴,很多都是父母砸鍋賣鐵還要舉債幫助他們買房結婚;儘管他們不和我談這些,但我可以感到他們內心的悲戚。家兄聽後嘆氣說:這是我們住房政策的罪過。他也算是住房問題的管理者,但他對國家住房政策能有多大作為呢。從朱鎔基總理文集的最後一篇,我們可以看到他不贊同發展私人轎車,可是在任時他對此有過作為嗎?難有作為也罷,但作為管理者對無可奈何的焦慮者說一句「焦慮不能創造價值」,是否分寸不當。
近期,敝人寫於十年前的一篇舊文「醜陋的北大人」在網上傳播(CND編者註:原文附在本文後)。文中有這樣一段話:「那一年我系一個學生的畢業論文中有虛假成分。答辯委員會的一致結論是推遲半年畢業,重寫一篇論文。系領導在沒有充分了解情況下否決了答辯委員會的結論。矛盾上交,一直吵到校級領導。我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在我們擺出全部情況,系領導聽後放棄辯護時,校級領導卻在連續兩次會上,勸說我們寬大那位同學。他們大概不會想到,他們的聲譽在多數與會教師的心目中一落千丈。這一幕令我們黯然神傷。古人云:國家興亡,食肉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同在一個校園中,大家對北大名譽的理解與珍重竟存霄壤之別。」
系內矛盾上交到學校,與我們約談的就是時任副校長的林建華先生。這是我與林校長的一面之緣。林校長當時態度平和、不站隊。但過後教務部的領導竭力勸說這個答辯組的教師放行作弊的同學。因認為這是校方的意思,林副校長的形象在我系這些教授心目中一落千丈。
接下來披露一下過後發生的,也是我從未講述過的事情。
當時是兩名本科生涉嫌抄襲剽竊。有一名的論文好得出奇。參考書目中外文書幾十本,更有海量的親自調查的材料。答辯會上,這兩方面都漏出馬腳。最後一刻我問她:調查有錄音或筆記嗎,還保存着嗎?她說有。我說:回宿舍拿一趟。只要有調查記錄,任憑她論文中的其他不實之處,我都準備放行。但直到最後一個學生答辯完畢,她也沒有回來。此時該同學已經獲得美國大學的全獎。而答辯會上的結論是重做論文,延遲畢業。稍後該生又偽造了調查採訪的錄音。隨矛盾上交,此事在我系師生中成軒然大波。在幾方對峙,我堅持不退讓之時——我的態度系內師生皆知,該同學來電話要和我面談。我一再表示不同意面談,她再三再四地堅持,最後她來到我家。見面後就說:我是作弊,我欽佩您的態度和眼光,我只對你一個人講,我也必須對一個人講出此事,不然我心裏堵得慌。在教務部和我系教師座談會上,我只分析論文,不談該同學和我的談話,因為那是私人談話,不該作為證據。經過激烈爭論後,達成妥協:兩名涉嫌剽竊者,剛才說到的那位延遲畢業重寫論文,另一位放行通過。放行的這一位,日後到香港讀書,一年後再次作弊被學校開除。如此結局,讓人唏噓。
拙文「醜陋的北大人」中那一段落的結語是:「同在一個校園中,大家對北大名譽的理解與珍重竟存霄壤之別。」這裏加上一句:大家對北大精神的理解,也存霄壤之別。
林校長道歉信的結尾,表達了他對一個白字導致大家忽視了他的重大思想感到失望。我認同他的大小之別。願與林校長和大家一同關注、討論更大的事情。
(作者為北大社會學系退休教授)
附:《醜陋的北大人》by鄭也夫

這個場景,北大人稱為一塌糊塗(一塔湖圖)
筆者按:今年(2008)逢北大110年校慶,校宣傳部早就在編輯一部紀念文集。本文是數月前應學校宣傳部的幾番熱情邀請而勉力寫成的。他們看後當即通知我,這樣的文章無法入選。我卻以為每個人有自己校慶的表達方式,校方應該有寬容的胸襟,不該像衙門那般喜聽諛詞。入不入那本文集,我說了不算。但該說出的話還是要說的。
我是2004年2月調到北大社會學系的。已經記不得多少次了,朋友們讓我談談對北大的印象。我心口如一:我哪裏了解北大,它是龐然大物,我是邊緣侏儒,我只在有限的程度上了解我的一些學生。但是以後的經歷卻使我深深地疑惑:校內各級領導都了解北大嗎?我們所知道的事情他們都清楚嗎?經過各自主客觀上的微妙組合,每個北大人都有自己對北大的印象。中心的人未必沒有盲點,邊緣的人未必沒有洞見。一個基層教師可能見木不見林,一個全局領導者可能失去了細微和縱深。普通教師的積極態度就是利用一切機會談自己的印象,發自己的牢騷。它是一個邊緣人參與北大建設的第一步。
接觸北大、形成印象,在成為它的一員之前就開始了。大概是1988年的五四,我應邀參加北大團委組織的一個座談會。會上一位同學站昂首天外、慷慨陳詞:「社會在改革,北大也應該改革;北大不要作象牙塔。北大有太多的沒有用的課程,都應該撤銷,北大要為社會服務,要為中國現代化做貢獻。」我記得當時我也像他一樣霍然起立:「照這位同學的看法,很多院系和專業應該撤銷,梵文、考古等等,能夠幫助中國致富嗎?如果完全致力於實用,大學還是大學嗎?」該同學的言論在那個時代,乃至今天,出現在社會上都稀鬆平常,使我驚訝的是,他可以在中國第一學府中像發現真理一樣,坦然陳述。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舉辦了演講比賽,我當時還是人大教師,被邀請擔任評委。第一個講完,我的感覺是真好,別的學校本科生恐怕達不到。第二個講完,驚呼更好。講到第三個,覺得只有北大能如此人才薈萃。再聽第四個、第五個,壞了,越聽越倒胃口,仿佛看到了一批精緻閃光的螺絲釘。聽完全部,悲從中來。幸虧,有個異類,數學系的殷俊同學,風格迥異。寫這篇文章時,我欣喜地從網上發現了他的演講,引用幾句,給大家一點印象:「學了地理學,我們知道,北大是一條河,前進時難免泥沙俱下,但進入社會的大海時,泥沙終將沉澱。但如果這條傳統的河在某個重要地點淤塞了,就將腐敗發臭,毒害而不是清潔靠近它的人。學了生態學,我們知道,北大是片森林,只有保持多樣性,才能永葆生機。學了物理學,我們知道,能量越低越穩定,結構越規則越穩定。所以北大的同學們,請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嚴謹吧。學了統計學,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北大的一個樣本,別人往往就通過我們來認識北大。所以我們要時刻牢記:『我就代表北大!』我們來到北大,就像一張張軟盤,到北大這台計算機上來,拷走了知識,也拷走了精神。在拷走的同時,我們還要問問自己,我給北大留下了什麼?」最終殷俊獲得優勝。評委們推舉三人作總結髮言,我是其中之一。我在發言中說:「你們講的都很好,但是怎麼好的像是一個模子出來的,今晚幸虧有個數學系的同學,他挽救了這場比賽,平衡了一個世界。我想二三十年代的北大不會是這個樣子,不可能是這個樣子,因為它那時的老師就不是這個樣子,它的教師和而不同。」
演講比賽上另一個令我悲哀的事情是主持比賽的同學對評委總結髮言的順序安排,倒數第三是謝冕老師,倒數第二是我,壓軸的是白岩松。簡直是豈有此理,謝老師是三人中年齡最長者,是三人中唯一的本校教師,白岩松是年齡最輕者,非學院中人。校園文化怎麼可以輕看自己的長者,高抬一個媒體少年呢?同學們連本校的大牌教授和一個媒體記者的差異都不知曉,怕不是分寸可以度量的了。它發生在堂堂第一學府,足見今日中國之禮崩樂壞。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門課即將結束時,去北醫三院看了一次病,記得花了二、三百元錢。我不懂學校的規矩,報銷未果。補齊了手續,正發愁明天還要來校,不然就過期了。這當口碰到了上我課的一個同學。我將這事委託給她。但是我以後再也沒有見到她。我猜想,她忘記了這事,那票據作廢了,最終她選擇了躲避我的策略。她如果和我講出此事,我決不可能要她賠償。遺忘可以理解,躲避是不可原諒的。過後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找到她談談,錢我當然不會要,教育她是我份內的事情:一個連這點責任都不敢面對的人,日後能擔當家國重任嗎?但我最終放棄了。沒有得到應有的教誨是她走到這步田地的原因之一,我身為一名北大的教師卻繼續着放任。
那一年我系一個學生的畢業論文中有虛假成分。答辯委員會的一致結論是推遲半年畢業,重寫一篇論文。系領導在沒有充分了解情況下否決了答辯委員會的結論。矛盾上交,一直吵到校級領導。我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在我們擺出全部情況,系領導聽後放棄辯護時,校級領導卻在連續兩次會上,勸說我們寬大那位同學。他們大概不會想到,他們的聲譽在多數與會教師的心目中一落千丈。這一幕令我們黯然神傷。古人云:國家興亡,食肉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同在一個校園中,大家對北大名譽的理解與珍重竟存霄壤之別。
這次爭論不幸撥動了我系遺留下來的派系矛盾之琴弦。一位教師在衝突關口對我這個局外人說:當年校方為什麼非要系所合併呢?兩邊都不是壞人,但我們爭吵了這麼多年,我們這些人的最好的時光都浪費掉了。我看她幾乎要哭出來。我不知道我系派系的全部歷史,但我親身感受到這是怎樣的一個系。我是個「老游擊隊員」。就讀過的高校和供職過的單位,總計十個,可算見多識廣。而這是我所經歷過的最冰冷的、少交往的單位。而我們恰恰是最需要交往和溝通的所謂思想者。
外部人常以為,北大的學生最好。差不多每次碩士生面試後,都少不了幾位教師大發牢騷。因為總會遇到多個筆試分數很高,難以淘汰的考生,他們除了應試的教科書,什麼都沒讀過,有些已經應試多年。一句話,我們這些教師在同考生的博弈中被算計了。我們都知道,高級人才的選拔重於培養,你打死鄭也夫,他也練不成劉翔。那麼明知成才規律如此,明知我們敗給了考生,為什麼不挖空心思,反省考試路數,精心設計試題,重新博弈呢?似乎大家都很忙。我們的感慨,始於面試後的牢騷,也終於面試後的牢騷。年復一年,周而復始。
本系多位教師和我說過,社會學系的碩士論文是全校各院校中最好的。我沒有比較,無從判斷。但我是這兩年中唯一讀過我系全部碩士論文的教師,我知道,我系專心寫畢業論文的碩士生越來越少了。如果他們都全力以赴,會有半數,即30人,達到現在的尖子,前三名的水平。他們心有旁騖,是因為擇業的壓力,他們忙不迭地去面試,用人單位動輒要他們去實習。擇業大約要花去近一年的時光。一言以蔽之,同社會的博弈,我們同樣是失敗者。我們應該深刻反省,制定方針。可惜這同樣是排不上隊的事情。
人有足夠的惰性,不然何需暮鼓晨鐘,那敲打全為驚醒你。一個特殊時刻(譬如110周年校慶)也有這種意味,所以才有了這篇不合時宜、殊少頌揚的文章。
回到本文開篇的那個段子。一個認同實用的學生,怨得上北大嗎,況今日社會功利滔滔。我們說,大學是服務於社會的。但這是一種特殊的服務,不生產衣食,不提供住行。它服務社會的方式,恰恰是要和社會拉開距離。它要平衡、反省,乃至批判社會主流價值觀。他需要自己的規則,自己的標準,自己的氣質,自己的情操,自己的精神。在這些方面,北大還有自己赫然凌駕於其他院校,凌駕於世俗社會的定力嗎?如果這諸方面,不是大學幫助社會提升,而是任憑社會席捲大學,那其實是辜負了社會長久以來的重託,大學可以壽終正寢了。
鄭也夫(北大社會學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