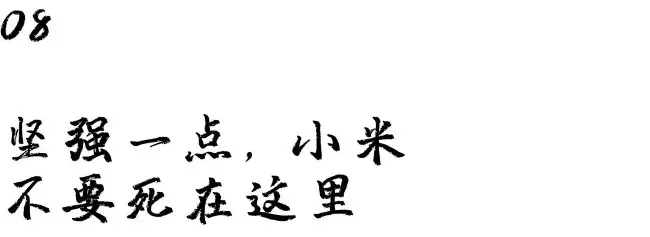
醒來時我聽到了一群人嘰嘰喳喳的聲音。
那個曉麗呀,給你唱首歌好不好?哎呀算了,我唱得太難聽了,不給你唱了。
你喜歡聽誰唱的歌呀?我給你放一首。
你皮膚怎麼這麼好啊……
是一群護士,像小朋友一樣,圍着我嘰嘰喳喳叫。原來是被他們吵醒了。吵死了。好多人在面前,很煩哪,怎麼會有這樣的人類啊?
有人在拍我的臉,有人在唱歌,有人在給我梳頭、扎辮子。擦身體的,餵藥的,量體溫的,她們在輪番照顧我。
我一睜開眼,她們就說:「哇,醒來了,醒來了!」一個個特別的興奮、開心。
有好幾個人說:「把你喚醒了,我們就可以下班啦。」她們全都放下了手中的活,開始收拾自己的東西。
手術從6月1日下午4點開始,一直做到晚上8點。
醫生打開了我的腹腔,抽掉滿腹的髒血。瘤體已經破裂,污染了腎臟。醫生剝掉了錯構瘤。又切掉了半個左腎。留了半個。
如果把錯構瘤連同整個左腎一股腦切除,手術只要兩個小時。只切除半個腎的手術複雜多了,要先把瘤體小心剝離,再切除半個腎臟,然後做血管縫合,腎臟縫合,腎臟止血……
再把肚子縫回去。
肚子上開了一條36厘米長的口子,從胃部側面一直往下,再向左折向左腎的位置,像大寫的英文字母L。
先後兩位醫生縫這條刀口。刀口豎着的一段是一位醫生縫的,針腳比較寬鬆,刀口橫着的一段是另一位醫生縫的,針腳則比較細密。兩位醫生的手藝活不一樣,看上去非常明顯。
刀口的下面還打了兩個洞,插了兩根引流管,分別把腹腔和盆腔里的髒血、積液引流出來。
6月1日晚上9點做完手術,一直昏迷。再次醒來是第二天早上8點。
疼痛難忍。麻藥逐漸失效,全身到處都痛,越來越痛。好痛啊,快要痛死過去了。
醫生給我裝了一根鎮痛棒。醫生說:你覺得痛得無法忍受的時候,就自己按一下鎮痛棒。
於是我就自己按一下。結果直接被打昏迷。昏迷了自然不知道痛了。
所以說它是麻醉棒,更合適,把人麻昏過去,睡着,自然不痛了。多虧有這根鎮痛棒。
做手術前就上了呼吸機。醒來以後,體徵很微弱,血壓也很低,更要靠呼吸機了。
呼吸機的管子從嘴巴、喉嚨插下去,一直伸進肺里。不能說話,不能吃東西,也不能自己呼吸。非常難受,生不如死。
我心裏對自己說:堅強一點,小米,你已經從生命的盡頭折返,你不要死在這裏,你要從這裏出去。
要從重症監護室出去,得先拔掉呼吸機。
這呼吸機像是長在我的肺里,而且越長越牢了。我覺得它像極了以前在科幻片裡看過的異形怪物,在支配着我的呼吸和生死。
我說不了話,我用盡方法向醫生護士示意,幫我拿掉呼吸機。可我能用的方法太有限:使勁地轉動眼珠子、搖頭,嘴巴發出嗚嗚嗚的聲音——只有我自己能聽出我說的是:「這個不要了這個不要了。」
後來,有位醫生聽明白了我說的話。他回答我:明天8:30給你取呼吸機啊。
第二天,我一直等到九點三刻,醫生才來給我取呼吸機。
那個呼吸機好大啊,我覺得它已經佔據了我的整個胸腔。醫生把它拔出來,讓我看,一邊說:你看看,你肺里都有些啥!怎麼這麼噁心哪,你一個女孩子,又不抽煙,怎麼有那麼多痰?
它就像一頭大象的耳朵,又大又噁心。
我感覺如釋重負。太爽了,又可以用嘴巴說話了,又可以自己張大嘴巴呼吸了。
不能喝水。喝水還得靠鼻飼管。
最重要的是,拔掉呼吸機,我就可以離開重症監護室了。

6月5日,我的病床從ICU推到了普通病房。
我看見了老公、媽媽、小姑子、弟弟,我在杭州的親戚,基本上都在了,一個個淚眼婆娑的。
他們都覺得,我從ICU轉到普通病房就好了。老公拍了一張我躺在病床上的照片。哇,看起來就像一具死屍。老公是5月30日晚上從海南飛回來的。
轉到普通病房的那一天特別難受。又一次感覺生不如死。
疼啊。做手術前就疼,做完手術更疼。比我當年的剖腹產還要痛十倍。
在ICU里有很多護士照顧。轉到了普通病房,沒了。老公留在病房陪床,其他親戚都被趕出去了。
那天晚上我開始劇烈地咳嗽。醫生告訴我,之前的呼吸機已經讓肺部感染。
本來就痛,咳起來更痛。特別是那些動過手術的刀口,我一咳嗽它們幾乎就要裂開。痛死。後來每次咳嗽前,我都讓老公先幫我擠住肚子。防止裂開啊。兩個人都累得滿頭大汗。
最難受的是不能聞任何味道,一聞就反胃,乾嘔。你也不能捂鼻子,因為鼻上里插着管子,一直通到胃裏。你輕輕一按這根管子,胃部仿佛就開始攪動,更加反胃。
隔壁床住着一位大叔,75歲,癌症晚期,一個人住在病房裏。
他照顧自己的方式是點外賣吃。都晚上9:00了,他還在吃外賣,估計是麻辣燙,味道非常的刺鼻。他還吃得很香,整個房間都是他喝湯吃菜的聲音。
難受。反胃。特別反感。我覺得我想滅了他的心都有了。
怎麼會跟這樣一位大叔住一個房間?我問老公能不能找醫生換房間。
大叔聽見了,說:「這個房間已經是挺好的了,我做你的鄰居也是挺好的了。」
老公對大叔說:「大叔,你能不能聲音輕點。我老婆剛從重症監護室里出來,什麼味道都聞不了。」
大叔就不再吃那些東西了。哦,是不在病房裏吃。後來大叔對我說:「我都是去醫院那個小公園裏吃的啊。」
等我身體好一點,我對大叔說:「不好意思,那一天我身體特別難受。」
這個鄰居大叔,真的已經很不錯了。在他身上,你還能看到生命的既煩人又可愛的氣息。不像是在重症監護室,時時刻刻都是死亡的味道。
記得重症監護室里有四張床,我是17號。
我斜對面住着一個女孩子,浙江安吉人,23歲,肺部感染。在我做第二次手術之前她被拉走了,家屬把她拉回安吉。
在被拉走之前,我聽見一個醫生對另一個醫生說:「給病人留一口氣啊,留給家屬。」
是啊,我聽見醫生這麼說。也許,那個生命垂危的女孩子也聽到了。給病人留一口氣。這口氣也是留給家屬的。可以活着帶離醫院。
我對面的老太太已經住了很久了。粉碎性骨折,腦子也摔到了。在排隊等做手術。還沒排上。
我左邊的是一個老頭兒。一直昏迷,一句話也不會說,滴水不進,大小便失禁。
重症監護室里四個病人,我最清醒。
活着好不容易啊。

第一次下床學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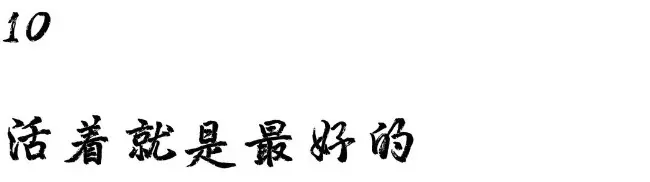
5月28日發病,5月30日第一次手術,6月1日第二次手術,在重症監護室待了8天,在普通病房又待了18天。
所有人都找不到我了,喝茶也找不到人了,談事情也聯繫不上了。
有朋友「氣憤」地說:小米肯定是賺大錢了,電話也不接了,這個裝逼可裝到家了。
劫後重生,很多朋友見到我以後就先哭,說,你現在都瘦成這樣了。
我說,你們不要這樣了。
我一個人的時候,還是忍不住會哭。
2022年元旦,我從北京回杭州,想起這一年的遭遇,我一路哭回來。送我的司機不敢跟我多說一句話。
2021年終於翻篇了。沒多少人能通得過這一年的考驗。
有人說,2021年是過去10年裏最糟糕的一年,但它是未來十年裏最好的一年。2022年比2021年更難。
對我,不是這樣的。2021年最難,我活過來了。

出院後第一次遠行
我1981年生於河南濮陽。先生是我高中同學,同桌。我大學讀漢語言文學,先生讀藝校。我們2002年開始談戀愛,2011年結婚。
在學校里我就自己開店。那個時候我就想着做生意賺錢。不以賺錢為目的生存都是耍流氓,我就是這樣想的。
大學畢業以後我就來到了杭州。我2006年~2012年在阿里上班。996算什麼,我們比996還厲害,從早上8點忙到晚上12點。
晚上12點,對我來說,只是正常下班時間。還可以再去玩一下,就是這樣子。我的朋友都是這個樣子的。我也是這個樣子,一個兩肋插刀的「女俠」。
別人找我幫忙,我從不拒絕。但我脾氣不好。
我的開場白經常是這樣的:「我今天只有45分鐘時間,多一分鐘都不會給你。請組織好你的語言,開始你的表演。」
朋友害怕和我交流,剛開始聊天的時候,會緊張得語無倫次。

每天喝酒,至少兩場打底,多則三五場。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喝完以後給老公打電話,又給朋友打電話,讓他們同時去接我。
看到他們一排人等在酒店門口,我好驕傲啊,有這麼多人願意來接我。那時候我已經醉得不行了。
有一次我去鴻雁老家,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放蕩不羈的狀態啊,操着很大的玻璃杯,大口大口地喝白酒,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杯,喝得不省人事,直接從凳子上滑下去了。
經常嗨到半夜三四點,有時候到凌晨五六點才結束回家。吃個早餐,洗個澡,送女兒上學。真的太消耗自己了。
什麼東西都想要,什麼東西都想觸及。每樣東西都捨不得放棄。我好像迷失了。
從醫院出來後我再也沒喝過一滴酒。不再喝酒了。
也不熬夜了。晚上11點,最遲11:30,朋友們就找不到我了。以前我把手機放邊上,有誰找我,不會找不到的。
過去這一年,我沒打過一針,沒去整過形,沒貼過面膜。
清靜下來了。累了就睡一覺,睡一覺不行,睡兩覺。大多數時間吃素。
我覺得活着就是最重要的事情,這是我這場大病之後最重要的感悟。活着就是最好的。
現在更多的是,一個人靜靜坐着,看看書。我原來不愛讀書的。原來讀不進的書,現在能讀進去了。原來那種看不進去的文字,現在發現,那些文字是有靈魂的。
一個人坐着,安靜地喝茶。生病之前,我從來不會一個人坐在這裏喝茶。以前我會坐在茶桌前喝酒。
喝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喜歡泡茶,泡茶之前,我沐浴更衣,穿上最乾淨的衣服。泡茶,喝茶,讓我的心靜下來。
有一天我發現,我從小的夢想並不是賺錢,我的夢想是寫一本書,過詩一樣的生活。
每天喝喝茶、種種花,這就是詩一樣的生活。

出事前,我、一米(鴻雁)、二姐(榮芳)、三水(張淼)四姐妹,成立了一家公司,經營一家叫「一米一粟」的茶室。
出院以後,我才真正知道一米一粟,是多麼的來之不易。其他的事情都省省吧,只做這「一米一粟」。
我一直記得那個夢,我來到了生命的盡頭,那裏有大片的草坪,有防腐木做的圍欄,上面掛着鮮花。
出院以後,我在茶室外面的露台上鋪了防腐木。就像夢裏看到的一樣。有鮮花,有藍天,還有小鳥。

我在醫院裏陷入昏迷的時候,老公找人給我算命。算命先生說,你老婆命不該絕,不要擔心。他們擔心我死了。
老公在不到一米寬的陪護床上睡了十天。
原來我經常跟老公吵架。認識很久了,我一直對他很兇。
在重症監護室,有護士幫我擦身體,幫我刷牙、洗臉、弄頭髮。轉到普通病房後,這些事情就由老公做了。
病情嚴重的時候,我大小便失禁,老公一點不嫌棄,也不怕麻煩。這時我大腦已經很清醒了,因此很羞澀。我說,找個護工幫我弄吧。但老公不肯。
那時候,我就默默地說:「老公,我一定要活下來,好好對你。」
已經5月份了,他覺得直接用濕紙巾擦身體,太涼了,就用溫水先溫一下再拿來給我擦。
我覺得他太細心了。這麼細心,真好。以前他應該也是這麼細心的,只是我看不到。老公平時特別痴迷拍照,喜歡手工,動手能力很強,是個技術男。已經在手裏這麼多年了,現在我才發現他有多好。
他照顧得非常周到。一口湯,一口粥,一口熱水,他都要自己先嘗一下燙不燙,才讓我喝。這個太燙了,再晾一下。那個,再加點礦泉水。
有一天我躺在病床上,覺得這老公真帥。我脫口而出喊道:「老公!」
之前我從沒喊過「老公」,從來都是提名道姓地喊。在病房裏我第一次喊出了「老公」這倆字兒。
開始他沒反應。
我想,是不是我在病房裏喊他老公,他覺得不太合適?
過了一會兒,他回過頭來,給了我一個靦腆的微笑。
就像20年前,那是在2002年,他第一次到河南新鄉學院來找我,我在校門口看到他的微笑。
我突然又有了戀愛的感覺。
是的,20年後,我又重新戀愛了。

2014年我生下女兒,媽媽到杭州來照顧我。她是1954年的,今年68歲。
有段時間,我覺得她一定得了老年痴呆症,腦子都不太清醒了。我生病以後才發現,她並沒得老年痴呆,她很穩重,每一個關鍵時刻都清楚地知道該去做什麼。
媽媽非常愛我。為了我,她可以連命都不要。她只是相對比較強勢,因為她當了一輩子的老師。
在做第二次手術前,我從昏迷中醒來,醫生問我:「你有什麼想吃的?」
我想,這就是傳說中的送行飯吧。我對醫生說,我想吃一碗麵。
媽媽也覺得這是送行飯。她哭着去飯店裏,幫我點了一碗她認為很好吃的面。
其實我根本不想吃什麼面,我只是想,這是送行飯,我只想吃一碗媽媽燒的面。
出院以後,媽媽經常對我說:想開一點,對自己好一點,不用管我和你爸爸,我們有退休工資的。
2021年5月28日早上,送女兒去學校,再見到她是我出院的那一天。女兒看着消瘦的我,說:「媽媽,我以為永遠見不着你了。」
我想起6月1日那天,我曾經告訴自己:如果重生,就做個小朋友。
感謝上天又重新給我生命。每個周末,我都帶女兒到外面去玩,一起做小朋友,不管晴天還是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