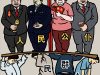這樣劉文彩公館裏的水牢變成了中國地主階級剝削和奴役窮人的人間地獄的樣板,在全國到處宣傳。直到文革結束後,陳列館派出專人採訪70多位知情者,查閱了大量的文史和檔案資料,才得以真相大白。這水牢根本不存在,冷月英一會說1937年坐的水牢,一會兒說是在1943年。而水牢位置卻是劉文彩公館堆放鴉片的倉庫,1945年被人放火燒掉之後才蓋了地下室,冷月英怎麼可能在1937年或1943年在地下室里坐過牢呢?而且地下室與風水墩只隔幾步。劉文彩對於善惡之事非常忌諱,在風水墩燒香拜佛,對於一心想善哉善哉的大地主,怎能在佛根清靜的鄰近地,進行令人髮指的酷刑。
文革結束後,陳列館派人來調查冷月英時,她只說「自己記不清了」,「領導叫我不要隨便說」。當實在被追問得厲害時,她才說:「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讓我這樣講的,要問,去問縣委好了!」
其實,這造假之作不是在文革結束後才被揭穿的,冷月英的假話謊話根本不堪一擊而不攻自破的,在文革期間也被他們自己的狗咬狗互咬中揭穿了。
當冷月英剛開始在當地血淚控訴時,很多居民就故意問她:我們怎麼不知道劉文彩家有水牢呢?你是哪裏來的,我們怎麼不認識你呢?面對這些問話冷月英不得不回答說:「我說的是冤枉話,但這不是我要講的,是上面叫我來說的。」當局害怕這樣下去中洪這部造假機器要癱瘓,所以立即制止她不得泄露內幕真相。
冷月英不敢說真話了,但是在文革中,在派性的互咬中還是被揭穿出來。安仁鎮有一名叫萬洪雲的廚師,他原在劉文彩長兄劉文淵家幹活,做得一手好菜而深得劉文淵的賞識。上世紀五十年代生病就醫時,被大夫李伯華打針在身上留下了一個凹痕。當局為了妖魔化劉文彩,就把這道凹痕說成是劉文彩用彈簧鋼鞭打的,並特地定製了一條彈簧鋼鞭,讓他拿着去現身說法到處訴苦,控訴劉文彩的罪行。於是他也成了「家史演講組」成員之一,並成了僅次於冷月英的第二號「訴苦明星」,為當局煽動階級仇恨而賣命。
萬洪雲因控訴劉文彩的罪行而竄紅了幾年,不料在文革派性鬥爭中,萬洪雲與冷月英雙方各處對立的一派,相互展開了派性之戰。萬洪雲先用大字報揭露冷月英根本就不是劉文彩的佃戶,也從來沒坐過水牢。冷月英等人也針鋒相對寫出大字報反擊,揭露萬洪雲身上的凹痕不是劉文彩打的,是醫生打針時打漏了留下的凹痕。
當局眼看着造假機器又陷入了危機,再不制止會把內幕真相全都穿棚,就不得不把萬洪雲趕出了「講演組」,《收租院》里根據萬洪雲挨打的塑像也拆掉了,還把他定為壞分子來批鬥。但是這根彈簧鋼鞭卻留了下來,成為劉文彩罪證的證據陳列着。
於是宣傳材料中改寫了一番:居然讓劉文彩的廚師混進「家史演講組」來了,(問問是誰讓他混進來的,還不是你們這些人嗎?)可見階級鬥爭之複雜,今後更要提高革命警惕,把好階級鬥爭這一關。(應該是把他造假撒謊這一關吧!)
當局為了補救造假被揭穿的命運,就把冷月英提升為縣革委副主任,打倒一個,樹立一個。接着以清查謠言為名來威脅和恫嚇當地民眾,使他們再也不敢議論水牢的真與假的問題。
那時凡是有人說劉文彩家沒有水牢的人,幾乎都被抓起來吊打,用恐怖手段讓民眾閉口。當年凡是說沒有水牢的人當局都加以迫害打擊,李蒙松因為說劉文彩家沒有水牢就被抓去勞改,判刑10年。在《莊園擋案》裏還記載了李維嘉(四川省政協副主席)親自出馬逼民主人士王安懋,劉樹成作假證的材料。雖然當局現在已承認「水牢」故亊是虛構的,是假的,但李蒙松和許多冤案受害者至今還沒有平反。
1988年,地下室的水抽乾了,鐵籠搬走了,有關水牢的印記消失得乾乾淨淨,只見上面換了一塊牌子,上書「鴉片煙室」四個大字。還有那「刑具室」「行刑室」經過考證,也都是屬於子虛烏有的事。所以把「行刑室」「刑具室」都撤了,恢復當年「瓷器室」「年貨室」的原貌。
雖然道具和佈景可以改動變換,但是「劉文彩經常用關水牢和地牢的刑法殘害群眾」的印象,卻深深地烙印在人們的記憶中。特別是郭沫若在參觀《收租院》泥塑展覽後所寫的那首《水調歌頭》詞,至今仍鐫刻在《地主莊園陳列館》的序館高牆上,似乎還在告訴人們「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郭沫若的《水調歌頭》詞是這樣寫的:
「一入收租院,難忘階級仇。大邑土豪惡霸,暴發一家劉。水牢地牢連比,長槍短槍無數,隨意斷人頭。苦海窮人血,糧倉地主樓。
飛輪轉,彈鞭動,鬼神愁。荒淫無恥,佛殿金鐘伴玉甌。轉瞬人間換了,活把閻王駭死,萬眾競來游。教育耿千載,風雷震五洲。」
在郭沫若的筆下,劉文彩地主莊園變成了人間地獄,而劉文彩本人也成了罪該萬死魔王。所以他的墓在文革還沒到橫掃一切之前的1958年大躍進期間,已經被人挖墳掘墓碎屍萬段了。
收買賄賂多名喇叭筒,為造假大造聲勢
在這個龐大的國家造假機器中,並不是只有冷月英、萬洪雲這兩個人擔任喇叭筒角色,為了擴大造謠渠道,擴散謊言範圍,加強虛張聲勢的力度,讓這些喇叭筒奔向工廠農村機關學校,到處去「憶苦思甜」,使階級鬥爭的烈火在全國各地熊熊燃燒,所以中洪當局特地成立了「家史演講組」,打造了多名喇叭筒,羅二娘也是其中之一。
在羅二娘聲聲控訴中:大地主劉文彩要吃她的奶,她不得不扔下自己的孩子來給他餵奶。結果睡在床上的劉文彩把她的奶頭咬破了,還要強姦她!《收租院解說詞》是這樣寫的:「當年羅二娘因交不起租子就是這樣被拉去,而自己的孩子卻活活餓死了。開始劉文彩每天讓羅二娘擠幾盅奶來吃,以後就讓羅二娘到床邊直接餵奶吃。有一次,羅二娘餵自己快要餓死的孩子。剛剛餵過,這時劉文彩又要吃奶,羅二娘把奶頭送進蚊帳里,劉文彩吸了兩下沒有奶水,就狠狠地咬了一口,當時鮮血直流,痛得羅二娘滿地直滾,至今奶頭上還留下了傷印。它記下了勞動人民刻骨的仇恨!同志們,誰人沒有父母?誰人沒有親骨肉?誰人不是母親所生?當你的媽媽遭到如此悲慘遭遇時,你有何感覺?你是怎麼想的呢?」
人們都聽說只有給嬰兒孩子餵奶的,沒聽說過給大老爺們餵奶的。如今這個大地主不僅要吃她的奶,還把她的奶頭咬破,讓她的孩子吃不到奶而活活餓死,甚至還要對羅二娘強姦。這種超乎尋常悖理的事按在大地主劉文彩身上,怎不引起群眾對整個地主階級的仇視與仇恨!
在中央電視台副台長陳漢元所導演的電影《收租院》中,卻說劉文彩曾雇了六個奶媽來供他喝人奶。這還不夠,又把劉夫人王玉清醜化了一番,說王玉清愛吃鴨蹼(即鴨腳),每次要吃三十隻,為此一次得宰殺十五隻鴨子供她吃鴨腳。她吃的鴨腳是用人奶再用文火慢慢地熬製的。
為了這不同尋常的「人奶」,中洪當局把所有的惡毒招數都栽在劉文彩夫婦頭上,中洪為什麼要在「人奶」上做足文章呢?大概是想進一步妖魔化地主階級,因為它是喝人血的象徵!當中洪的造假和撒謊水平到了如此地步時,真可謂是搜腸刮肚想盡一切心計而無所不用其極了。
不過中洪在栽贓陷害劉文彩的手段中除了喝人奶外,還有更惡劣的:電影《收租院》竟說劉文彩強姦了七、八百個婦女,大概他把姦污少女一千多名的毛皇帝錯按到劉文彩的頭上了吧!
羅二娘第一次在當地的戲院登台亮相時,就遭到了當地居民的強烈抵制。連她的大兒子羅學成都罵她不要臉:過去我家燒壞了鍋,養的豬都是「別個」(劉文彩)送的,現在你撒謊說假話!她的親侄子羅大文說,每逢過年,家家戶戶幾乎都得到過總辦(劉文彩)發的錢糧,羅家也不例外。
羅二娘的報告為何引來當地民眾的一聲聲譴責?原來她是個當地的醜八怪,長得像陰間裏的鬼怪——雞腳神,於是有人就用髒話罵她,「你洗乾淨沒有?」這個從未進過劉文彩家門,也沒有租種過他家田的婆娘,解放後沒聽她說過苦,土改時也沒訴過苦,到了階級鬥爭年代她卻來了勁。
原來這是中洪當局通過賄賂收買並做了思想工作之後,才讓她上台表演的。在「四清」運動中,當時大邑縣組織部女副部長朱賓康曾住在她家,動員她來作假,並給了她一個公館和許多好處。(筆者朱忠康聲明:這個朱賓康與本人不是本家,與這個被狼叼走良心的女部長毫無瓜葛,更不會做出這種坑害別人的卑鄙之事)
羅二娘這個造謠喇叭筒在三年大饑荒年代,她家活活地餓死了四口人——她丈夫、小女兒、大兒媳、大孫子。大概因為窮怕了的緣故,所以在朱部長的利誘和威逼下不得不登上賊船。到了文革,她已經被當局馴化成冷酷無情毫無人性的冷血動物了。她反咬一口,把鄰居折騰得死去活來。
解放前她把家俱賣給了鄰居潘德成,文革時她告訴紅衛兵說潘德成搶了她家的家俱。於是紅衛兵就替她報仇。此時潘德成因為在解放前做過八天保長(就像現在的村主任、居委會主任職務)被抓進監獄死在獄中,紅衛兵就把潘的老婆與孩子抓起來一通毒打,把家中的家俱都搶光給了羅二娘。更為毒辣的是紅衛兵在潘妻胸前掛了一隻煤油燈,燈火直接燒潘妻的下巴和臉,燒得潘妻嚎嚎慘叫。
這個專門把好人當作壞人來整的女人,死去後,連老鼠都沒有放過她,她的臉竟被老鼠咬穿了兩個洞!
在中洪當局物色喇叭筒時,曾想從劉文彩手下做過長工僱工身上打主意,但結果都碰了壁,請不動他們。當局不得不又重新找到了一個貧農劉青雲,為了收買他,官方給他家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給了劉青雲1000元錢。五十年前的1000元錢相當今天的數百萬元。當時一個農村勞動力一年的年收入約30元錢,1000元就相當一個農民33年的收入!這樣的重獎是多麼誘人!
於是官方給他量身定做了一套故事:「三個石頭支一口鍋」,說他們「一家人衣不遮體,妹妹沒有褲子穿,只能睡在蓑衣裏面」等等,並教他怎麼哭,什麼時候哭。但是劉青雲是個堂堂的男子漢,這些胡編亂造的謊言通過他的嘴裏一說,自己也感到羞恥。而且他家因父親抽鴉片而敗落,是劉文彩送了兩畝田維持生計的。如今竟要他在眾人面前把恩人說成大壞蛋,他的內心怎麼能受得住如此的煎熬。於是他把這1000元錢退還給了官方,堅決退出這場「訴苦」鬧劇。
這樣官方才找了冷月英和羅二娘,冷月英在接受了500元的好處費後登上了訴苦會的講壇,從此成了揚名全國的造謠喇叭筒。
不被利誘不畏強權錚錚鐵骨的劉家長工
中洪一貫標榜自己是為窮人革命造反的工農黨,黨旗上的鐮刀斧頭就是對付地主資本家富豪們的工具和武器,所以口口聲聲代表工農大眾利益,代表人民的立場。在他們的眼裏,那些曾在劉文彩家幹過活的佃工長工們一定會聽黨的話,起來造劉文彩的反,掀起階級鬥爭的高潮。
下面的這一串串充滿黨文化黨詞彙的解說詞都是根據想當然杜撰出來的:「長工杜春廷,從小進劉門;深受奴隸苦,血汗被榨盡。病老一息存,地主豺狼心;拋入慈竹林,臨死猶含恨」,「電刑摧殘心肝碎,死去活來志不移。決不甘心當奴隸,不向財主把頭低。」……解說詞中的許多人名都是虛構的,把它套在誰的身上都適用。
所以中洪在物色造謠喇叭筒時,首先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劉文彩的長工們身上。他們使出了全身解數,為這些長工僱工說盡好話,以便為黨的階級鬥爭服務,想不到這些人不但不聽黨的話,反而都一致稱讚劉文彩的為人高尚,在他們眼裏,劉文彩是個道德的楷模,是個大善人!
官方曾用小臥車去接他們,讓他們來充當造謠宣傳員,結果遭到他們的拒絕。三個長工牟春發、傅傳興、谷能山當時就說:「喊我坐臥車,穿新衣服我都不去!如果我要捲起舌頭說話(亂說),那比冷月英、羅二娘的待遇要好得多!」氣急敗壞的中洪官員碰了釘子後,就反咬一口,把這些長工僱工稱作劉文彩家豢養的爪牙與打手,這樣「被壓迫」的窮人一下子又在黨的手裏都變成了劉文彩的幫凶,在展覽館中展了出來。
到了1965年,當局為了進一步打造「收租院」,就請了四川省美術學院的師生們來創作雕塑人像,這些「藝術家」們深入民間「訪貧問苦」,聽他們吐苦水,說劉文彩是如何兇惡殘暴,結果竟讓他們大失所望,眾口都說劉文彩是大好人、大善人。這些「藝術家「們不得不諄諄善誘地啟發他們,要讓他們對地主富人充滿仇恨,讓他們說劉文彩的壞話。當過劉文彩長工的呂忠普卻盡說劉文彩的好話,氣得「藝術家」們拔腿而走。
他們又找到對門一個叫谷能山的長工,谷能山具有陽剛之氣,一副大義凜然壯漢形象。這些充滿浪漫主義的「藝術家」們對他充滿希望,如果讓他來擔當反剝削反壓迫反抗劉文彩的英雄人物,那麼洪鏟钂的「光輝形象」一下子就拔高了許多,整個「收租院」作品就能增加不少「光輝」,就立刻圍着他作起草圖來,並為他設計好了在劉文彩酷刑下一個寧死不屈的好漢形象,樹為領頭反抗剝削壓迫的英雄。「藝術家」們用階級鬥爭理論來動員他站出來訴苦,控訴劉文彩的罪行,但卻不起作用。「藝術家」們並不死心,又對他做了大量耐心細緻的工作,包括給他許多好處和金錢類的誘惑,但也沒有打動他的心。後來「藝術家」們又對谷能山說:「你是貧僱農,是無產階級,是好人;劉文彩是吃人肉、喝人血的剝削階級,你要給他劃淸界線。」而谷能山卻斬釘截鐵地回答他們:「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槍斃,我也說他(劉文彩)是個好人!」
這些「藝術家「見軟不成,立即露出猙獰面目通知民兵把他抓走關了四個月。對門的呂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嚇得他連夜歩行50公里,到大山深處的天宮廟煤礦里躲了起來。
「藝術家」本想用谷能山來醜化劉文彩,想不到沒成功,於是「藝術家」就把谷能山與劉文彩一起來醜化。他們把谷能山塑造成劉文彩的幫凶,即《收租院》裏的「風風匠」。《收租院》解說詞是這樣寫的:「在這個院子裏就放着6颱風谷機,並有專門的『風風匠』來搖,這些窮凶極惡的傢伙,拼命地搖啊,搖啊,真是搖得佃戶渾身發冷,搖得佃戶發抖……」
在由《四川日報副刊》主編王治安所寫2001年出版的一本名為《轟天絕唱——〈收租院〉泥塑奇觀》一書中,更是寫得玄乎:「在劉文彩殘酷盤剝中,更毒的招數,是在風谷機上加鋼珠(飛輪),大斗大秤,一斗租谷,只能算是六七升。請聽用淚水書寫出的一首歌吧:風谷機,鐵滾滾(加鋼珠)。地主用它來收租,五石七斗干黃谷,風來只有三斗六。年年汗水空長流,一家老小餓斷腸,即使年年大豐收,也受不住這般剝削苦。」
今天的媒體文人還在用造假撒謊發財,這些人與沒有文化的冷月英、羅二娘相比有什麼區別?!
劉文彩永遠活在長工的心中
劉文彩家中從來就沒有宣傳中說的那種狗腿子。他家只有四十來個僱工,這些人都是貧僱農,他們平時里種菜,管理果園,打掃衛生,處理糧食,秋收時收租谷,空閒時在莊園裏打打牌,從未在外傷害過他人。本地老農說:「主人都是善人,下面的人也學主人的樣。」
所以在中洪在妖魔化劉文彩而大造輿論攻勢的年代裏,沒有一個長工背着良心跟着中洪充當造假喇叭筒的,更沒有一個踩着劉文彩這座被打倒的形象而往上爬的。為什麼?為什麼被中洪當作苦大仇深的僱工們一致說劉文彩好?這是因為「物極必反」。中洪的造假機器造得太誇張了,太不成體統了,太不成人性了,已經達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如果把妖魔化後的劉文彩與中洪暴政幹部們相比較,倒是恰如其分,惟妙惟肖。那時正處於大批餓死人的年代,中洪一邊干盡了壞事,一邊卻反咬別人干盡了壞事,其實恰恰是他們這夥人才是無法無天,強姦民意,指鹿為馬,殘害民眾,驅趕產婦,逼死人命,編造歷史,抹黑別人,恩將仇報,殺良冒公,裝神弄鬼,造假撒謊者。妖魔化劉文彩,就是那些魚目混珠、顛倒黑白、喪心病狂變態者的中洪黨員幹部們才能幹得出來!
在長工的心目中,劉文彩既不是地主更不是惡霸,而是一個和藹可親的普通人,他幾乎是與長工們同吃同住同生活,他關心別人,和藹可親,不分貴賤,平等相處,不擺架子,生活在群眾中間。
中洪為了醜化劉文彩,把他塑造成一個窮奢極欲過着荒淫無恥帝王生活的惡霸,特地化了三萬斤大米在劉家一間普通客房中,打造了一台金壁輝煌的「龍床」。當年打造「龍床」的木匠李福清和雕花匠李慶安至今已是九十多高齡者,他們說:「劉文彩49年就死了,他哪裏享受過這個『龍床』啊!」
中洪除了打造「龍床」外,還在劉家保姆和劉元貴住過的房間打造了一間劉文彩「珍寶室」,化費巨資大量採購珠寶當作劉文彩炫耀奢侈生活的物品進行展覽。耗去相當於一萬個農民一個月的血汗錢。還打造了一間劉文彩的「逍遙宮」,說是他玩弄女性的地方!在《收租院》電影中,竟說劉文彩強姦過七、八百個婦女,央視副台長陳漢源大概把姦污千名少女的當代毛皇帝醜事栽到劉文彩的頭上了吧!
在莊園大門口,還陳列着一輛福特轎車,《解說詞》說它是劉文彩為了自己的轎車能開到成都,就修了大邑到成都的公路。而事實是修公路時間是1943年前後,1948年劉文彩才買了一輛二手的吉普車。展出的車從來不是他家的車。安仁雖有過這樣的車,那是1946年劉文彩向西康省政府要的,供「文彩中學」的校長和教師們用的,他本人從未用過。
他們還把原來好好的「僱工院」打爛,把僱工住屋拆建降低高度,使其變得像淒悽慘慘的景象,打造出一個長工受奴役生活在條件惡劣的環境景象。
正當主管部門用3萬斤大米打造一架「龍床」栽到劉文彩頭上時,莊園後面的貧下中農正在死亡線上掙扎着。現年90歲的老貧農廖桂英當年全家15口人就餓死了一半,他的大伯子劉元安一家5口全都餓死。老貧農劉丙南一家死得最少,也死了2個人。
中洪當局為了達到專制統治的目的,所有的卑鄙手段都會使用,所以才眼睜睜的看着百姓活活地餓死而不去救助,卻為了打造這台並不存在過的「龍床」而耗盡民脂民膏!
誰最好?誰最壞?不是一目了然嗎!
那麼這些長工們在劉文彩家中是怎樣生活的呢?還是聽聽這些長工們是怎麼說的吧!
「劉文彩一家的生活在富貴人家中應當算是很儉樸的。」總管家薛疇九說:「劉吃菜都不大捨得,上街都未進館子裏炒過菜,儘是家裏喊廚子去做。家裏臘肉是終年不斷,其他就未吃啥了。」
「劉文彩生活簡樸,他衣着樸素,飲食簡單,長年只吃三樣菜,一是回鍋肉,二是煮回鍋肉的湯加青菜,三是時令蔬菜。」
「劉文彩對人非常隨和,對長工非常好,從來不罵長工,重話都沒有,誰都可以給他開玩笑,幹活也很輕鬆,下午沒事就到街上玩或打牌,有時劉文彩還去看長工們打牌,甚至與長工一起玩牌。」
長工伍志宣說:「他對窮人好得很,很關心我們。我和他打牌,他說,贏了算你的,輸了算我的。我們家裏吃不起飯找到他,最少都要送我們一斗米,還要給臘肉。安仁叫花子多,都是外地來的,安仁本地沒有一個叫花子。為什麼外地來的叫花子多,劉文彩善良,都給吃的,就來得多。」
這裏應該特別的提一提:賭博贏了算你的,輸了算他的,所以與劉文彩賭博打牌永遠只會贏錢不會輸錢,這大概是世界賭博史上首創吧!
還有與劉文彩做買賣也永遠只會掙錢不會賠本,這大概是商品交易中的一種首創吧!
三十年代,劉文彩剛從宜賓帶着大批財富回到老家,就鼓勵鄉親們經商致富。當時安仁鎮只有一家菜油作坊,他問老闆有多少庫存,老闆說有二十大缸,每缸兩百斤。劉文彩當即全部把油買下,之後油價就漲了,他又把這四千斤的油全部白白送給了油房老闆。劉文彩說:「我就是要獎勵那些經商致富的人」。以此給鄉民灌輸商品意識,致富意識。
還有與劉文彩往來永遠只佔便宜不會損失!這大概是人間往來的一種首創吧!
1940年前後,劉文彩為了給弟弟劉文輝建立一個小院接待賓客,看中了鄉民羅世維的房地,經過商量後,他把自己的一套新修的多了一倍面積的房屋跟羅世維換。二十多年後,中洪當局準備以這個體裁來編造一個劉文彩霸佔民房的故事,動員羅世維做造假宣傳員,進入「家史演講組」之中,遭到了羅世維的堅決拒絕。
劉文彩做這種倒賠本的事太多太多了,在興建文彩中學時,凡是規劃區內拆遷戶的房子、田地,他都是用一倍條件來換取,他用兩間房子換人家一間房子,他用二十畝田換取別人的十畝田。有一次有戶人家是十畝田,他應該用二十畝田去換,但是發現家裏的田契只有一張四十畝的,於是把四十畝田都送給他了。
「劉文彩家養有許多雞,長工們經常去拿幾十個蛋來煮着大家吃,劉文彩從來不說他們。」
陳發洪說:「我們家裏糧食接不住時,劉文彩開個條子叫我們去擔米回家,不要錢。」
龍萬富說,「在劉文彩家當長工吃得好,長工和先生(管家)同桌吃飯,三天一個小牙祭,七天一個大牙祭。小牙祭就吃雞、鴨、鵝,大牙祭就吃豬肉,肉隨便吃。(鳳凰衛視《大地主劉文彩》中劉文彩之子劉元華稱一月兩次牙祭,初二與十六)每月的工錢是60斤大米(毛時代人民公社裏的農民,一個全勞力每月不足3元錢,最多只能買到12斤平價米)。」
當年劉家廚師劉玉林說:「劉文彩對人很好,遇見他(指劉文彩)家忙的時候,劉文彩就下廚來對他說:切厚點,沒關係。」(估計是肉切得厚點吧!)他還說:「劉文彩沒吃過啥子,都是一般的。幫劉文彩兩年,他怎麼做劉文彩就怎麼吃,從沒說過他。」
而中洪當局卻要這些長工們泯着良心說劉文彩剝削欺壓他們,逼得他們家破人亡,於是衝出這座人間地獄,起義造反投奔了洪鏟钂找到了紅太陽。《收租院》的解說詞這麼寫着:「受苦僱工齊反抗,罷鐮鬥爭氣勢昂。揚眉吐氣眾長工,膽戰心驚活閻王。」「歷盡千辛闖險阻,掙斷枷鎖出牢籠;找到救星洪鏟钂,陽光燦爛紅旗舞。窮苦奴隸得解放,堅決革命緊握槍;毛主席思想放光芒,五州四海紅旗揚」
這些精神變態症與妄想狂人胡編亂造的詞能讓這些長工們信嗎?所以他們頂着巨大政治壓力,打死也不為官方充當訴苦明星!
劉文彩為農民做好事道不盡說不完
在劉文彩莊園《收租院》陳列館門口兩旁,各寫有五個大字「地主收租院」,「窮人催命關」。裏面的展品把劉文彩的莊園描寫得像座人間地獄,劉文彩像個活閻王,每一次交租農民就像進入鬼門關一樣。那麼事實又是如何呢?也還是聽聽劉家的佃戶們農民們是怎麼說的吧!他們說起劉文彩為鄉親們做的好事,幾天幾夜也說不盡道不完!
《收租院》解說詞說:劉文彩的鐵板租把農民一年的收成剝削得乾乾淨淨,「劉文彩的『鐵板租』每畝高達一石七八斗,超過了正常年景的產量,不管天旱地澇,雷打火燒,租子一粒不能少。」還說「那時侯,有多少人因交不起租,而被逼迫賣兒賣女、妻離子散;又不知有多少人在這鬼門關里,被弄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交租真的像交鐵板租,每畝高達一石七八斗嗎?
鳳凰衛視《大地主劉文彩》一片中,記者曾問當地老人:劉文彩收的租谷多不多?老人的回答:「不多」,接着又問每畝交多少?老人回答:「一石」。但是這一石只是一季的一石。四川是兩熟地區,一年收穫兩季,一季是穀子,一季是麥子,一畝穀子就是收一半交一半,一半就是一石,其餘麥子及田坎上種的蔬菜、豆類都是由農戶自得。這能算是鐵板租嗎?
交租真的像過鬼門關嗎?
所有的農民都說:去交租髙興得很,那裏擺了十幾張桌子,交了租後湊齊一桌八個人就開飯,上的菜都是大盤大碗的紅燒肉回鍋肉,吃得滿嘴都是油,隨便吃飽,有人還把孩子帶去一起吃。剩下的還可端回去給婆娘娃娃吃。好些人為了來此多吃一頓,就把一次可以交完的穀子分兩次交。
送糧的人能吃到一頓飽飯一餐美食,這是劉文彩的首創吧!
劉文彩真的是放高利貸,巧取豪奪,榨乾農民每一滴血汗嗎?
陳子云姐夫有一年賭賭輸錢過不了年,父親就帶他姐姐去找劉文彩借三斗米回家過年。劉文彩說借啥子借嘛,你在我這裏拿五斗米去就是了嘛。就這樣白送給她五斗米。
劉文彩真的把交不夠租的人賣去當壯丁嗎?
當地人卻說劉文彩保境安民,誰家有人被拉了壯丁,只要告訴他,他就一定去給你討回來。
劉文彩真的每年收租都要登報貼告示,限期將租子送到嗎?
事實卻是每到年底劉文彩都要給窮人開倉施米給農民發錢,他到處張榜貼告示,通告窮困鄉親在規定時間到各處糧倉來領米糧,時間長達兩天,一直到倉米發完為止。
劉文彩逼租逼得窮人把小孫女賣去當丫頭,把窮人逼得家破人亡,離鄉背井逃亡他鄉。《收租院》裏塑有一個交租的小女孩,說「她小小年紀,就已經感到這個世道的罪惡與不平!」
但是事實卻相反,每當青黃不接收成不好的時候,劉文彩就要過問有哪些人家過不去,就要去扶人家一把,把溫暖送給別人。
劉汝明佃了劉文彩2畝3分田,因為家窮,五年未交過租,劉從不過問。陳子云家有一年交不起租,這一年就被免了。王子全佃劉文彩10餘畝田,因為收成不好,劉文彩就把10餘畝田全部送給了他。
唐紹軒佃了劉文彩十餘畝田,有一年天干收成不好,黃牛又被土匪搶去,家裏交不起租,他在路上遇到劉文彩時就跪下求他。劉文彩把他扶起來說不要跪,有亊站起來說。聽了此事後他說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過了幾天,劉文彩還買了一條黃牛送給他。給其他五家窮人也送了牛,都不收錢。
曾有一個走投無路的農民找到劉家,劉文彩親自出來接見他,他說他窮得連年都過不了了。於是劉文彩叫家人拿出很多年貨給他,足夠讓他全家人好好地過一個年,臨走時,劉文彩還告訴他:「這樣還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過了年再來找我,我重新給你想辦法。」
無論是青黃不接還是天災人禍,劉文彩都要傾其所能向別人伸出援助之手。這類事實在是太多太多了,陳克明、劉清雲、傅世語家的房子都被火燒過,都是劉文彩把他們房子修好的。
官方宣傳材料稱劉文彩專放狗去咬那些討飯的人。
鳳凰衛視主持人在《大地主劉文彩》一片中講了個笑話,說是有一個要飯的老太婆討飯討到劉文彩家時,劉家就放出狗來咬這老太婆,於是這要飯的就逃。此時她的肚子裏憋着一泡屎,她想這屎是大糞是肥料,是莊稼的一枝花啊,我不能把它拉到這裏,肥了劉文彩的田。於是她逃啊逃啊逃,逃了一天。她停了下來想拉這砣屎。又一想不行,劉家占田數千畝,方圓幾十里田地都是他家的,所以還不能在這裏拉屎。於是她又走呀走呀走,走了一個晚上。到了白天,她想這一回應該不是劉文彩家的田了吧,就立刻下蹲拉出了這泡屎。不料人家告訴她,這裏還是劉文彩家的田,氣得要飯的老太太一下跳了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