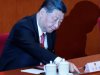我在加州大學開課,有不少學生是中國大陸來的。上個學期我教過一門「中國文明史」,一百五十個學生註冊,幾乎一半是中國同學。有的念得很認真,考得也很高,但相當一部分是不太認真的,似乎是想「混」一個容易的學分(「我是中國人,何必上課去聽美國人對『中國文明』的印象?」)。考試的時候,我發現這批學生特別善於互相幫忙,用手機或平板電腦把答案傳來送去,甚至集中在講堂的一個角落裏一塊兒研究小考的正確答案應該怎麼寫。
不問對錯,只問得失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正確答案」的態度。他們衡量一句話的價值,用的好像不是一個真與假的標準(「這句話是真的還是假的?」),也不是一個道德標準(「我應不應該寫下這句話?」)。用的標準是「這麼寫是否對我有利?」似乎認為把小考分數弄得更高是「聰明」的行為,上大學的目標是學會用聰明的方法。
作弊不是中國大陸學生特有的問題。哪兒來的學生里都會出現這個現象。但中國大陸學生還是有特殊性。要是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來的學生,很少看到那種「作弊作得成功就是本事」的態度。港台同學要是作弊,更會覺得是難為情的事情。
因此我們可以問:為什麼?我覺得我們不要輕易地責備中國大陸來的學生。他們的社會背景不同,而且他們成長的語言環境早在他們出生前已經設定好了。
回頭看上個世紀的50年代。任何社會有「官話」與「日常話」的區別,但中國共產黨在50年代推廣的政治語言是個極端的例子。當時,不管你恨不恨地主,你得學會在鬥爭會上大喊「打倒地主XXX!」。萬一喊錯了,大會把批評的矛頭轉向你自己,你不但得承認錯誤,還得「感謝黨對我的教育」。這是你的「表現」。日子久了,怎麼對付官方語言變成了一種獨特的技能,或說是一種語言遊戲。衡量一句話的價值的標準變成:下棋下得對不對?語言處理得聰不聰明?「真」與「假」不是標準了。到了60年代的下一半,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進一步惡化了語言的墮落。中國傳統的「儒家」價值觀把尊敬長輩和認真讀書放在首位:孝順父母,聽從老師。但毛對年輕紅衛兵說「造反有理」,鼓勵他們批評父母(「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侮辱老師,甚至打死老師,這樣就摧毀中國社會的最深最基本的價值觀。到了文革,不只是「真」得讓步給「實用」;連「道德」也得讓步。「利」壓倒了「義」。不問是非,不問對錯,只問得失。
出了門效忠政權,關了門罵習近平
80年代的「改革開放」之後,社會理想稍微能夠恢復一點,但在六四屠殺和鄧小平南巡以後,公共價值觀只剩下了賺錢和民族主義這兩條。「義」還是輸給「利」。宗教(佛教,基督教,法輪功等)的再興起說明中國老百姓還繼續嚮往人本的價值觀,但這些信仰都處於官方價值之外,甚至是官方打壓的對象。
到現在,官方的語言還擺設在社會的表面上,不管多麼虛假,老百姓只好配合它,必要的時候在「語言遊戲」里下一招棋。不少人注意到了當代中國「精神分裂」的現象。關了門罵習近平,出了門效忠政權。對西方呢,罵它是霸權主義,想壓制中國的,同時盼能有綠卡。
前幾天在中國的微信上有人發了這麼一條短訊: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在加沙地區旅遊或是務工碰到了危險,在暫時無法聯繫到咱們國家的大使館時,你會選擇向以色列政府求助還是向哈馬斯求助?你的選擇代表了你最真實的立場。」
馬上有網民回答:「很大一部分中國人會向以色列當局求助,但永遠站在哈馬斯一邊。」更有人補充說:「就像很大部分中國人會送子女去美國留學,但永遠站在俄羅斯一邊。」
這不是簡單的「自我審查」問題。這種矛盾心理的兩頭都是真實的。但我們也可以問哪方面的認同是更深的?我有個很出色的中國朋友(不便透露姓名)說她的同胞考慮自己的得失是「無條件」(unconditional)的,效忠政權的價值觀是「有條件」(conditional)的信仰。換句話說,哪天官方的價值觀與個人的「得失」利益沒有關係的時候,價值觀就垮了。我覺得這位朋友的話說到點子上了。
做一個簡單的「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吧。要是習近平明天出來,站在中南海門前宣佈(他絕不會這麼做,這只是「思想實驗」而已):「我決定下台,而且從現在起,我們要設立民主制度,有普選,憲法,人權,等等」會有多少老百姓上街抗議,說:「不行,不行!你們共產黨多少年幹得這麼漂亮!你習大大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那麼寶貴!不能下台!不行!」?
要是站出來這麼說的人不多,那我們就得面臨一個事實:中國人效忠中共是「有條件的」還是「無條件的」?母愛是無條件的,但「愛黨」有條件。條件一走,愛會繼續嗎?
習近平知道老百姓對他的「愛」是有條件的嗎?肯定知道。要不然為什麼那麼怕事?那麼偏執狂?那麼願意花大筆錢在「維穩」工作上?
我的意思不是說政權脆弱。所有的媒體,警察,軍隊,大錢都控制在中共的手裏,不能說它脆弱,而是一種堅硬的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