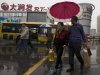摘要:故事正在向相反的方向演變:裁員不再是件壞事,更像是一場等待「上岸」的狂歡。
在圖書館枯坐了兩個月後,李岩終於讀完了一本書。被裁員後的這些日子,為了免於被父母發現破綻,他每天早上假裝出門上班,步行十幾分鐘到家附近的圖書館看書。
李岩曾是許多人羨慕的對象。過去十年他一直在互聯網公司工作,是典型的行業紅利受益者。今年初,伴隨着裁員和上有老下有小的現實狀況,讓他一夜間成為了媒體口中「最慘中年人」代表。
但回憶起被裁員的那一刻,李岩只感到「如釋重負」。畢竟,入職這家公司後,李岩就發現負責人當初所畫的宏大藍圖難以實現。沒有人告訴他應該做什麼,這種混沌和模糊是大廠常態。幾個月後,李岩在煎熬中等到了裁員的結果,這期間,招聘他的負責人甚至早已離開公司。
當光環和虛榮不再,越來越多人正「認清」互聯網和大廠的本質。
一位字節跳動員工告訴鏡相工作室,她所在的業務線強調績效,每季度會根據績效末位淘汰。以前她一天只需要審核400條內容就能達標,現在需要審核800條。
另一位互聯網大廠員工楊倩也有同感。她本是業務線裁員的倖存者,但現在內心卻無比期待離開。因為工作壓力,她今年病了好幾次。她說很多和自己一樣身心俱疲的人,都把裁員當做一種被迫休息。「也是一種解脫。所以當大規模裁員的時候,我覺得大部分人心理感覺是靴子終於落地了。」
始於2021年的互聯網大廠裁員現象,經過劇烈且持續的兩年時間,2023年是人們對大廠職場祛魅的一年。小紅書上,「求裁員,求N+1」的帖子層出不窮。幾年前那些教人如何升職加薪的內容漸漸沒了熱度,這屆年輕人甚至中年人,對職場也已經沒有「執念」。
鏡相工作室在訪談數位親歷裁員的大廠員工和獵頭後發現:儘管寒潮還未結束,但人們似乎已經學會了與這種狀態共處。
從最初的恐懼、茫然、無力、無奈,到現在的接納,甚至期待。整個裁員故事正在向相反的方向演變:這似乎變成了一場許願。裁員不再是件壞事,更像是一場等待「上岸」的狂歡。
等到靴子落下的人
當裁員的痛感血淋淋地擺在獵頭Rachel面前,她也一度感到惶恐。
Rachel是擁有5年從業經驗的資深獵頭,她習慣將大部分候選人都處成朋友。2022年,互聯網大廠裁員兇猛,她經常會接到被裁員的候選人打來的電話。「他們會問我怎麼辦?接下來的時間找不到工作怎麼辦?你快幫我找找有沒有合適的工作?」答案其實是很難有合適的崗位。
在她的觀察里,裁員潮剛開始時,候選人往往羞於提起自己是被裁掉的,但這一年來,這些候選人都會主動和她說明。
「所有人都需要一個被市場教育的過程。」獵頭林集告訴鏡相工作室,眼下候選人的預期和姿態正被不斷拉低,從趾高氣昂、不屑一顧到急迫,「不挑食」地去找到一份工作。
獵頭韓暘遇到過很多人,「一開始給100萬不願意去,給70萬時說想等一等,等到50萬甚至50萬以下,後來就直接不工作失業在家。」
上述獵頭總結,有三類人很容易被裁:一是業務線裁撤,波及業務屬性比較強的人;二是末位淘汰,績效不好的人;三是年齡到了,又沒有很好上升空間和潛力的人。

獵頭Rachel為這些人的危險度劃分了等級,其中互聯網中層是大廠裁員的高危人群,也是就業市場中最難找工作的一群人。「今年大廠專家崗位都不給我們做了,只會給我們一些高級崗位,對美團來說是P10以上,對阿里來說是P8/P9職級的崗位。」她認為,造成這一難題的根源是互聯網大廠對降本增效的追求。
獵頭韓暘也印證了這個觀察:互聯網大廠把更高比例的資金傾斜到對高職級人才的狩獵。
這無疑縮小了被裁員下來的中年人的選擇空間和就業難度。
身為30歲的女性,高麗想找到合適的工作很難。她在BOSS直聘上投遞五十幾份簡歷,只收到5個面試。她常常因為年齡被拒,去面試會被追問「有沒有結婚,打不打算生孩子。」談薪環節也不如人意,2萬的工資直接被砍到1萬。
即便不是被裁掉,一年前主動從某互聯網公司離職的39歲田宇,在做了一年自媒體後想重回職場也無比艱難。投出去的簡歷都石沉大海。
他曾在知名媒體就職數年,後來轉戰互聯網大廠。田宇說,在他收到回復的郵件中,大多是「抱歉年齡超了」「抱歉你的簡歷跟我們崗位不符合」。
「說實話這個世界還挺殘忍的,」Rachel的候選人給她發過一張截圖,是一個網上的討論「有人40歲還入職字節的嗎?」這種時刻她會格外感傷。雖然對互聯網大廠不感興趣,也從沒考慮入職大廠,但她也會在那一刻陷入焦慮與無助,「我也擔心40歲的時候是不是像他們一樣被時代拋棄了」。
求職不僅為難中年人,對年輕人也不再友好。28歲的郭頌被一家國內最大規模之一的互聯網公司裁員後,入職了廣州一家小型互聯網公司,總包降薪30%,儲蓄額度降低60%。她想過再回到大廠,因為那裏體制更完善,有光芒,自己的虛榮心還在。但面過字節、快手、小紅書等公司後,都沒了下文。
和大廠說拜拜
高麗曾短暫地待過一家互聯網教育大廠,因為試用期沒過被迫離開。
她有屬於自己的職場高光時刻。她做過四年互聯網運營,在前公司搭建的方案至今仍是可以被直接使用的模版。在之前的崗位中,她永遠是被獎賞的那一個,獎盃和獎狀塞滿一柜子。而否定的聲音伴隨着她進大廠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沒有多餘時間給她去適應,她需要直接上手就開始工作。在她摸着石頭過河的階段,領導總是會說她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
「出了一點點問題,就會馬上找到我談話。」正面評價從來沒有,她只能反覆熬夜更改方案。等到轉正環節,「我傻傻地以為我能轉正。最後的理由是,答辯數據太差了,保都保不住。」

高麗的獎盃。圖源受訪者
高麗始終後悔,如果當時讀過勞動法,一定會去爭取N+1賠償,可能一個月或許半個月。但當時的她像一個沒有得到老師認可的孩子一樣哭得泣不成聲。最終還跟領導說「是我自己的問題,謝謝你的照顧。」
離開後的高麗認為看清了大廠的冷酷,也開始反思大廠體系。她認為自己並沒有大家所說的不堪,而是「項目本身也沒有那麼高效,任務太多,擠壓我的時間,讓我想不到那麼好的創意了。」
楊倩也覺得這些互聯網公司已經不可避免有很多大廠病。「它的企業文化和試圖宣揚的東西在日常執行中已經做不到了。」更重要的是,互聯網大廠不是一個能久待的地方。「你的身體和心理都無法承受當前的工作節奏,對中年人和有家庭的人非常不友好。」
此時此刻,幾乎所有人都想要逃離。畢竟即便是裁員風波下的倖存者,也難有幸福感可言。
30歲的魏可早在去年就有回鄉打算,原本計劃今年年底離職。2022年春節前三天,在得知鄰近工位的三個同事主動申請被裁且成功後,他也開始了「謀劃」。直到今年8月,魏可終於抓住了機會,他主動要求被裁員,順利拿到賠償,如願離開了公司。
同樣被裁員的郭頌,在收到通知後,第一時間就分享給了朋友。「朋友們,我被裁了,我拿錢了!」相比於朋友的擔心,她的第一感覺是興奮。她想要開始旅遊、出去好好放鬆。
期待被裁員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郭頌在那家互聯網大廠經歷了一次轉崗,轉崗後她並沒有那麼喜歡那時的工作,「在裏面獲得的成就感不是很強,如果被裁了的話,正好可以換一個自己更感興趣的方向。」裁員某種程度上給了她勇氣去嘗試之前不太敢嘗試的東西。
和郭頌相熟的另外一位同事也有計劃回老家,一直期待被裁,郭頌形容這位同事已經渴求到在社交平台發帖「求求了」的程度。
比起年輕人的灑脫,中年職場人多了幾分無奈。36歲的楊倩時常會和同事聊到這些,但交流並不會緩解焦慮,有時還會加重焦慮。大家都想着自己太不容易,中年人很累。「但其實這不是一個絕對焦慮或絕對平衡的狀態,它可能隨時交叉進行,有時候覺得好像裁員靴子落地了休息一下,然後又想起未來市場不太穩定,有各方面不確定性。」
消失的紅利
對很多人來說,大廠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的存在。因為身處其中光暈實在耀眼,讓人來不及洞察光芒的另一面。正如那些搭乘過互聯網上升通道的人們很難接受一個事實:所有的成功都是時代的紅利。
不少候選人曾希望拿着大廠經驗到中廠收割一波股權,期待上市後的指數級變現,「但很不幸的是這兩年發生什麼大家都看到了,港美股都上不了,造富夢破滅了。」獵頭韓暘說。
「過去經濟好的情況下,互聯網大廠需要更多人去支撐。現在環境變化了,首先判斷的是人效。」51獵頭聯合創始人朱聚鵬,從他二十幾年的從業經驗分析當下互聯網裁員潮。
過去三年,狂歡戛然而止。無序擴張被按下暫停鍵、融資燒錢難以為繼等各種因素疊加導致越來越多的企業不得不「棄車保帥」。那些短期內無法盈利,自己造血的業務和人註定將被砍掉。
華東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研究所的顧楚丹、楊發祥曾以字節跳動作為案例,訪談了多位內部員工。研究表明:極少互聯網企業的裁員符合「經濟性裁員」要求,一些互聯網企業還有較強的盈利能力,但仍在削減工作崗位,「裁員已經由短期的人事削減工具轉變為組織戰略變革的重要手段,不管職位高低都有工作的不安全感」。
一面是企業端對「人效」、「盈利」的迫切追求,一面是人才端儲備供過於求。如此錯位的背景下,只有一類人會相對安全。Rachel總結為「核心業務的人永遠不會被裁」,韓暘認為「擁有不可替代的技術,對前沿技術應用很有理解,專業能力不離手」的人即便在被裁員之後也很好找到工作。
裁員的雪花甚至也落到了韓暘自己公司。他是一家800人規模的獵頭公司高級合伙人,他描述在北京公司看到的場景:兩間辦公室合併成一間,人一個接一個走掉,辦公室空位越來越多,800人如今只剩500人。在互聯網紅利褪去後,那批因為趕潮而招進來的擅長互聯網方向的獵頭也散去了。
對於韓暘來說,這已不是他經歷的第一個周期。他曾經歷過外企在國內蓬勃到退場,互聯網繁榮到暗淡,他覺得任何行業都有波峰波谷,在漲潮時去投入去學習,在退潮時尋求轉型。
當然,一個令人欣喜的變化是,中國互聯網經過過去20年的發展,已經脫離了野蠻生長,正在向「精英化」轉變。放到更大的背景下,互聯網行業的收縮下降不過是經濟循環的一部分,對於普通人來說,也許更應該關心怎樣才能穿越周期。
只是歷史只會不斷重演,而人們永遠不會吸取教訓。「現在互聯網的紅利告一段落,這些人又開始湧向晶片和新能源汽車。」一位獵頭這樣感嘆道。

陣痛之後
當裁員的殘酷預期被打破,「先被裁的人先享受人生」似乎正在成為一種共識。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試圖掙脫這種束縛。何森2020年畢業,目前在一家短視頻互聯網大廠工作。即便他明白,裁員的風波怎麼也還輪不到自己,但他不得不為了不在35歲之後成為互聯網大廠的棄子而未雨綢繆。
「經歷這些事情後會發現公司穩定性不強,你按部就班去做好工作,最終善終的可能性很小」。他一邊認真工作,以便在公司獲得晉升,積累資源;另一邊他把熱情放到更多他處:支教、做公益組織。
在大廠工作的何森發現大廠穩定性並不強,他現在把熱情放到做公益等事情上。圖為何森支教學校的孩子們。
轉正失敗後,高麗覺得考公考編會是出路。在互聯網在線教育公司時,總感覺無時無刻不在拉新、抓續費。考上家鄉教師編,是她逃離互聯網大廠後的美好幻想。
一些突如其來的暴擊和重創後,人們往往會調低自己的心理預期。
在經歷裁員風波後,「穩定性」成了李岩篩選公司的優先級標準。在圖書館枯坐了兩個月後,李岩現在已經入職了新公司,雖然整體降薪30%,但他感覺到被老闆信任,能負責很多事。
「職級往上升,學到新東西」曾是他過去的堅持。現在他越來越覺得與其讓市場按照自己的規划走,還不如找一個稍微舒服順心一點的地方待着。人到中年,最後發現不過又回到了原點。李岩也想開了,「如果回頭再選一遍的話,大概率還是一樣」。
心理諮詢師提供了關於裁員的另一個視角,在諮詢師周夢媛眼中,裁員可能具有積極意義。這讓人有了一個探索自己的機會:我到底在做什麼?我想要做什麼?我還能做什麼?生存焦慮是真實存在的,但失去後也會發現「原來你想像中性命攸關的事情或許沒那麼重要。」
周夢媛正是從金融行業轉行到自由職業心理諮詢師。雖然工資降低也不穩定,但她覺得「人們真正想要的工作和生活,會在做的過程中去體驗,而不是靠想像。」
Rachel今年30歲,再過幾年她想要辭掉獵頭工作去干自己的事情。她時常和候選人說「如果你沒有經濟壓力,想要獲得快樂並且能承擔因為快樂導致的空窗期,那就去選擇快樂。」
等到裁員的靴子落地,楊倩已經準備好在找新工作時可能面臨的降薪和降級。「畢竟差不多報酬的崗位就那麼多。」現在面對裁員她越來越感受到「它不是個人原因,而是一個時代的陣痛。」
陣痛未必是件壞事。也許人們最終會意識到,裁員不過是漫長人生中的一個節點。比如高麗,被互聯網在線教育大廠裁員後,她有一個長遠又足夠美好的目標:她想回到家鄉,一個華北平原的小縣城,考上教師編制,做一名真正的老師。她會把自己闖蕩北京的經歷分享給像她一樣的孩子,讓他們少走彎路。至於她自己,「應該把一些激進的想法放一放,然後平平淡淡組建一個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