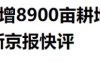2006年,在胡杰帶着講述文革早期的死難者、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故事的紀錄片《我雖死去》到香港放映時,我第一次採訪胡杰。此後這些年,因着不同場合的採訪或是電影節的機緣,我總有機會見到他。他長著一張方正英武的臉,大絡腮鬍子,雙目炯炯有神,卻永遠謙恭低眉,開口說話時,神色誠懇得讓人難以拒絕。這麼多年,他的相貌沒有什麼變化,好像歲月的風霜在這個孤身求索的男人身上留不下痕跡。
2014年夏天,他帶着新的紀錄片《星火》來香港的幾個大學做放映,此時,距離《尋找林昭的靈魂》面世已經十年。此時,距離《尋找林昭的靈魂》面世已經十年。在《星火》裏,他果然找到了和林昭一樣的一群從不曾屈服、卻被歷史殘酷地抹去痕跡的年輕人。
《星火》是一本地下油印刊物的名字,1960年出版第一期,印了30本,發刊詞寫着:「放棄幻想,準備戰鬥!」它的創辦人是一群被打成右派的大學生。他們在甘肅的窮山溝里勞教時,見證了遍佈中國鄉村的慘絕人寰的大饑荒。在那個城市裏還在歌頌畝產萬斤、超英趕美的大躍進神話,而向城市逃難的道路都被封死的年代,這些能說、能寫的大學生是大饑荒極少數的知識分子見證者。有學生上書中央,卻立刻被抓了起來。嚴酷的形勢下,其他的夥伴把深切的痛苦和反思匯成了《星火》。學生們說,他們豁出去了,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如果你有機會看到這本薄薄的、手寫刻印的小冊子,一定會驚訝於在50年前中國濃黑得化不開的精神世界裏,會留下這樣犀利的文字。《星火》裏的政論,直指對人民公社制度乃至整個共產政權的反思,提出中國共產政權的本質是與納粹同構的國家社會主義,而學生們要追求的則是民主社會主義。林昭的長詩也經由同學介紹,刊登在《星火》的創刊號上,《海鷗──不自由毋寧死》:「我們犯下了什麼罪過?/殺人?放火?黑夜裏強搶?/什麼都不是——只有一樁,/我們把自由釋成空氣和食糧。」
《星火》只活了幾個月時間。第二期已經編寫好的雜誌還沒有來得及付印,20幾名星火成員便被集體抓捕,作為「蘭州大學反革命集團大案」,被判刑15年到20年。少數幾人被槍決,比如張春元、林昭。張春元的未婚妻、《星火》成員譚蟬雪在度過了14年牢獄生涯之後,出獄便開始盡全力收集資料、追索這段歷史,用了21年時間寫成《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紀實》(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2月出版)。譚蟬雪說,歷史血的腳印,必須要記得,必須要留下來。
曾在拍攝林昭的故事時訪問過譚蟬雪的胡杰,則在知道這些線索後,從2008年開始根據這些線索,重新尋訪《星火》的當事人,2013年製成了紀錄片《星火》。
距離拍攝《尋找林昭的靈魂》已經過去了15年。胡杰當年曾訪問過的一些重要當事人,也是《星火》的見證者,今天再想訪問時,卻已經不在人世,或者身體蒼老得無法再面對鏡頭。歷史就這樣一分一秒地流逝,啞聲,無法復原。這正是胡杰一直在悶頭趕路的原因。他偶爾也抱怨,這麼重要的事情,為什麼同路人那麼少?但抱怨歸抱怨,腳步並不停下。
十幾年過去,再回看《尋找林昭的靈魂》開頭那段導演獨白,才意識到,那不只是影像語言的選擇,而更是胡杰本人對自己和歷史的一次交付、一個誓約。「這個故事使我最後作出一個決定:放棄我的工作,去遠方尋找林昭飄逝的靈魂。」經歷了時間的考驗,這個誓約,才顯出它真正的力量。
以下是我h與胡杰的訪談摘要:
你為什麼決定持續地拍歷史題材?
胡杰:中國1949年之後的這一段歷史太重要了,是人類歷史的一個活化石。這樣一個極權制度,它的所有行為方式,都是人類所經歷的很新鮮的東西。那些在其他國家已經被宣佈是罪惡的東西,我們的歷史依然在沿着這條路,用一種強大的方式在往前走。我覺得它的重要性在這裏,它給人類一種逆向的行動案例。今天的每一個縣城裏都還藏着非常慘烈的故事和有價值的東西,不管是反右,還是之前的各種土地改革、鎮反、大躍進、大饑荒、四清、文革,甚至是文革之後,所謂的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但為什麼沒有人,或者這麼少的人去做?我覺得挺不能夠有一個很恰當的解釋的。很多年輕人說他們想在紀錄片的視覺上、趣味上進行探索。但是他們碰這些題材。他們是不明白自己有一個更沉重的、更重要的歷史嗎?還是怕觸碰這個東西?我不是太清楚。我真的覺得太重要了。
的確,不僅拍攝這些題材的人少,而且你也會經常被批評為是表達方式落伍、影像泛道德化等等……
胡杰:所以我覺得這麼多年以來,中國的文學、藝術這一塊真是出問題了。過分的商品化,過分的迎合了時髦。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現代,他們現代的目的是什麼。是要批判嗎?還是僅僅想要外國人、商人喜歡?他們的作品裏有沒有情感,有沒有愛,有沒有基本的價值,有沒有對人類命運的基本的關切?我覺得這是挺重要的。也許我的觀點確實老了。他們已經走到一個超自然的狀態,我還停留在對土地眷戀的、19世紀式的情感上。但是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還沒有過去,我們對土地懷有情感的時代還沒有過去。盲目的世界旅行者的身份不適合我。我不是一個世界的公民。──你知道嗎,關鍵是如果我們的祖國,成了美國,我可以去當世界公民。關鍵它現在還是一個極權的、無意識、連自由都沒有的(狀態)。馬克思說如果沒有出版自由、任何自由都不要去談,這是共產黨老祖宗說的話。我們現在過香港海關,拿一本買的書都怕被查到。我們的時代還沒有過去。在這個時代,我覺得最重要的仍然是一個精神上的尺度,如果沒有了這個東西,我覺得不管是什麼藝術家,都是很窩囊的。
你自己從歷史上去尋找這種精神尺度,就是從林昭開始的嗎?
胡杰:我有一個很傳統的觀念。我老是認為俄羅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由一批有精神高度的藝術家造就的,比如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這一代人。他們是有精神高度、有精神尺度的人。後來我發現了林昭。發現了林昭後,我覺得她是和那一代人有同等高度、同等精神素質的人。這就變成了我對生命的標準。後來在拍攝紀錄片的時候,我越來越發現,其實是有這麼一批人的,比如星火中的張春元、向承鑒。他們使我們對民族有了精神上的光輝,不會再是一個別的東西了。我最近的《星火》,也是想表達說,不是沒有人說話然後大饑荒發生了,而是有人說話,只是被全部鎮壓、殺掉或者關起來了。這就讓人感覺到,那一段歷史上,並不只是一段恥辱的歷史,其實還有那麼多中華兒女為之去拋頭顱、撒熱血的。而且我覺得,這個民族可以生存不滅,就是因為有這樣一些人對於罪惡不低頭,他可以被打敗,卻不可能被戰勝。林昭就是這樣的人,你可以把她槍斃,但你不可能去戰勝她。我覺得這個民族是要有這樣的精神,這樣道德的追求的。
正是這些人的光輝,吸引你一直拍下去。
胡杰:是。我們的歷史完全被割斷了,被模糊了,被人為地淹沒了。搞紀錄片的人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更不能以政權的權力的導向來論英雄。我就想通過一系列的紀錄片,將那一代人的英勇,精神上的高拔表達出來。中華民族最困難的時代,在我看來,就是1950年代一直到文革,那不像是抗戰,抗戰時我們有軍隊、有槍,可以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抵抗,但像1957年,他們就是默默地在監獄中去忍受。他們抵抗的是更為強大的敵人,這個敵人就是荒唐。但民族遇到這麼大的災難的時候,那些人還能挺身而出。堅守着自己的良知。你可以不說他是英雄,但我就覺得應當把他們在民族最困難的時候所做的犧牲,給表達出來。這個時候做紀錄片,我覺得沒有別的選擇,就是去研究、去採訪、去拍攝。我先用最樸素的方法去做。後一代人可能不會這麼做,但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像我這個年齡的,急着要做的事情是把這些東西先搶救過來,因為你不搶救,他們就死掉了,沒辦法再復原了。
當你用影像,讓那些已經死去的仁人志士,重新活過來,煥發出光彩的時候,在這個過程里,你會想要和他們說話嗎?你和他們之間,是什麼樣的一種情感?
胡杰:不僅是說話,而且是傾訴,是一種深談。更有意思的是,你不會認為他們老了,他們永遠是那麼年輕,好像永遠那麼勇敢、有智慧,讓你去和他們交流。我在做林昭的時候,一直覺得她就是這麼年輕、勇敢、有智慧,然後潑辣,說話不饒人、帶刺,就是那樣一種感覺。
你自己的經歷似乎根紅苗正,你也是通過林昭,才開始了解那段歷史嗎?「尋找」這兩個字,似乎也是一種對自己的約定。
胡杰:是的。原來我也都是懵里懵懂,一說到反右,就知道是個運動,然後想到小時候家裏鄰居就是右派,但是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是右派。通過採訪林昭的故事,才知道原來反右的時候有300多萬右派,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至少三分之一。在最初看到林昭的稿子的時候,簡直是太震撼了。因為我從來沒看到過這麼銳利的、深刻的、充滿情感的、而又像是茨維塔耶娃的詩歌一樣有張力的文字,來批胖一個極權的政權。而「極權」這個詞,我們當時看了都心驚肉跳的,因為沒有人敢用這個詞,誰要是用了就要槍斃誰的。我看到林昭在獄中多次用「極權」來批判、用血淚控訴這個政權的時候,我當時真是很害怕的。就是這樣去看完了她的東西。看完了之後,我就在想,能不能用紀錄片來總結一下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運動,或者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是怎樣的實踐。然後我開始採訪,在採訪了非常多之後,才明白「反右」是怎麼回事,之後的大躍進、浮誇風、大饑荒,又是怎麼回事。一環一環,災難變得不可避免。當看到了這樣一種情形的時候,你會對社會制度提出疑問,為什麼會是這樣,這個社會制度哪裏出了問題。我是軍人,黨員,在部隊15年,還介紹很多人入了黨。我是一個對於共產黨沒有偏見的人。但就是因為沒有偏見,所以當我進入到歷史的時候,才覺得它太有問題了。我不是因為有刻骨的仇恨才(這麼想)。
你知道,會有很多人說,你在神話林昭,那個年代很複雜,沒有絕對的好人,等等。
胡杰:如果不是我親自去拍的時候,我也可能覺得他是在神話。但是當你去採訪到,這些人確實存在的時候,你會發現這不但不是神話,而且這就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總是有這麼多敢於犧牲、敢於為了自己的良知犧牲的人,所以這個民族她不會永遠腐敗下去。做紀錄片,我肯定有個人的立場和感情在裏頭的。我是站在雞蛋這一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