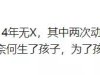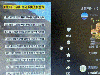如今,網上流行一個梗:「在上班和上學之間,我選擇了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間,選擇了求佛。」
如果你以為這只是年輕人的一句玩笑,那就錯了:2019年以來,「寺廟」在社交平台上的搜索量增長了368倍,今年以來寺廟相關景區門票訂單量不僅暴增,而且預定門票的人群中,90後、00後接近半數。
這是讓很多人都看不懂的一個現象:社會愈加現代化、年輕一代所受的教育也更好了,為什麼他們竟會轉身去求神拜佛,擁抱這類看似落後的「封建迷信」活動?
1
對不確定性的恐懼
現在的年輕人為什麼熱衷於上香?
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這說到底還是年輕人沒能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以至於把希望寄托在神佛身上。
《新京報》評論就認為,這樣的生活之路「顯然走偏了」,畢竟向神靈禱告是虛妄的,「奮鬥才是青春的底色」。
然而,「上香」並不必然只是指望天降橫財,和「奮鬥」也未必矛盾,不然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為何主張新教倫理才是資本主義興起的奧秘?
正如《北京日報》的社論指出的,僅僅說教沒什麼用,「與其憂心年輕人上香,不如關心他們在『求』什麼」,從根子上解決他們的內在心理需求。
這種心理需求究竟是什麼?簡單地說,他們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大增,原子化的個體又缺乏社會網絡和公共機構可以求助,無論是父母還是親友都無法有力地回應他們的困惑和面臨的挑戰,此時,神佛就成了最後的替代選擇。

古人之所以迷信,與其說是其愚昧無知,不如說是他們那時還無力掌控自己的命運,對一系列影響自己人生的外部力量都無能為力,於是轉而相信這都是冥冥中有神靈的力量在左右。
社會學家楊慶堃在《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中發現:「生活越艱難,人們越是傾向於尋求巫術和宗教的幫助;越是貧困的階層,其成員也就越迷信。」
這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相比起其他人,窮人可想而知更難掌控自己的生活,因而宿命論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可取的人生態度——把一切歸結為「命運」,那就卸下了自己的心理負擔,不用再為那些重要、但自己卻無能為力的事而煩惱,並且還得到了一個讓自己心安理得的解釋。
按照現代的標準,任何傳統社會都是迷信的,近代早期的英格蘭既是「科學文明曙光」的時代,卻也是占星術流行的巔峰。直到深入的現代化使得人們越來越有信心掌控外部環境,理性、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公共機構和法律規範的不斷完善,才使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無須求助於巫術就能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問題。漸漸地,巫術就不再是最優、更別提是唯一選擇了,到最後,它甚至成為多餘的了——如果吃藥就能治好病,為什麼還要找不靠譜的神婆?
這樣說來,那到了如今科技這麼發達的時代,又有什麼必要上香?
再現代化的社會,都還做不到掌控所有風險,甚至風險倒是比以前更大更多了。農民的生活是高度重複性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懇種地就是,至於天要下雨,那也不是自己能管得了的,就別操心了。然而到了現代社會,每個人從就學、就業、投資,生活日常,幾乎無不都面臨着抉擇,社會的容錯率又低,一步錯步步錯,而大部分風險又遠遠超出個體所能掌控的程度。

生活在傳統社會中的人,在面對天災人禍時當然也很脆弱,然而正因此,社會才會自發形成一種弱者相互支撐的社群文化。生活在其中的個體不是孤立的,但在社會快速現代化的過程中,親族、同鄉等傳統的社會支持網絡逐步瓦解,而公共救助機制卻又不完善乃至根本缺失,這樣,兩頭踏空的個體赫然發現自己要獨自面對複雜的不確定性,社會又默認這都是個人的責任,這就給他們施加了極大的精神壓力。
當那些懷抱夢想的年輕人來到龐大、陌生的現代城市裏尋求機會時,他們可能沒想到那有多困難。動盪而陌生的生活耗盡了他們的力氣,又失去了原本有機的社會紐帶,在失敗和失意時卻沒有後路可退,這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沃土:人們相信社會是冷漠、殘酷、弱肉強食的空間,任由個體面對無情的機器。
這些年社會之所以瀰漫着焦慮,決非偶然,畢竟誰都能感受到風險在上升,而焦慮感的由來,說到底就是「面對不確定性,想控制又控制不了」。
一個反覆出現的規律是:越是在那些結果難以預測的領域,人們就越是迷信。「墨菲定律」中有一句俏皮話:「散彈坑中沒有無神論者。」因為在危機四伏的戰場上,沒有人能避開所有風險。
同樣的,球賽結果極難預測(所以才緊張刺激),再老練的球員和體育記者都無法料見最終比分,因而球場上的迷信也格外突出,以至於有人相信章魚能預測世界盃結果。當然,像彩票就更別提了。
無論是焦慮還是上香,本質上還是一種對不確定性的恐懼。此時,神佛就提供了稀缺的確定性——靈不靈且另說,但至少讓人把這種壓力轉嫁給了一個超自然存在,最後就算事沒成,那也不是因為自己不努力或做了錯誤選擇,只是神仙們的問題。
2
求神還是求己
理解了求神的心理根源,我們才有可能真正着手應對解決那種困境。
客觀地說,當人們面對一個龐大、莫測又無法掌控的不確定世界時,對神靈的信念確實可以堅定他們的信心,撫慰心靈,並在法律難以保障的時候約束立約者的行為。因而看似弔詭的是:求神可能「迷信」,但卻並不必然是「落後」的。

閩粵一帶自古就有悠久的出海傳統,而從事海外貿易不僅需要巨額投資,而且是高風險高利潤的事業。正因此,對這些地方的人來說,在神靈面前的契約所奠定的商業同盟、信仰所帶來的敢闖敢幹,都是他們更好應對風險時極為關鍵的。
魯迅晚年曾在雜文《〈如此廣州〉讀後感》中說,很多人對廣東人的迷信「加以譏刺」,他也承認「廣東人的迷信似乎確也很不小」,「然而廣東人的迷信卻迷信得認真,有魄力」,不像江浙一帶只不過搞點儀式糊弄一下:「廣東人的迷信,是不足為法的,但那認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而「中國有許多事情都只剩下一個空名和假樣,就為了不認真的緣故」。
魯迅在意的並不是「迷信」本身,而是信眾的主體態度:如果是自發的、認真的信仰,那也是好的,這樣才能投入地把事做好。
同樣的,現在真正關鍵的恐怕也不是年輕人上香本身,而是他們是否有一種認真做事的精神,從而更好地應對自己所面臨的種種不確定性。
不確定本身是個中性詞,未必就一定帶來恐懼,它也可能是「高風險高回報」的機遇,所以上一輩才有那麼多體制內人拋棄鐵飯碗毅然下海——相比起一眼能望到頭的一潭死水,他們寧願拼死一搏。
不是說他們那會就沒有風險,倒不如說,當時那種對「明天會更好」的信念,部分是時代紅利,但更多的也是因為一窮二白,沒什麼可失去的,人們多多少少相信只要敢想敢幹,未來不至於比現狀更差。對未來有好的預期讓人傾向於選擇挑戰,擁抱不確定性,反之則寧願選擇穩定。
風險社會裏沒有「絕對安全」這回事,但國人常有一個牢不可破的幻想:只要抱的大腿夠粗、飯碗夠鐵、自己的欲求夠低,就能換來安全。大多數人更加傾向於接受確定性帶來的痛苦,而非不確定性帶來的痛苦——誰也不知道地火何時上涌,就選擇那個最堅固的岩塊吧。

就此而言,現在更值得警惕的,是社會上瀰漫的保守、畏懼風險的心態。
這當然也情有可原,有位年輕朋友說,這兩年他始終面臨揮之不去的焦慮感,因為感覺自己的生活「處在失控邊緣,也許一個很小的事情就會突然把我壓倒」,這還是在他沒有債務問題、父母身體健康、也沒有孩子和家庭的前提之下,而這其中任意一個都是重擔。
這兩年來很多人都過得提心弔膽、步步驚心,關鍵就在這裏:弱小的個體在巨大的風險面前本能地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因為他們深知一腳踩空就是萬丈深淵,除了小心謹慎,就只能靠運氣。
這確實是當下無數年輕人的現實處境。劇作家莫斯·哈特在自傳中就曾感嘆:「我願意斗膽做出這樣的猜測:在一切成功的職業生涯的宏大設計中,運氣始終是一個強有力的影響因素。」所謂「運氣」,其實說白了就是一些普通人不可控的偶然性外部因素。
僅僅責備年輕人「迷信」,加以「奮鬥」的說教,並不能解決他們的困境,關鍵之處在於如何減少這種外部風險,給他們提供支持,重新奪回對生活的控制感。
這當然需要社會公共機構給予更多的保障,鼓勵人與人之間的橫向聯結,而不是任由孤立個體去面對和承擔所有風險,否則沒有人能堅強到搞定所有問題。
現代社會要開闢出新領域、新可能,無不都需要冒險,但「冒險」並不意味着讓人不系保險帶一躍而下,而應當是在提供充足支持的情況下,鼓勵人堅持獨特的品質,向前探索和開闢新的可能。
人們上香,已經不是為了神靈面前的契約,而是個人主義的風險管理,尋求好運來贏回對生活的掌控感。
然而「好運」究竟從哪裏來?在這個龐大的時代,每個人面臨的不可控變量極多,也確實可能隨時陷入複雜的潛規則,但這並不意味着個體什麼也做不了,一個常識健全、認知正常的普通人,也能在暗礁遍佈的大海上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
這與其說是「運氣」,不如說是一種在不確定性的當下,認清形勢並活出自我的「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