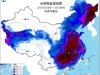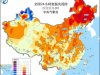兩年前,海外媒體曝光了涉及新疆維吾爾地區少數族裔被要求強迫勞動的一系列證據。據統計,作為中國政府扶貧計劃的一部分,每年有超過五十萬名維吾爾工人被調派從事季節性的采棉工作[1]。其中,許多人並非自願參與。
就在我完成這篇文章的當下,美國政府宣佈將於今年6月21日起執行《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這部法律於去年12月在得到兩黨普遍支持的情況下通過了參眾兩院批准,並由拜登總統簽署成為法律。該法規定禁止進口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供應商能夠提供明確且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它們的供應鏈不存在強迫勞動,才可以獲准進口[2]。
人類學家Darren Byler對發生在當代中國新疆地區針對維吾爾和哈薩克民族的大規模拘留、技術監禁、強迫勞動以及宗教鎮壓提供了理論分析。文章基於《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一書,對其中涉及的相關內容進行了梳理。
疫情時代以來,中國各地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社會管控演習」。無論是大範圍的封城、集中隔離,還是健康碼系統下的數字監控、強制且常態化的核酸檢測——無不讓民眾感受到來自公權力不同程度的壓迫。
新疆發生的事能否給中國其他地區民眾帶來一定的啟示?今後中國各地是否會面臨不同程度的「新疆化」?而我們又將如何面對一種科技監控下法治失序的生活?
——————————————————————————-
本書所撰寫的內容基於作者在2011-2018年間於中國西北部的維吾爾地區超過二十四個月的民族志研究。並且,通過參考政府官方文件、有關科技公司報告以及來自警方內部的信息,發現該地區少數族裔的社會生活已被國家主導的技術系統徹底改變。
在本書中,Byler提出了一個名為「恐怖資本主義」的理論框架——有關當局利用種族差異,並將其理解為一種威脅,通過結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了新形態的原始累積,同時強化了國家權力——用以解釋在中國新疆邊緣民族群體所面臨的壓迫。
首先,這裏的「恐怖」指的是「野蠻的」維吾爾族裔以及中亞殖民邊境的穆斯林群體對境內「文明」的主流民族構成了非理性的內在威脅。官方把突厥裔穆斯林視作潛在恐怖分子的立場,開啟了正常法治外的例外狀態。當個體被鎖定為「犯罪嫌疑人」(一種犯罪前定罪),正常的民事保護則不再適用。因此,出於對威脅的感知,使得將該地區大量少數民族團體置於某種「緊急戰時狀況」,並對其採取殘酷的控制手段,被認為是正當的。
這場由官方發起的反恐戰爭將目標主要鎖定在年輕的維吾爾男性身上,其中涉及的種族隔離也對性彆氣質做出了劃分。漢族男性的男子氣概和國家權威綁定,成為全球城市建設與版圖拓展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恐怖資本主義」擴張的基礎。而維吾爾男性所呈現的男性氣質則構成了一種威脅,導致大量該族裔青年男子因技術監視而「被消失」或無限期集中拘留。於是,生活和社會再生產的重擔壓在了留下來的女性身上。
與許多穆斯林社會一樣,維吾爾文化里的傳統規範也引發了不同形式的性別隔離,並最終體現在勞動分工和宗教實踐上。其中,女性很大程度被排除在公共場合之外,被迫從事家庭內的無償勞動,而男性則通過外出工作以賺取薪酬養家餬口。伴隨着維吾爾男性在中國社會公共參與空間的不斷萎縮,女性需要在維持家庭的同時承擔額外的有償勞動。
有關當局常常將維吾爾男性的男子氣概解讀為某類「病態威脅」,並以此為理由迫使他們與家中的婦女兒童分隔,或強制摘除女性身上的面紗,象徵性解放該群體受到的伊斯蘭父權壓迫。這種形式上的女權實踐成了公權力打擊宗教自由的工具。例如,每年三八婦女節,維吾爾男性會被地方當局要求為妻子洗腳,以展現某種漢文化下的性別平等。然而,這與伊斯蘭的習俗背道而馳——把腳放進容器中清洗是不潔的象徵。本質上,官方只是粗暴地把女權主義釋義為某種「夫妻和睦」,而未觸及父權制的核心。
男性們為了掩藏身上特定的「陽剛之氣」,展示某種「文雅風範」,會選擇把鬍子剃掉。並且,通過身着昂貴的西裝,讓自己儘量顯得像個都市「成功人士」,以減少「文明人」對他們的敵視。不過,對處於「邊緣」的男性來說,性別隔離下同性之間的情誼成了他們對抗壓抑外部環境的重要依靠。過去圍繞功利主義和經濟成功的男性友誼隨着殖民化進程逐漸轉向基於某種道德義務——他們有必要互相傾聽意見,分享自己的遭遇,經由「講故事」,度過那些極度憤怒、害怕或悲傷的時刻。
維吾爾人一直是積極改造世界的主體。「殖民洪流」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敘述的空間,以在生活中留下有意義的痕跡,並帶來一種還能「自主」的安全感。在作者採訪的四十多名年輕男性中,幾乎所有人都有一位非常親密的同性朋友幫助其「活下去」。雖然友誼並不能治癒他們在種族化運動中受到的創傷,但通過一起商談,似乎還能找到應對生活的途徑。
其次,有讀者可能質疑在這裏引入「資本主義」作為分析框架中的一部分是否合適,或者認為以中國威權治理為中心進行闡述更為恰當。不過,Byler表示雖然國家權力是解釋種族壓迫的重要層面,但這類框架不能完全用於分析案例中跨國經濟及政治力量、科技公司和「再教育營」在其中的自主權、外來移民於當地的生活經歷,以及技術發展下有關參與者的種種「獲利行為」。
國家雖然能產生強大的作用,但最終總不可避免受到公共和私人機構一系列話語與經濟利益的影響。在「新疆問題」上,許多身處其中的安全和情報工作者都屬國有企業、私營技術部門或安保公司的僱員——儘管該群體也常常面臨被起訴、降級和撤職的風險,但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受經濟因素而非國家權力驅使。這些公權力的代理人通常只關注如何為自己及家人謀求更好的生活——其行為背後並不存在純粹的政治動機。
除了將中國國家當局置於歷史變革的中心、通過更規範的政治權力框架解讀之外,當代的權力配置也受到全球資本主義及殖民地關係的影響。這裏作者想要駁斥一種「有無國家權力參與」的二元論結構。此處想要展現的是,全球性的反恐敘事如何與跨國資本主義結合,在新領域創造新形式的剝削。總體來說,「恐怖資本主義」是一種包含了國家資本、科技與政治監視,以及不自由勞動的獨特配置。
因此,這裏所說的「新」可以理解為對過去市場之外的東西賦予商品屬性。傳統上,「圈地運動」主要涉及開採自然資源,將被殖民者的土地轉化成財產——用作工業生產的一部分——並迫使被殖民者接受低價報酬或無薪資工作。然而,當代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正在改變人類的生存方式。舊時社會生活中那些從未被商品化的部分——行為及生物特徵數據——正被用以創造可以衡量和預測效率、欲求及犯罪行為的商品。
第四次工業革命後,以大數據為依託的技術發展強調了一種「軍工聯合體」在科技創新和國民經濟中的關鍵作用。通過調整軍事及警務工作中有關工具的使用範圍,政府和企業將技術應用擴展到新的生活領域。越來越多的機構利用信息通訊技術,例如,數字取證工具、生物特徵檢查和圖像識別系統,來控制、操縱公民及勞工。
這種「恐怖資本主義」將技術壓迫和全球經濟聯繫起來。除開傳統的知識產權外,監視系統和警務安全設施下的第一種資本形式是數據。中國政府在新疆開發了一個「完美」的數碼化環境,讓境內一些大型的私營和國有科技企業得到了研發數字取證、圖像和面部識別、語音識別等有關技術的機會。這些企業不斷從該地區的1500萬維吾爾人那裏搜集數據,從而讓肖像識別、虹膜掃描、語音簽名等科技從概念發展為新的現實,並將以上「智能安全解決方案」運用到其他領域。
第二種資本形式是「數字圍欄」系統下不自由的人力勞動。自2018年以來,新疆有關當局一直將圍困當地群眾的營地和「再教育」體系描述為一種「經濟載體」,其規模和該地區1990年代開始吸引漢族移民的石油、天然氣、棉花等一類資源規模相當。這些被拘留的民眾分散在營地和工廠中,管理人員利用智能手機跟蹤、檢查站、面部掃描等監控方式將這些維吾爾人安排在合適的勞動崗位上,確保其「聽話」。
即使在政府宣傳中,這些「沒有正式就業的人口」通過地方當局幫助,能夠「自由」地選擇在離家近的地方工作或實習,卻也只是一種虛假的「自由」。因為沒有談判空間以協商工資或抗議不合理的扣薪規定,這裏的市場行為依舊是「不自由的」。
然而,沒有人談及中國的治理策略是如何將維吾爾教師趕出教育系統,限制其合法的宗教活動。與此同時,在自然資源部門的不當開發下,人口的生活成本逐年上升。由於系統性的工作歧視,當地少數族裔中的許多人被排除在新經濟體的工作之外。隨着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接管地方政府事務,針對維吾爾社群的「佃農剝削」和「強迫移民」被不斷強化,最終導致該群體就業不足。
不過,根據中共官方文件顯示,當地維吾爾及哈薩克民眾作為「過剩勞動力」反而成了發展新疆經濟的額外紅利。而且,大量的政府補貼——場地及設施的免租優惠、勞動力培訓支持——吸引許多私營企業將部分生產轉移至新疆。重要的是,該系統生產的大部分產品都用於出口——這就是為什麼把相關環節所涉及的強迫勞動和全球資本主義前沿生產結合起來理解的主要原因。
因遭到不合理對待,零九年維吾爾地區發生了大規模的街頭抗議、警察暴力和騷亂。高強度的武力鎮壓和國家控制使得該群體對當局產生了更深的怨恨。與此同時,在政府的鼓勵下,越來越多的漢族遷移至南疆,加強了對地方土地的徵用。因此,原本就已緊張的局勢進一步惡化。許多事件被官媒描述為「恐怖主義」,但其中喪生或受傷的大多數人往往是維吾爾示威者。他們通常手無寸鐵,並被警察使用的自動武器打死或打傷。
不過,這種打壓卻讓許多人對其所熱衷的宗教實踐更加虔誠——既是一種象徵性的自我保護,抵禦來自漢族日益增加的壓力,也是逃避國家對信仰、教育和經濟控制的一種隱晦表達。2014年五月,地區領導人開啟了「人民反恐戰爭」。其目標不僅包括打擊發動襲擊的罪犯及相關支持者,更是將範圍擴大到基本的宗教活動。起初,這種反恐行動只把宗教領袖送往集中營,但在2017年起,審查行動開始針對境內所有的穆斯林人口。
恐怖主義敘事的興起以及ISIS(伊斯蘭國)的建立引發了一種全球性的「伊斯蘭恐懼症」。對中國來說,集中表現在當局開始有意限制穆斯林習俗,例如將定期參加清真寺活動和齋月禁食視作宗教極端主義影響下的「精神疾病」。「人民反恐戰爭」實際上變成了如何阻止維吾爾人進一步「維吾爾化」和成為穆斯林的一項計劃。
並且,政府機構將公權力授予有合作關係的承包商和其他私營企業,建造了數百個名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大型集中營,以圖改造該地區的原住民。更進一步看到的是,受益於當地豐富自然資源的私營企業和政府通過發展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PP)開展了大量業務,推動了科技監視產業的發展。
「恐怖資本主義」利用全球性的「反恐」敘事以正當化國家和私人資本對數據及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行為——以此拘留工人、強迫其勞動。有時,工廠老闆被允許從拘留人口中挑選工人。其他情況下,地方當局會為工廠安排合適的人選,擬定勞動合同。在技術創新的外衣下,中國政府製造並扭曲放大了維吾爾族裔所能產生的威脅,仿佛這些恐怖分子數量眾多且無處不在,成為其合法侵佔該地群眾土地和勞動力的託詞。
在書中,Byler詳細闡述了這類以殖民項目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擴張。其中,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是相互助益的——數字媒體監控在政治操縱和經濟領域所能發揮的關鍵作用,使得監視搭配着「不自由勞動」,一同幫助完成了被管控群體的認知轉變,並且引發了新的知識生產,而這種知識框架下所倡導的社會生活,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和殖民計劃的終極目標。
以「恐怖資本主義」為分析框架,Byler回答了以下幾個關鍵問題:1)國家引導的「治理系統數碼化」如何作用於維吾爾社會的再生產過程?2)利潤豐富的政府合同使得科技企業得以研發、部署用於監視及管理當地少數民族甚至其他地區人口的技術——這樣的技術對個體生命價值產生了哪些影響?3)物質、「數字圈地運動」如何控制目標群體,並為公共治理和私營生產創造新形式的自律行為及勞動力?
通過考察維吾爾人的社會再生產過程,作者發現自2010年起,3G網絡和社交媒體應用程式的興起讓當地少數民族能夠與更大的穆斯林世界和全球宗教運動聯繫。然而,一四年「人民反恐戰爭」的到來創造了新的種族標籤——將年輕的維吾爾男性旅行者和所謂的恐怖分子威脅關聯。於是,原本促進文化生產的數字空間逐漸成為新的技術陷阱。在微信上分享都市異化小說、帶有民族主義和穆斯林文化的視頻以及其他宗教信息,都會被當成「被消失」和無限期拘留的證據。
隨着運動激烈程度的不斷加劇,維吾爾青年們越來越需要被迫做出選擇——要麼在警察的密切監督下為有關當局工作,例如,擔任政府承包商、營地指導員和情報人員,要麼被送進集中營和勞動工廠。於是,作為拘留生活的替代方案,多數人選擇了「秘密警察」的工作。然而,一旦以「數字管理員」的身份投身系統,他們很快便能意識到其任務是協助當局拆散家庭、審問鄰居和監視他們的親朋好友。而且,這樣的反恐鬥爭工作是終身制的——不存在退出機制。選擇退出意味着對國家不忠,從而再次面臨被拘捕的風險。
由此,新的政治和經濟形式被創造,而維吾爾群眾需要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角色:被拘留者、警察或被拘留者的親屬。除了幫助監視同胞外,他們中的一些人被要求通過社交媒體展示其外表並且出席帶有濃烈政治意味的公開活動,表達其愛國熱忱。並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接受「再教育」,以體現他們對國家意識形態和漢文化的渴望。
於是,反恐運動下警察和普通民眾間的對抗演變成了後者單方面服從的慣性反應。例如,人群自發在檢查站出示其身份證,即便每日頻率多達十餘次。監視和拘留的常態化讓暴力通過有秩序的標準操作流程呈現,從而掩蓋了家庭和生活的支離破碎。
基於對犯罪行為的威脅性評估存在廣泛且任意的特點,任何看起來擁有「維吾爾外表」的個體都有可能遭到逮捕。正當司法程序的缺失,導致官員在決定某人是否被拘留方面握有很大權力。因而,一種「警察擁有絕對權威」的印象深深印刻在了還未遭到關押群體的腦海中,由此催生了大量年輕維吾爾人想要投身系統的渴望。
除了直截的高壓干預外,當局對關涉維吾爾族裔歷史的文化作品進行了大範圍的審查——進一步放大了該民族精神中的脆弱性。展現突厥英雄傳奇和維吾爾人革命的歷史小說,作為民族分裂主義的典型被禁止宣傳;而早期獲得國家批准的包含伊斯蘭教和維吾爾文化的書籍如今也被扣上了宗教極端主義的「帽子」;所有相關的電視節目和音樂也被重新評估。
因為審查的滯後性,許多維吾爾音樂家、詩人、演員和電影製作人被拘留。有作家甚至聲稱,1990-2000年間,國家文化部常常要求他們撰寫有關伊斯蘭教或少數民族問題的文章,展現溫和的宗教虔誠或民族自豪感,而如今他們卻因完成這項由當局授權的任務而遭到懲罰。同時,在微信和抖音等社交媒體公司的幫助下,政府開始不加掩飾地宣傳政治教條,重塑維吾爾族裔的精神世界。通過「再教育」,教會他們用「紅色語言」表達審美、書寫感受——推廣一種殖民主義下的文化產品。
在這種情況下,有的維吾爾人選擇離開,通過申請庇護,成為一個「永遠的旅行者」。他們可能再也無法回到那片土地,同時需要切斷與其他同胞的聯繫,與過去的一切保持距離。不過,到了新的國度,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開始有了正常的社會角色。年輕維吾爾男性不必再擔心自己的「陽剛之氣」被過度認為具有威脅性,他們開始在來自不同地區的移民群體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中國境內維吾爾社會所遭遇的一切,存在於全球殖民與剝削敘事的前沿。無論是克什米爾、巴勒斯坦,還是新疆及哈薩克地區所發生的悲劇,都建立在對特定種族的掠奪和削減上——有利於占社會主導地位的群體聚攏財富與權力。這裏表現為一種原始積累——將生產價值構建在特定的對象上。
維吾爾人作為一個集體,通過「數字圈地」與公共治安運動、「再教育」以及監控下的「非自由勞動」,變得富有生產力。國有和私營科技企業推動的資本流動,放大了他們對國家的威脅,並由此產生了新的經濟和社會控制形式。隨着這類機制逐漸走向常態化,身處其中的人們也會變得適應。這場針對維吾爾人的「實驗」會覆蓋更多群體。權力、數據化、新的知識生產的不斷擴張,最終會觸及生命本身,侵蝕每一個個體的靈魂。
願盡力通過一種非簡化的思考及描述,回歸人與社會本有的複雜。
[1] BBC(2020).新疆棉:新證據揭露時尚產業背後的強迫勞動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5344353
[2] VOA(2022).《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即將實施,美議員促拜登政府嚴格執行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lawmakers-urge-biden-to-rigorously-implement-uyghur-forced-labor-law-20220606/66062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