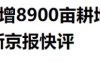1958年在公社化進程中大辦公共食堂,被視為進入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金橋」。辦不辦食堂、吃不吃食堂被看作是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當時批判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條重要的罪狀就是反對辦食堂。《人民日報》報道過一條消息,說雲南有個「右傾分子」反對群眾辦食堂。群眾說我們的食堂是「雷打不散」,那位「右傾分子」說「我就是雷公,就是要把你們的食堂打散」。這是作為反面典型來示眾的。在這種形勢下,農村幾乎是社社有食堂,隊隊有食堂(當時的生產隊相當於1961年以後的生產大隊)。
北京雖沒有普遍搞食堂,但在「大躍進」高潮期間,飯館吃飯自行付費,發揚共產主義風格,愛給多少給多少。每天我在菜市口的「南來順」吃早點。一天早上,一進飯館就大吃一驚,屋子中間是十多張方桌拼成的一個台子,放着油餅、燒餅、麻花等食物,旁邊有大桶,裏面是豆漿、杏仁茶等。這些都是任君自取,四周的方桌上有小笸籮,中有零碎錢幣,由君自行付款。飯館裏的人比平常多了好幾倍。油餅等一端出來都是一搶而光,「南來順」堅持不到一個禮拜,又改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了。「南來順」的一位老職工說:「賠不起啊!」那時,人們仿佛到了君子國,如此隨意地對待經濟,經濟難道不會報復嗎?
1959年秋天報復就來了,先是商店的東西越來越少,購物票證越來越多。什麼時候進入困難時期?在我看來有個標誌性的事件,那是在1959年「十一」以後,有個秋風蕭瑟的早晨,人們起來買早點時發現北京人習慣吃的燒餅、果子(炸果子,一種類似油條的食品)、油餅、豆漿、杏仁茶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菜粥」。這件事給北京人留下極深的印象,因為大多數北京人早上沒有吃菜粥的習慣,當時所有的飲食攤點都是國營的,要變一律都變。困難的緩解也可用早點鋪的變化作標誌,1961年冬天一個早上,所有的早點鋪都支起鍋炸油餅了。而且很奇怪,油餅炸出來都是白的。我曾問過,是不是沒炸熟?回答說,這是大油(豬油)炸的,怎麼炸也不掛色。
1961年春末夏初,通知我們下鄉宣傳《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由於經濟困難,本來大學生停止了下鄉勞動等活動,這次是個例外。當時食品奇缺,農村餓飯現象很普遍,而幹部則利用權力多吃多佔。有民謠說「書記拿,隊長偷,社員縫個大衣兜」。「十二條」基本原則是局部改變1958、1959年的激進做法。如確定農村所有制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而辦公社時強調「一大二公」,許多縣就一兩個公社,這次退到一個鄉一個公社;又如制止「一平二調」,平調老百姓的財物儘量退回,退不了的作價賠償。我去的是北京郊區的一個生產隊,那真是凋敝不堪,觸目驚心。我住在隊部,因為常停電,天黑就睡,早上起來,仰望天花板,很奇怪,怎麼是黑的呢?天大亮了,我站在床上穿衣服,空氣一震動,轟的一聲,天花板好像裂開了,原來夜裏天花板上聚滿了蒼蠅。生產隊很窮,惟一的大牲口是一條瘦驢。負責飼養瘦驢的是個「富裕中農」,所謂「富裕」只是個成分了,他餓得瘦骨伶仃,眼睛都有些發藍了。就這樣,有個社員還到隊部告發他,說他偷吃驢飼料——糠,而且拿着他的糞便作為證據。
下鄉的第一件事是勸導老百姓種「十邊地」(指溝邊、路邊、屋邊、河邊、池塘邊、田邊等),並說「誰開墾誰種,誰種誰收,誰收誰有,二十年不變」。社員不相信,當面就駁斥我,什麼二十年不變,搞「『初級社』你們說二十年不變,不到兩年變了」;「『高級社』也說二十年不變,結果不到一年變了」。我只是個19歲的學生,根本解釋不了。問一同下鄉的教務長,他含混地說,不要管它。
第二件事是解散食堂。「十二條」中還說「公共食堂制度,必須堅持」。還有「辦好食堂」的指示,我下食堂幫廚,名義叫食堂,真辜負這個好名字。「食堂」只蒸「豆面窩頭」,開飯就是社員來打窩頭,端回家去吃。所謂「豆面」不是用豆子磨的,有人說是用榨過油的豆餅磨的。面粗而輕,有些像鋸末,蒸好的窩頭一拿就碎。像我這樣一頓可吃一斤饅頭的小伙子竟吃不下一個窩頭,然而社員還常常為給他的窩頭掉下一塊而爭吵。還好下鄉不到一個月,傳達了中央給農村幹部和社員的一封信,其意在於解散食堂。不過話說得比較婉轉,說「吃食堂光榮,不吃食堂也光榮」、「吃食堂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吃食堂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前面留了「吃食堂」兩句恐怕是為了顯示與以前的宣傳的承繼關係。這封信一宣讀,社員大樂,食堂馬上散夥,連一天也不等。這是我下鄉後第一次看到農民發自內心的樂。食堂把糧食按定量分給個人,還好,北京農民還有鍋,不至於糧食拿回家後沒法做熟。
下鄉不到兩個月就返校了,解散食堂很成功,宣傳種「十邊地」則被頂了回來。後來曾碰到當地社員,問起「十邊地」,回答說老百姓還是種了,又說能種一季就種一季,收的糧食吃到肚子裏誰也拿不走。
這次下鄉還有兩事可記,一是有位同學膽子真大,竟敢搞「包產到戶」,把他所在生產隊的田分了,當時就受到校方的制止和批評,可是這曾使農民興奮。二是我所在的生產隊中有位菜園子的「把式」(當地以種菜為主,從外面聘請有種菜技術的師傅)姓李,他教給我許多種菜的知識。我曾說「李師傅,我一定請您吃頓炸醬麵」。他笑了,說「等五月節小貨(指園子裏速生的小白菜、小菠菜、青蒜之類)下來罷,讓你們吃點真正的鮮菜」。我存了些面票,準備讓他吃個夠。可惜的是不到五月節(端午)就被召回學校,那個邀請成了一句空話。時間過去了四十多年,每想起此事都有些遺憾,眼前還會浮起李師傅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