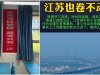今年是我下放農村當知識青年46周年,我的高考經歷就是在知青歲月中度過的。我生性愚笨,考了3次才終於「跳農門」,而且其中一次與收音機有關,可謂與「機」福禍相倚。
湖南省臨湘縣中山湖農場,是一個以知青為主體的國營農場。1975年盛夏,我高中畢業下鄉來此時,全農場有知青約一兩百人。兩年後的1977年冬,中國恢復中斷了十餘年的高考,我們農場有一二十人躍躍欲試,其中5人入圍,最後僅一人錄取,而且那唯一的一位報考的是理科,卻陰差陽錯地被錄進典型文科類的岳陽師專中文科,可見當時國家求賢若渴之急切。我一直喜歡文科而數學成績不好,被它把總分拉得太低,所以這次連「五類分子」都不是。
第二年仍要高考,我改變策略「投機取巧」:改報純文科為考英語,因為那個年代考外語類數學只作參考不計入總分,正如考藝術類對外語的要求。於是,我向當中小學老師的父母親死纏硬磨,讓家裏節衣縮食咬牙拿出半個月工資,給我買了一個袖珍收音機學英語。
田間地頭,我在農場干農活時,就把那收音機裝在口袋裏,邊務農邊收聽中央及湖南、湖北人民廣播電台的英語講座節目。甚至有一次,我挑一擔牛糞下田不慎摔倒在田坎,有熱心人士關切地問我不要緊吧。我微笑着沒把這點小「摔」當回事,但隨身傳出收音機里的英語聲卻讓別人當了回大事。
正如千個觀眾有千個哈姆萊特,對同一人或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同隊知青及對我們進行「再教育」的貧下中農聊將此事當做「美談」,說我辛苦幹活還不放棄學英語:但緊繃階級鬥爭這根弦的農場幹部卻對此高度警惕,從中悟出了「階級鬥爭新動向」,「上綱上線」地說我是「收聽敵台」,因此我被叫到農場場部關禁閉寫反省。
那已是1978年春了,粉碎「四人幫」後撥亂反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了一年多。可春風難度農門關,我們那農場對「四人幫」的餘毒似乎還沒大肅清。我寫「反省」申辯用收音機聽的是國內人民廣播電台的英語講座而非國外的敵台,農場那幹部先撇下我收聽的是何電台不談,直接指責我的「反省」上端沒有引用毛主席語錄。我隨手拿來一份《人民日報》辯稱:「四人幫」時期黨報每天頭版報眼上都有一條毛主席語錄,現在已去掉了這樣的形式主義,我沒引用是緊跟目前的大好形勢。
我的知青農友廖賢平當時在農場當電影放映員,以他的電學知識為我辯解:徐的收音機只能收聽國內的中波收不到國外的短波。他也被訓斥階級覺悟不高。
1978年夏,我還是參加了高考,意料之中地名落孫山。好在我們農場有3位考上了,一位考的是中師,一位是本科,廖賢平則於當年底被補錄進了郴州醫專。他頗有才氣和志氣,後來繼續攻讀湖南醫學院(現併入中南大學)碩士和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現併入上海交通大學)博士,曾任廣東武警醫院院長。
恢復高考的第三年,即1979年春,我對考英語仍依依不捨。為洗清農場幹部抓住收音機給我安的罪名,我跑到臨湘縣公安局「投案自首」。該局民警笑着打發我走了:我們不需調查你是否真的收聽了,這都什麼年代了,哪有什麼「收聽敵台」罪呀!
我這才無「敵」一身輕,由我父親爭取插進臨湘一中,安安心心地補習了兩個月,通過是年7月7、8、9日三天的考場拼搏,總分上了重點大學分數線。或因不自量力好高騖遠,第一志願報的我心儀已久的名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我還差分哩,結果錄取一降再降,降到了我沒有填報志願的零陵師專(現升格為湖南科技學院)英語科。
據現有資料統計,恢復高考的三年錄取率是新中國建立以來最低的時期:1977年570萬人考取27萬錄取率5%,1978年610萬人考取40萬錄取率7%,1979年469萬人考取28萬錄取率6%。
我能夠成為其中的幸運兒總算是百幸,尤其是與恢復高考首年農場遇難的3位農友相比:那是1977年冬,農場漁業隊6名知青駕一葉木舟下湖捕魚,忽遇風暴翻了船,其中一半人溺水身亡。隨後知青們激怒了,加上有要高考的藉口,許多人都不願回農場幹活。如今冷靜思考農場幹部揪住我收音機大做文章的事件,也覺得情有可原:他們並非對我有特別的偏見或敵意,而是拿我來殺雞儆猴以阻止知青擅離農場的「返城潮」。如此想來,我又是幸中的不幸。
人的一生,總難免禍兮福所倚或福兮禍所伏。譬如我零陵師專畢業分配在臨湘二中教英語仍不甘心,4年後仍傻拼考研究生,果然如願考上了華東師大,只是改洋為中攻讀的是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元明清戲曲方向,好在碩士論文來個中英結合:英譯本《西廂記》研究。眨眼早逾花甲已退休4年,不管旁人如何看我,我常以唐代柳宗元筆下那外來虎對「黔之驢」的看法自嘆:技止此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