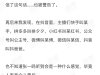表面上人們更多表現為喜氣洋洋,像被集體施了催眠術一般,臉上掛着那種沉默詭異的表情,從此不再開口。米沃什的觀察力是驚人的。他強調,在波蘭作家當中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一件比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兩年之內,他已經感到不能忍受,意識到了後面即將到來的一劫不復的精神災難。
對於西方列強的失望,也是為東歐知識分子與中國知識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經驗。書中有一章叫做《看西方》,作為今天的一名中國知識分子,在其中也能夠找到許多共鳴。稍微拉遠一點看,當時波蘭知識分子遭遇到的這些問題,由戰爭的暴力與破壞一下子摔在人們腳面上的重負,也是一個現代性的遭際。人們從一個自洽的、受庇護的傳統社會,被拋入需要個人承受巨大壓力的現代社會,許多傳統文化並不提供這樣的支持。
米沃什設想後來的讀者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人們沒有就黑格爾式的歷史運行觀做出一番討論嗎?他的回答是:議題是人家設計的,對方有備而來。「在武裝好的理論家和應戰者之間存在着比例失調的現象,就像坦克跟步兵決鬥一樣。」某種情況與中國一樣:一個人即使熟讀四書五經,掌握了唐詩宋詞這樣精美的文化,但是對現代社會如何組織起來的,什麼是人與人之間平等合作的關係,也仍然一無所知。結果是,運用前現代的方式去解決現代性的問題,本來應該往前一步,結果卻變成了往後一步,甚至是好幾步。
讀到這些章節,我的腦海中會浮現出許多前輩的面容,想起他們說過的許多話。一位我尊敬的前輩,曾與我談起過最初接觸「社會發展觀」所產生的巨大心靈衝擊,他感到有人能將歷史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全部說透,真是了不起。王蒙先生也始終強調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自己早年的選擇無怨無悔。無論如何,我們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感受,尊重前人的道路,我自己的父親所走的也是同一條道路。但是米沃什告訴我們,任何選擇不是憑空產生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部條件,看似自由的選擇其實未必自由。再者,選擇也是建立在自身現實與思想基礎之上,而這些基礎本身可能是十分薄弱的。在這種條件下人的頭腦更多是危機的產物,它釋放危機以及複製危機。
米沃什揭示了某個晦澀的深層心理結構:深層是個人前途及道德危機,人們能夠感受到的卻又是發自內心的服膺(臣服),他沒有把這個過程說成是出於外在壓力。面對一場「精巧的辯護」這種批評,米沃什的回應是,他只是誠實地寫出了自己看到的東西,將不同聲音、不同人們自己的解釋、理由寫進書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聲部敘述,而沒有為了仇恨或怨恨,將事情簡單化、符號化,更沒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裏的人們的需要。
三
每本書有其自身命運。隨着時間的推移,歲月的淘洗,該書的第三章「凱特曼——偽裝」,顯得越來越有意義。它不僅適合極權主義的早期,而且對於後期極權主義,同樣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銳地指出,在來自歐洲東部的人,會發現西部的人們,不管是搬運工還是出租車司機,看上去表情坦然,輕鬆而自然,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而沒有那種內心的緊張、晦澀和難言。受到「辯證法壓力」的人們則充滿了矛盾。人們必須演戲。必須戴上面具。在大街上、辦公室里、會議廳、工廠、甚至在起居室,人們說每一句話必須考慮後果。戰戰兢兢的狀態,並沒有培養起人們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過是逢場作戲。如果不能中斷,那麼只有越演越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國駐波斯外交官的一項發現,它被稱之為「凱特曼」。按照這位外交官的描述,穆斯林世界的某些人們認為,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傷害,不僅應該對此保持沉默,而且還要公開否認自己的觀點,公開羞辱和貶損自己,採用對方的立場和語言,出席一切在他看來是荒唐的儀式和表演,爭取加入到對方的陣營中去,藉以蒙蔽對方,引對手犯錯誤。
如此,人們在強權面前的潛台詞就變成:你要什麼,我給什麼。我正好是你要的那個東西,我是你的邏輯,你的立場。這下你沒有什麼可說了吧。如果犯錯誤,那是你的錯誤,你的不幸和無力,與我無關。你的錯誤由你來承擔,我的錯誤也由你來承擔。因為我就是你。這樣一來,事情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本來是被迫撒謊,現在變成了一項主動的策略。他不承認自己是一個被欺騙者,反而認為自己是欺騙對方的人。他不是失敗者,而成了是得勝者。在這種貌似欺騙中,他獲得了某種道德上的優越感。在眾目睽睽之下,這個人眼睜睜地從任何責任感中逃脫了。
某種情況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說里發生的。比如《革命時期的愛情》裏的王二,作為在豆腐廠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輸送豆漿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這成了他的一樁愛好,很難說這僅僅是因為工作的需要。革委會主任老魯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須不斷逃離。讀者或許產生這樣的印象,老魯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現實,變成了他的內在要求,這樣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魯,以對方的邏輯,藉此戲弄對方。他東躲西藏卻又拋頭露面,他在空中飛來飛去卻又不斷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魯抓住了衣領,但那個領子是白紙畫的,輕輕一掙脫就被撕成了兩半,他本人就如斷了尾巴的壁虎一樣逃走了。還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魯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氣絕身亡。老魯嚇得趕緊把他往醫院送,送出廠門他就活蹦亂跳了。氣得老魯說,下次王二再沒了氣,不送醫院,直接送火葬場。
在小說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現實是另一回事。在現實中,重複他人的邏輯和錯誤,並不意味着找到自己新的起點,而恰恰會掩埋自己原來的立場,歪曲自己的感情。讓人性停留惡作劇的水平之上,並沒有增添任何新的東西進來,富有意義的東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長此以往,策略也會長成人的面具,戴在臉上拿不下來。以一種空洞去對付另一種空洞,一種虛無去對付另一種虛無,一種同樣是掩飾來對付原來的掩飾,這當然不需要花什麼力氣,只要順勢就行。
米沃什抱着一種博物學家的興趣,列舉了各種不同的「凱特曼—偽裝」。
民族凱特曼。既然你們說蘇聯是最偉大的,那麼我讓你沒法找茬的做法就是——每說一句話,都稱讚一下俄羅斯的偉大成就,腋下隨時夾着一本俄羅斯雜誌或書籍,嘴裏時時哼着俄羅斯歌曲,在俄羅斯藝術家演出時,報以熱淚的掌聲。而實際上,我可能認為那是一個野蠻國家,對此只有無比藐視。
革命純潔性凱特曼。人們全身心地被「聖火」、「英雄」的神話所充斥,又被徹頭徹尾的仇恨所灌滿。憎恨把人們的人性拉向比較低矮的去處。
美學凱特曼。一個人在家裏坐擁廣泛收藏的各國作家的經典作品,以及各種現代藝術的唱片,他已經從這種東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學品味,但是卻隨時準備拋棄和犧牲它們,加入到正在流行的惡俗趣味中去,並因為自己擁有這些偽裝的技巧而感到暗自滿意。
職業工作凱特曼。一個學者能夠做到嚴格按照黨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個要求的報告。
懷疑論者凱特曼。即犬儒主義凱特曼。
形上學凱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帶來的處境,覺得這未必不是一場新的、不可或缺的贖罪煉獄。
倫理凱特曼。人們搖身一變,披上了「新人」的外衣。他們表現出根除了舊社會的惡習,自覺將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工作勤懇,任勞任怨,嚴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常常表現得歡天喜地,對一切都感到很滿意,並要求別人也這樣做。米沃什認為,倫理凱特曼,是一種最為強勁的凱特曼,包括能夠做到對原先的朋友鐵面無私,告發周圍的人得到鼓勵。
「凱特曼」遍地,則是偽裝遍地,謊言遍地。事情的真相被一層層覆蓋了起來,被無數次地摺疊在裏面,無從打聽。結果是人們患了各種精神分裂症,重度和輕度的、長期和短期的。一個人與他自己相分離,與他自己之間隔着一條大河,他弄不清楚在他自己身上那些是真實的,那些是重要的;弄不清什麼是該喜歡的,什麼是該拋棄的。事情原有的界樁被一再移動,他日益變成含糊含混。
對一些人們來說,他們一開始也許並不是故意要撒謊和作惡,他們本性上也許是善良的,但因為擁有某個不謹慎的開頭,繼而步步邁向謊言的深淵,越走越深,難以自拔。如果說最初還有良知的愧疚,知道自己的良心在什麼地方,漸漸地,他變得不辨是非、不分善惡,因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模模糊糊地認為能夠矇混過關就是真相本身。即使他原來是一個普通人,結果照樣也可以挑戰社會和他人:打着真與善的旗號,兜售他本人的假和惡,與他的大環境處於互為輝映「鏡像關係」當中。
不難想像,也許有一天人們對這些厭倦了,想要重新開始,卻不知道從何開始,源頭在哪裏。人們離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恥成了新的道德觀。
米沃什承認,他本人也玩過被要求的「遊戲」,也妥協讓步過,因此該書既是與他留在波蘭的朋友之間的對話,也是與他自身的對話。這樣一種自我反省的立場,正是我們今天特別匱乏的。在溯本追源的今天,也應該包括通過審視自身的道德狀況,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進整個社會的道德復原。一個人起碼要堅持住自己,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塊僅僅是遭受損失的大陸。
波蘭歷史學家亞當·米奇尼克(1946——),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想起了詩人米沃什的詩句。1982年米奇尼克寫道:「當你獨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淚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動着手槍——在這漆黑的、沒有星光的夜晚,多虧了你最愛的詩人,你能夠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賴於滾落的石子翻個身(切·米沃什)。於是,你想要成為那塊扭轉事件方向的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