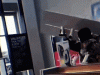目前,從封閉隔離到氣候變化等任何事上都呈現出教條主義確定性的盛行,在這樣的世界,質疑精神至關重要。
多虧了啟蒙運動和科學思想和技術的發展,敢於質疑的心靈在現今時代基本上遊刃有餘。但是,現在似乎不再如此了。
這是因為懷疑精神賴以生存的言論自由在最近一些年一直遭受越來越激烈的攻擊。它越來越多地被描述為一個問題或一種風險或一個威脅。有人告訴我們,言論自由傷害弱勢群體,令弱者受到傷害。政客、學者和評論家們現在頻頻談及極右翼勢力往往將「言論自由當作武器」。最近,來自常青藤大學的一幫法學教授甚至論證說,言論自由曾經受到保護,且被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認為神聖不可侵犯,但現在由於川普總統的使用可能給民主本身帶來威脅。
言論自由曾經被當作民主的前提條件,現在卻被描述為對民主的威脅,越來越明顯地顯示出,掌握文化和政治機構的人不願意容忍不同意見。如果言論自由被認為有這麼大的威脅,尤其是當今疫情期間,那些實施言論自由的人可能被認為是社會危險。這似乎已經是當今懷疑論者的宿命。
只要看看所謂的隔離封鎖措施懷疑論者現在討論的內容就明白了。他們被指控「手上沾滿了鮮血,」持有「致命性的錯誤觀念」。他們應該遭到排斥、審查、和羞辱。本着這種精神,《衛報》一位專欄作家甚至要求批評隔離封鎖共識的具體科學家應該被社交媒體封號,不准他們在上面發表言論。這一點兒也不令人奇怪。現在,懷疑論往往被描述為危險觀念,需要被摧毀以免我們都跟着遭殃。
不僅僅是對封鎖隔離措施的批評受到攻擊。對建制派世界觀其他方面的批評也遭到大致相同的待遇---也就是說被看作危險觀念和帶來威脅的東西。其實,那是我們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教育精英妖魔化批評的嘗試,這種批評有助於形成對懷疑論本身的更廣泛妖魔化。我們不妨想想圍繞那些歐洲懷疑論者或氣候懷疑論者的一陣陣尖刻攻擊。人們不是將其描述為持不同意見的人而是將其描述為道德上的低劣者甚至潛在的危險分子。
同樣,他們的書籍、文章和電台、電視形象也獲得中世紀教會對待異教徒文獻那樣的待遇:思想腐化之源頭。就拿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就比約恩·倫伯格(Bjorn Lomborg)批評當今環保主義某些方面的《假警報》所寫的書評來說,斯蒂格利茨宣稱「如果它成功地說服任何人的話,那就極其危險了。」
或者我們看看針對質疑政府封鎖隔離措施的《大巴靈頓宣言》的作者以及質疑封鎖措施的個人如理論流行病學教授蘇涅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的歇斯底里式批評。他們的人格和專業知識受到誹謗和中傷,更令人擔憂的是,批評家們還要求開除他的公職。這已經帶有現代高科技獵巫的特徵了。
當然,還沒有人談到燒死或溺死懷疑者。不過,文化和學界建制派的確似乎想將懷疑者尤其是表示懷疑的科學家剔出公共生活。其主流反對者宣稱,電視和電台製片人需要停止基於新聞報道的平衡謬誤理由邀請「邊緣」科學家到節目中來。他們聲稱,懷疑論者的觀點並沒有像主流共識那樣的學界和科學權重。
這種論證並沒有什麼新鮮之處。因為擔憂媒體上的氣候變化懷疑論者的存在,美國學者娜奧米·奧雷克斯(Naomi Oreskes)聲稱「記者的職業道德要求並不適用於科學。」她堅持認為,科學問題上的辯論應該僅僅限於科學機構的職業成員之間,他們的論證應該發表在同行評審的學術期刊上。另外一個評論家宣稱,聽任氣候變化懷疑論者在媒體上發表言論是道德懦弱的行為,它源於拒絕在唯一的真理問題上選邊站。
在疫情肆虐的過去一年,這種反對懷疑論者的聖戰已經進入超速行駛狀態。比如大科技公司如YouTube、推特和臉書已經使用疫情威脅來論證審查和管理新冠病毒政策辯論的合理性。當YouTube行政總裁蘇珊·沃西基(Susan Wojcicki)宣稱,任何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推薦意見相反的東西都應該被清除掉時,她似乎已經錯誤地把自己當作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言人了。
對懷疑論者的道德詆毀
從歷史上看,為呼籲審查辯護往往是基於這個理由,該文本要麼政治上具有顛覆性,要麼在道德上墮落。這種辯護如今成為反對懷疑論教條的關鍵部分。
在這方面,斯蒂格利茨指控倫伯格的《假警報》可能有「思想污染」的危險就非常說明問題。這個術語能引起更早時期針對異教徒和道德墮落的文學提出指控的回聲---也就是說,是道德污染或者是道德毒藥。比如約西亞·利茲(Josiah Leeds)在《關於印刷的毒藥》(1885)中區分了「淫穢」與「廉價小說的惡劣影響」,他聲稱雖然並不「一定是淫穢的」,但依然構成對社會的毒害」。
當然,今天的懷疑論者沒有被指控淫穢或道德墮落。不,他們被指控「否認主義」。這是他們的邪惡行為,他們的異教徒觀念。把懷疑論歸結為否認主義的範疇,人們給懷疑論實踐賦予了一種邪惡意圖。因此,懷疑論者不是在質疑或者懷疑普遍接受的立場;相反,他或她是在否認普遍接受的立場的真理性。這是這種戰略的准宗教威力,通常避免採取普遍接受的立場的《衛報》更新了它2019年的風格指南,意思是氣候懷疑論者從那以後往往被稱作氣候科學否認者。並不令人吃驚的是,同樣的修辭戰略也已經被應用在那些質疑封鎖隔離措施的人身上,這些人在社交媒體和主流媒體上常常被指控為「新冠病毒否認者」。
否認主義的觀念當然具有神學的威力,因為它來自否認上帝話語這個曾經不可被饒恕的罪惡。但是,其當今道德威力大部分來自它與否認納粹大屠殺的聯繫。該術語被用在那些否認大屠殺這場人類悲劇的人身上,這樣一來就成了事件之後的幫凶---否認大屠殺就理所應當地被視為罪惡。而將這個術語用在質疑封鎖隔離措施或氣候變化現有立場的人身上就是利用了大屠殺的殘餘。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對大屠殺浩劫(the Shoah)的無恥濫用是懷疑論敵人的標準做法。他們已經將否認大屠殺的行為轉變成為普遍性罪惡,一種可以用在任何懷疑論立場上的自由流動的褻瀆神靈之罪。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否認很惡毒,可能產生很糟糕的影響。氣候變化否認者導致本來能保持地球健康的行為缺失。拒絕戴口罩者導致新冠病毒傳播加快和致死率增加。」
其實,常常出現的是,道德聖戰者已經非常熟悉否認行為,他們已經不再說出觀點的區別是什麼樣子。這很難令人感到吃驚。人們對挑戰現有智慧者的不寬容心態加劇了否認主義指控力度,使其變得日益囂張。
在中世紀,異教徒罪惡往往與否認天主教的真理條款有關。如果異教徒拒絕放棄其立場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或將被燒死在火刑柱上。這個做法在宗教改革之後仍繼續存在。比如在英格蘭,巴多羅買·萊格特(Bartholomew Legatt)和愛德華·懷特曼(Edward Wightman)因為否認基督的神性而激怒了英國教會,兩人在1612年雙雙被燒死在火刑柱上。懷特曼成為最後一個受到這種懲罰的英國異教徒。
今天的否認者並不會被當作應該燒死在火刑柱上的罪人。相反,他們常常被當作心理有毛病的個人,在等待治療期間應該被隔離起來遠離主流辯論。其實,這是當今反對懷疑論思維的典型特徵:指控否認主義者壞蛋存在心理問題(psychologisation)。懷疑論者不僅僅是錯誤的,他們還患了病。因此,2009年學術會議詢問否認氣候變化者是否「有消費上癮的毛病。」
否認甚至成為心理學詞彙的組成部分。它被描述為一種防禦機制,用來保護患者免受現實的侵擾。否認被用來作為準診斷範疇將懷疑論轉化為心理問題。被當作否認者的懷疑論者也就不再是平等的辯論對象,而應該被當作道德上或心理上低人一等的人。正如伯克利計算認知科學家塞萊斯特·基德(Celeste Kidd)解釋的那樣:
「我們並不知道堅持擁有令人懷疑的信念的趨勢能否經過訓練而消除,如果人們意識到自己可能犯錯,他們可能被教導在行為上變得相應溫和一些。我們正在調查該觀點的可靠性。我們將檢驗一番看看結果如何,這正是科學的運行方式。」
如果給人洗腦是「科學的運行方式」,那麼社會就陷入大麻煩了。值得記住的是,這樣的「科學」曾經在蘇聯實施過,那裏持不同政見者通常被診斷為患了心理失常的毛病。這很難說令人吃驚。病例學懷疑論允許那些掌權者將批評者推到邊上去,認為他們不僅錯誤而且有病。
什麼是懷疑論?
在懷疑論通常遭到維持現狀者的詆毀和譴責時,澄清懷疑論到底是什麼以及我們為什麼必須捍衛它就非常重要。
作為一種哲學觀念,懷疑論自古希臘時期就已經存在。蘇格拉底說「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什麼也不知道。」他的要點是無知是積極探索真理的起點。這歸納了懷疑論者的定義性特徵:擱置判斷。因此,懷疑論者是對於什麼是真,什麼是善,什麼是正義等還沒有做出決定的人或者不處於做決定的位置的人。
這種擱置判斷並不一定意味着拒絕判斷。它可能意味着推遲判斷,同時懷疑論者繼續探索手頭的問題。與涉及到對真理做出否定判斷的懷疑不同,懷疑論代表了一種預判斷。它與教條或毫不懷疑的確定性態度相反。當然,在某些情況下,擱置判斷可能是一種逃避行為。但是,推遲判斷也可能是致力於進一步探索真理和追求清晰性的前奏。
作為哲學定位,懷疑論代表了對人類太容易擁抱教條的誘惑的挑戰。對古希臘人來說,懷疑論不是關於不相信什麼或否認某個特定立場的。真正的懷疑論者很少宣稱他知道某個特定立場是錯誤的。懷疑論意味着探索。雖然它的動機可能非常複雜,懷疑論的思想基礎是相信真理很難獲得。
就像任何好想法一樣,懷疑論不應該被教條式地追求。沒有必要放棄這樣的觀點,籠統的知識服務於沒有盡頭的懷疑探索的利益。一種懷疑論心態有可能接受科學研究的結果,同時對將來修改甚至拒絕它的可能性仍然抱有開放態度。
在當今獨特的不確定性世界,這種既有開發知識的潛力同時又不宣稱確定性或發現了真理就顯得至關重要。其重要性不僅僅在於促進科學的發展,而且促進民主公共生活的繁榮。沒有質疑的權利,就不可能有思想自由。這就是為什麼當今對懷疑論者的妖魔化——稱之為否認者、腐敗分子、道德低劣者——不僅反映了支持建制派者的詭辯論傾向,而且也是對人類探索本身的攻擊。
社會需要懷疑論才能發展。懷疑論鼓勵社會質疑假設和想當然的「事實」,它們很可能逐漸僵化並成為教條。它讓我們的思想生活屈服於新體驗。總之,懷疑論是確定性泛濫的解毒劑。
懷疑論者的態度在當下特別重要。在當今這個危險時刻,當人類遭遇新冠病毒的致命威脅時,有一種關閉辯論和限制言論自由的誘惑。在此情況下,不同觀點可能很容易被嘲弄和指控為對人民健康的威脅。在有些人看來,辯論本身似乎都是我們負擔不起的奢侈。但是,恰恰是在危急時刻,在疫情嚴重的當下,辯論和言論自由變得不可或缺。它們是人們用來鼓勵創新和運用公眾的智慧應對我們不知不覺陷入的危機的手段。
19世紀生物學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曾經寫到「懷疑論是最高的義務,盲目信仰是不可饒恕的罪惡。」現在,這個命題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值得我們去悉心接受。我們未來的自由或許就指望它了。
作者簡介:富蘭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英國著名社會學家,著有《恐懼:推動全球運轉的隱藏力量》、《受到圍攻的民主:不要聽任它被封鎖起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