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的危機與川普變法
公元2020年11月,世界史無前例地分成了兩個陣營:川普陣營和拜登陣營。美國的總統選舉歷來引人注目,但是全球有如此之多的人帶着如此之深的認同感捲入這場大選,以至於沒選票的外國人都會因為對美國候選人的認同而與親朋好友決裂,這在人類歷史上絕對是第一次。然而,無論你是支持川普還是支持拜登,你都會同意:西方陷入了深深的危機之中——支持拜登的認為西方已經在泥沼中陷落了四年,支持川普的認為西方即將陷落四年,而在川普執政以前已經陷落了八年了。
2017年7月,我在倫敦一個小型對話會議上聽了一場英國前首相卡梅倫與法國前總統薩科齊的對話。兩人一致認為西方的民主政體出現了體系性的問題,而不只是個別需要修補的漏洞。當然那時候兩人還沒使用「危機」這個說法,對問題的具體內涵也還沒有清晰的歸納與表述,只是有一些不成系統的片段看法。實際上,西方的危機從2001年的911起就已經嶄露頭角,從2008年的金融崩潰起開始顯山露水,2020年則借着新冠疫情的發力而開始全面爆發。
從根本上說,西方的危機起源於西方的勝利。「勝利者的魔咒」在於膨脹的自信心。這種自信很快會被提升到理論高度,形成一套炫人眼目的「勝利哲學」。人們相信他們不再需要腳踏實地地研究現實問題,而只需要像念咒語那樣把這套法寶祭出來,就可以所向披靡了。這套法寶隨後會疊床架屋地自我演變,生出不容他人質疑的神聖光環來。走到這一步,人們就離災難不遠了。適度總結經驗原本不是什麼壞事,問題在於,考慮到人類行為的非理性特徵,人類社會的規律性本來就是一件值得懷疑的事情,加上現代人類科技創造與商業創新的飛速發展,經驗的時效性早已大大縮短,這些「勝利哲學」很快就會與現實脫節,在這種情況下迷信「法寶」,想避免危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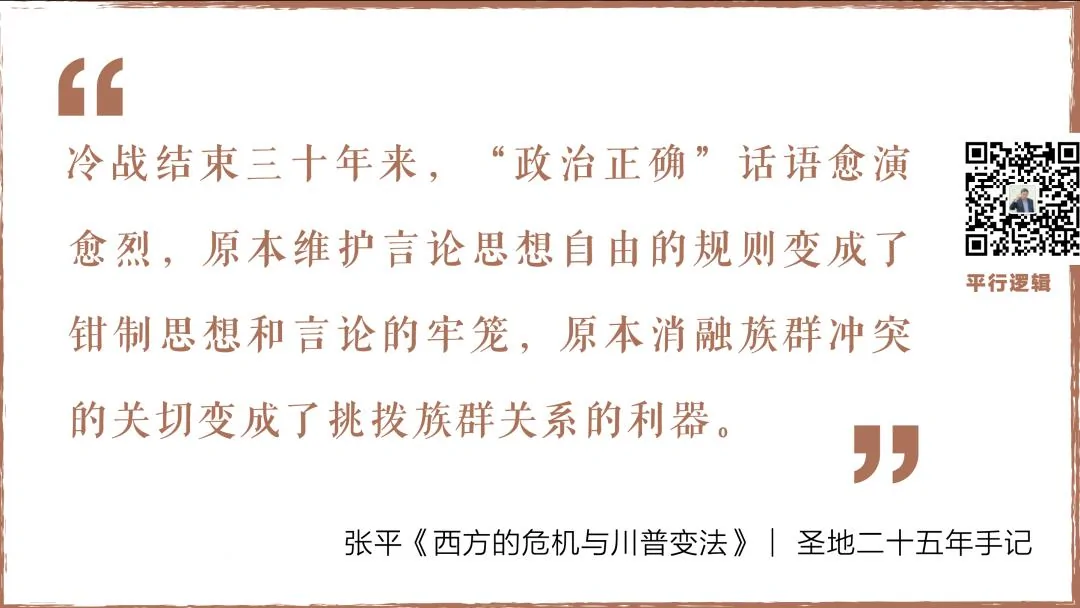
西方危機最深層的表現是「政治正確」話語的泛濫和肆虐。作為一種六、七十年代發展起來的一種意識形態規範,「政治正確」在冷戰結束後的九十年代開始以「勝利話語」的姿態加速擴張自己的地盤,並引發了越來越多的爭議。「政治正確」的初衷並不算壞,因為思想自由原本也是需要一些規則來維護的,對弱勢群體和少數族裔的敏感問題稍加注意也是合理的。但是無論什麼好東西,一旦自封光環,很快就會走向反面。冷戰結束三十年來,「政治正確」話語愈演愈烈,原本維護言論思想自由的規則變成了鉗制思想和言論的牢籠,原本消融族群衝突的關切變成了挑撥族群關係的利器。到2020年,「政治正確」借着「黑命貴」運動的助力,進一步發展成了近乎瘋狂的網絡「取消文化」,傳統被砸爛,異見者(包括多年來推進「政治正確」的學術圈)遭無情迫害。今日的政治正確,已經演變成了文化上的原教旨主義和極端主義。正如艾倫·布羅姆在《關閉美國的思想》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政治正確」給所有的事物都打上「正確」與「錯誤」的標籤,封閉了開放性思維的大門,使得新一代年輕人習慣於搞自信滿滿的價值判斷,而不懂得獨立自由的思考的價值。之所以說政治正確是西方最深層的危機,是因為這種思潮直接打擊着西方文明過去賴以崛起,如今賴以維持優勢的秘密武器——思維的創造力與商業的創新能力。
西方危機的第二個層次是族群關係的撕裂。如上所述,這個層次的危機是上一個層次引發和推動的。政治正確在這個問題上強調兩個自相矛盾的要點——「多樣性」和「族群歧視」。「多樣性」意味着你必須承認、接受乃至鼓勵、強調各族群間的差異性,且禁止批評,更不能去改變任何族群文化中的不良成分,無論這些不良成分如何與人類的普遍價值相衝突;「族群歧視」則意味着將各族群之間的差異,特別是少數族裔或者弱勢族裔在社會經濟地位方面的差異歸結為「歧視」的產物,煽動這些族裔與主體族群之間的衝突。2020年爆發的歐洲移民社群問題,美國黑人抗議運動,本質上都是政治正確這兩把「族群利刃」一手擴大差異,一手激化衝突的直接後果,而與子虛烏有的「系統性歧視」毫無關係。
西方危機的第三個層次是中產階級的消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資本全球逐利,西方的中產階級工作流失,逐步貧困化。在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情況,大資本用左翼福利主義的主張拉攏下層民眾和少數族群,用加稅的辦法進一步剝奪中產階級的權利,同時打壓中小企業的崛起和發展——大資本有的是避稅的辦法,無處可逃的是工薪階層和中小企業。但這種福利主義只能是飲鴆止渴,中產階級總有被榨乾的那一天,中小企業無法發展將進一步增加貧困人口,同時嚴重損害商業創新能力。最終,貧富差距不會縮小,只能越來越大,而中間階層的消失將使社會失去粘合劑,社會矛盾失去緩衝區,最終引發社會的崩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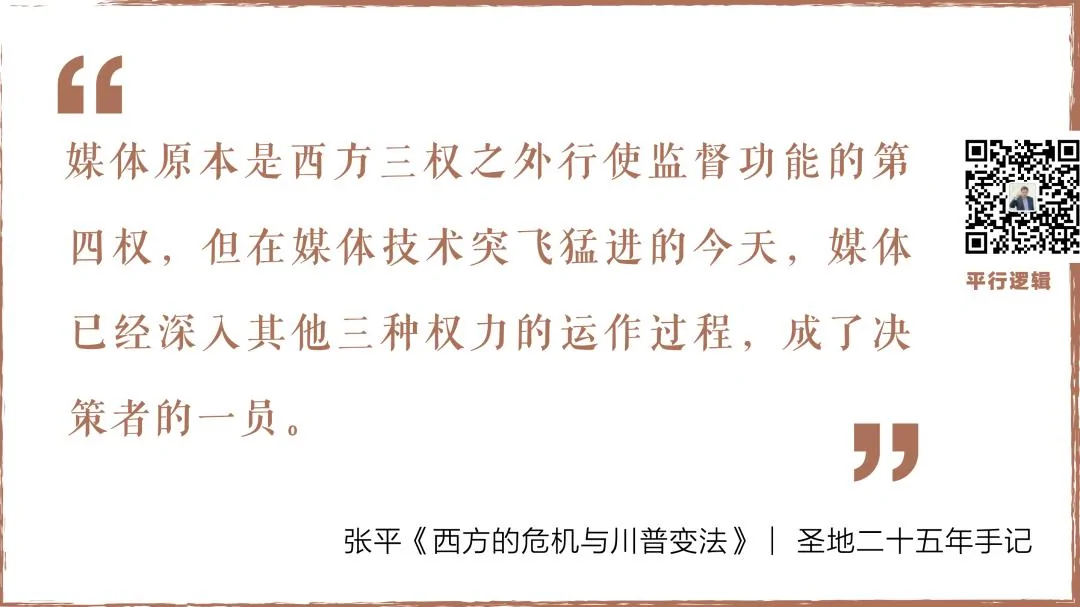
西方危機的第四個層次是媒體權力的無節制擴張。媒體原本是西方三權之外行使監督功能的第四權,但在媒體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媒體已經深入其他三種權力的運作過程,成了決策者的一員。在2017年的倫敦,卡梅倫和薩科齊不約而同地提到媒體的霸權問題。其中梅捷談到二戰時丘吉爾有一次為了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閉門苦思五天,謝絕一切訪問。然後他抱怨說今天的政治家再沒有丘吉爾的奢侈,不要說五天,連五個小時都不會有,因為媒體的介入程度會逼迫他做快速而草率的決定。問題是:媒體是這四權中唯一一個不用為自己的行為承擔罪責的權力,因此也是當今這四種權力中最為粗暴和不負責任的。兩人都沒罵「假新聞」,但提出來的問題跟川普是一樣的:當新聞自由變成了一種政治權力之後,誰來制約媒體?
人類歷史的循環很大程度上就是理念想像與常識理性的反覆交替。當理念與想像自我膨脹到與現實脫節的程度,危機與災難就不可避免,而出路則在於擺脫這些「法寶」的魔力,回到最基本的理性和常識上來。危機和災難都不可持續,如果改革不能讓瘋狂的頭腦冷靜下來,大崩潰就會把所有的人直接打回原形。就好像2008年的次貸危機,底層的房屋貸款被包裝成各種理念的投資產品,用五花八門的方式推銷,以至於人們忘記了最初的那些貸款是放給誰的,放了多少,還得起還不起。最終,當大崩潰來臨時,人們才會想起基礎的理性和常識仍然是王者,你無論怎麼忽悠,潮水總是要退的。
川普本質上是一個用直覺感受到了危機和災難的來臨,並試圖採取行動挽狂瀾於既倒的變法者,他是危機的結果而非危機的起因。他用粗暴的話語破壞政治正確的基本原則,試圖在思想的牢籠上撕出一條口子來;他用自媒體與傳統大媒體抗衡,試圖抵抗媒體霸權對政治權力的入侵;他給企業減稅,試圖挽救日益消亡的中間階層;他阻擋非法移民和特定地區人員的入境,試圖在族群撕裂問題上喘一口氣。他的基本邏輯是最為簡樸的實用理性和常識,就像他建造紐約溜冰場所使用的邏輯一樣:紐約市政府從陽光沙灘的佛羅里達僱用了一家建築商來造溜冰場,造了快七年還沒有蹤影;川普從冰天雪地的加拿大找來一家專業公司,四個月就造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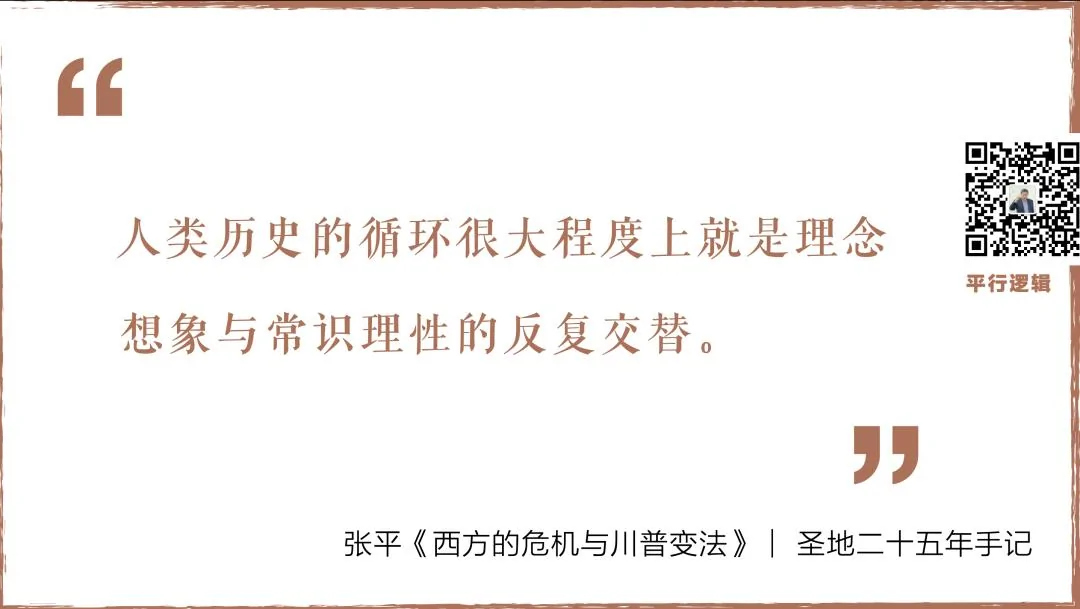
川普的樸素理性思維是他的長處,也是西方危機的出路,但同時也是他的局限。這種局限使得他在過去的四年裏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美國國內製度的變革上,而是消耗在了大量沒必要的國際爭端中,雖然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責權利關係確實也是危機的一部分,但那只是國內製度問題的外延而非成因。川普因此付出的代價也將是沉重的——當利益集團反撲是,川普毫無還手之力。而留給我們的問題是:川普變法是將隨着他本人的下台(如果不是現在那麼是四年以後)壽終正寢還是會以其它形式蓬勃生長乃至開花結果?當然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西方的危機還要持續多久?將會以怎樣的方式終局?
張平2020年11月6日星期五於特拉維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