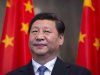我住在香港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這幾年每年都住六個月。很慶幸沒認識不支持抗爭的香港人,但討論香港情勢的對象多數是非香港人,而認為抗爭者是暴徒的外國朋友不在少數。

香港。
就我看來,他們對暴徒的抱怨好像只是因為在香港的舒適生活被影響罷了。他們坐在酒吧里高談闊論年輕人該如何如何,說若要批評警察暴力就不該以暴力反擊,說和政府坐下來談才是知識分子該有的作為。接着他們會開始計劃聖誕節,要在中環的瑪莎百貨買什麼英國進口的過節食品,該寄什麼聖誕禮物給歐洲的家人,或是索性買機票回歐洲過節吧,反正時局這麼亂,過節的氣氛都沒了。
我很少與西方朋友爭論,頂多說說自己的看法,我知道自己有先入為主的偏見,認為他們來自民主十分成熟的歐美國家,很難設身處地體會正在爭取民主或是新興民主的困境。我告訴自己,這些人真的是事不關己的外國人,他們並不會有被中國統治送去再教育營的一天,何必時時刻刻在意香港人或是台灣人的感受?再怎麼努力解釋也是隔靴搔癢,我想。
而正當香港警察大肆在各大學或是街頭濫補之際,國民黨推出令人不敢相信的不分區立委名單,有去中國立正敬禮唱對方國歌的,有呼籲中國武統台灣的,有以統一為目標的,還有對港警施暴頻頻叫好的。看到名單那天,我愣了一下,不知道究竟是港警抑或是國民黨比較可惡。
香港畢竟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警察奉命行事,或可能他們是中國安插在香港的武警軍人,難以對香港市民有同理心,因為在他們眼裏示威者不論合理非或是勇武都是分裂國家的反動份子。果真如此,港警的暴行似乎得以解釋。
而罵香港暴民的台灣人,彷佛乖乖讓中國當畜生豢養就不會有事的台灣人。他們看不見警察拿槍指着少年的致命處,用腳硬踩着被捕者的頭,護送打人的黑幫份子離去,或是無端逮捕路人強行搜索。他們只看見蒙面示威者破壞地鐵,在鬧區設路障對警察擲汽油彈。暴徒,他們說。

暴徒或者示威者。
但究竟誰是暴徒?暴徒是如何產生的?客觀看香港示威者的行為,的確是暴徒行徑沒錯,但如果應該保護市民的警察成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惡煞,濫打濫補市民侵犯被捕者,不反抗嗎?沒來由踢路邊的一條狗它都要暴怒咬你一口,不知反抗豈不是連禽獸都不如。
一位住在紐約的新加坡朋友轉發了一篇評論,大意是示威者對時局政府諸多不滿可以理解,破壞地鐵或許可以得到暫時的快感,但他們已經成為暴徒,他們的行徑無論如何得不到民主,只會終結香港的前途。
另一位住在倫敦的泰國朋友轉發了一篇香港經濟因示威衰退的分析,並且加上註解:所以最後是誰受害呢?這兩位都是我曾經在路透社新加坡共事的同事,他們的觀點不外乎香港目前已經失控,示威者趨向極端,百害而無一利。
雖不直接挑明,表面上似乎只是客觀看香港,但無論是各打五十大板,或是不置可否只譴責暴力,都已經選擇了壓迫者的一方。在執政者和人民所擁有的公權力或是武力完全不對等的情況下,前者的暴力勝於後者百倍有餘,後者的暴力則是為了保護自己,抑制前者的暴力。以暴制暴絕非上策,但坐以待斃任人宰割,忝為人。
我向新加坡朋友解釋,有些年輕人對此次運動有幾分近乎浪漫的革命情懷,雖知大勢難為,寧願放手一搏視死如歸,至少知道自己在香港的歷史上留下一筆。朋友答道:成為歷史中微不足道的一個註腳,究竟有什麼意義?我悲觀地想:那麼這麼苟且仰人鼻息活着就有意義?甚至連歷史的註腳都稱不上!如果努力也無法實現信念達成理想就該放棄,那麼人總是有死亡的一天,應該天天坐吃等死?
我再向泰國朋友解釋,或許因為我來自台灣,對香港發生的一切感受特別深,因為中國沒有打算侵略泰國,泰國人也無需擔心社會信用點數,我們的感受不同。朋友答道:我明白,但是示威只會把香港的經濟搞垮,對誰都沒有好處,他們應該跟政府好好談。我盯着手機上的對話框無法回答,身為國際記者不會不知道中國是個出爾反爾的政權,自始至終不願意回應的是香港政府。
這兩位朋友都是周遊列國的駐外記者,來自亞洲定居歐美,他們的看法竟然和在香港的一些西方人如此相近。我開始懷疑,是否有些西方人認為亞洲需要強權政府,民主只會造成動亂;一些亞洲人認為服從才能安定,民主無法幫助經濟成長。而這些人,都正在享受百分之百的自由民主。
在台灣何嘗不是如此?那些說不要大小聲務實別鬧事的人,在台灣生活無虞有絕對的民主自由,他們認為香港示威者破壞安定。難道香港人不能還是不該和我們有一樣的民主自由?或是因為香港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就該跟新疆人一樣被迫害?
最近《南華早報》有一篇投書,作者是殖民時期在英國皇家海軍服役的英國軍官戴維斯,1967年香港暴動時他負責訓練港警如何反暴,退役後在香港大學任教。當年親共人士對抗港英政府,最初只是工人運動和反政府示威,最後演變成恐怖主義及炸彈襲擊平民等行動。

港警裝備精良,紀律卻沒跟上。
戴維斯提及當年訓練的港警極為優秀紀律嚴謹,他們幾乎沒有什麼武器更別提裝甲部隊,面對火力十足的抗爭者也沒有出現如今日的警察暴行。而今警察擁有比以前更精銳的武器,把自己保護的滴水不漏,猶如驚嚇的男孩手持致命武器,而面對的卻是比1967年更不危險更不兇殘的示威者。最糟的是他們的長官絲毫沒有盡到領導責任,不但允許甚至還縱容警察違法脫紀的行為。
一個卸任的英國軍官見證了香港警隊半個世紀以來的變化,而當港警停止保護市民甚至開始攻擊市民時,誰是暴徒不證自明,更別提在香港社會藍絲黃絲如此撕裂之際,多數市民一致認為政府和警察必須對現今暴力現象負起最大的責任。
戴維斯在投書最後寫道:民主是一種極不完善的政府形式,但最主要的好處是,一旦我們有了民主,我們就可以把管理我們的那些尸位素餐無用者踢下台。是的,我們在台灣享有的民主的確不完美,但選票卻一定可以讓那些打算把台灣拱手讓人換取利益的無用者無法得逞。
在這個越來越荒謬的世界,還是要有一些熱情和希望,否則現在就放棄吧,反正勢不可為。我是絕對不會這樣想的。香港小心,台灣加油。
作者曾任路透社駐台灣及新加坡特派員,住過印度六年出版過一本書,目前在香港和普羅旺斯之間如候鳥般移居。